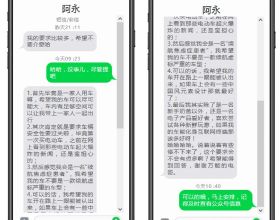許志傑
考古學界有論,吳金鼎發現了城子崖遺址,也是龍山文化的發現者,但命名乃至進一步闡釋論證龍山文化的重要性及其文化功能,則應歸於梁思永的貢獻。
吳金鼎發現了城子崖遺址
梁思永在《龍山文化——中國文明的史前期之一》文中,簡述了“龍山文化”一名的來歷,他說,“龍山文化之存在的證據,最初是吳金鼎在1928年春所發現而提出來的。在當地叫做城子崖的臺地的西面斷崖上,暴露著一個完整的文化層。在這裡這位發現者掘出了與石器骨器共存的,薄胎而帶黑色光澤的陶片。被這個文化遺物部分地堆成的城子崖,是山東省歷城縣東75華里的一條小河的東岸上,正對著小小的龍山鎮。因此,龍山這個名字就作了所發現的文化的稱謂”。“龍山文化”之名由此而來。
1935年,梁思永發表《小屯、龍山與仰韶》一文,對三種不同地區文化形態的關係進行透徹、科學,符合歷史邏輯推論的分析。他認為龍山文化最早期的時代,比仰韶時期的彩陶文化的時代早,而龍山文化與殷墟遺址小屯文化不是銜接的,但殷墟遺址小屯文化是由龍山文化承繼得來,而其餘文化則是在黃河下游比龍山晚的文化。梁思永這些對龍山文化的論斷在當時影響至大,至今為考古學界推崇。

梁思永主持第二次城子崖發掘時的合影,左一為梁思永,攝於1931年10月。
1904年10月7日,梁思永在中國澳門出生,他是梁啟超先生次子。1923年畢業於清華學校留美預備班,本計劃當年即赴美留學,但5月7日與長兄梁思成在北京被汽車軋傷,耽誤行程,傷愈第二年乘坐郵輪踏上美利堅國土,後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習考古和人類學。留美期間參與美洲印第安人古代遺址的發掘,其父梁啟超曾自豪地宣佈兒子是“中國第一位專門考古學者”,此話無謬。
1927年梁思永應父親要求,曾短暫回國跟隨考古學家、“有中國考古之父”譽稱的李濟先生到山西省夏縣西陰村發掘,並受邀在清華大學研究院擔任助教,次年返美繼續深造。1929年1月梁啟超病逝,當時梁思永剛到美不久,未能返國弔唁。1930年夏,梁思永獲得哈佛大學碩士學位,歸國後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
隨即梁思永便參加由“中研院史語所”發起的“東北考古計劃”,先後在黑龍江發掘昂昂溪遺址,在熱河完成中國人第一次系統的東北考古調查。其後到河南安陽參加小屯殷墟遺址發掘並主持後岡遺址發掘。1931年秋,趕赴山東參加龍山城子崖遺址的第二次發掘。
說到龍山文化,就不能不提城子崖遺址的發現與確定者吳金鼎。吳金鼎1901年出生于山東安丘一個耕讀之家,世代務農,卻崇學上進,到吳金鼎這代家中四男均考入大學,四女全都至少讀完初中。吳金鼎1919年考進齊魯大學文理學院社會歷史學系,後留校任教,1926年考進清華學校研究院,讀人類學,後專業師從李濟先生學習考古學。一年後返回母校繼續任教,並開始對濟南周邊的歷史遺蹟進行考察,其中1927年到1928年兩年時間對平陵城以及附近的城子崖進行了六次有目的的考察,並基本確定城子崖為重要歷史遺址。
當時齊魯大學尚不具備獨立考古資質和發掘條件要求,吳金鼎把自己的發現告訴了導師李濟。此時李濟領導的“史語所”考古組在安陽殷墟的發掘受到中原大戰影響而停止,收到學生提供的訊息,立即與傅斯年等人商量,並聯合成立“山東古蹟研究會”,對城子崖遺址進行有秩序的發掘。傅斯年任委員長,李濟為主任,日常工作由已經被聘為“史語所”助理研究員的吳金鼎負責,第一次發掘之後吳金鼎被任命為駐山東古蹟研究會負責人,直到去英國留學而去職。古蹟會成立之後立即開展田野工作,當時臨近冬天,因此選擇在各方面條件比較便利的城子崖開始。
第一次發掘為一個月,時間從11月7日到12月7日,參加的人員是李濟、董作賓、郭寶鈞、吳金鼎等六人。採用的是考古層位學的方法,發現城子崖臺地的斷崖上清晰可見的“文化層”,這次發掘最有特點的出土物是黑陶,其中的黑陶杯“黑如漆、明如鏡、薄如紙、硬如瓷,掂之飄忽若無,敲擊錚錚有聲”。此後,經過吳金鼎的整理,這些新發現文物展現出龍山文化的總體面目。
第一次發掘藝術品的收穫不如早先的殷墟,但城子崖的發現對於中國考古學的推進實在太重要了,可以說是中國史前文化研究的一個里程碑。1930年11月6日,山東古蹟研究會在山東大學工學院召開了城子崖遺址新聞釋出會,李濟發表講演,對城子崖遺址的第一期發掘進行階段性總結,對出土的黑陶遺存在中國史前文化研究上的重要意義給予充分肯定。
梁思永提出統稱為“龍山文化”
有了第一階段發掘成果的鼓舞,山東古蹟研究會隨即於1931年秋天開始了第二次發掘,時間是10月9日至31日,這次帶隊的是梁思永、吳金鼎兩位年輕的考古學家以及王湘等人。第一次發掘,因為李濟和董作賓知識結構的侷限,以及在相關考古發掘技術上的缺陷,發掘工作存在一定短板。但是,作為留美歸來並掌握了現代考古知識與手段的梁思永,已經完全突破傳統考古認知和方法,尤其在田野考古方面,填補了李濟、董作賓等老一代考古學家留下的空隙。李濟對梁思永在這方面的貢獻十分認可。他曾經這樣說:“梁君是一位有田野工作訓練的考古學家,並且對於東亞等考古問題做過特別的研究。兩年來他對於考古組的組織上和方法上均有極重要的貢獻。”
梁思永對於城子崖遺址發掘最大的貢獻,在於他透過安陽殷墟後岡遺址的發掘,出土了與城子崖遺址下層文化相同的黑陶期遺物,從而進行比照研究。他與吳金鼎捨棄第一次發掘時的層位學,採用西方最先進的科學考古方法——地層學,參照殷墟後岡遺址文化堆積不同土質、土色、包含物來劃分文化層,成功區別出不同時代的古文化堆積,發現彩陶-黑陶-殷墟文化遺存三者之間是以一定的順序疊壓著的“三疊層”。陶器多為手製,但輪制已經出現,這些陶器技藝精湛、造型獨特,遺憾的是製作工藝已經失傳。由出土的卜骨、築版與夯土分析,梁思永斷定城子崖文化與殷商文化為直接的傳承關係,同時又反襯對殷墟建築遺址的重新認識。城子崖遺址發掘首次發現以磨光黑陶為顯著特徵的新石器時代遺存,最初被稱為“黑陶文化”,後經梁思永提出統稱為“龍山文化”。
據記載,到了城子崖第二次發掘後期,暴雨突至,雨水迅將幾個已經挖掘了一米多深的探坑全部灌滿。根據以往經驗和辦法是等待坑水全部自然乾涸後,才能繼續發掘,這樣至少要等一個星期的時間。經過商量,決定採用吳金鼎提出的建議,借用村民的水桶將探坑中的水排出,晾乾,儘快重新發掘。梁思永、吳金鼎親自上陣,在齊腰的水中與民工一起排水,保證了發掘工期按時完成。此次挖掘,除去星期日休息,實際工作20天,單日最多用工48名,開挖探坑45個,總面積達到1520.8平方米,發掘古物共裝60箱,由龍山運至濟南山東古蹟研究會儲存。1932年3月,城子崖遺址第二次發掘的古物由吳金鼎全部整理完畢,發掘的結果再次證明安陽殷墟遺址與城子崖遺址出土的黑陶文化基本一路,證明梁思永在此前的推論是正確的,也以極具說服力的資料,糾正了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將仰韶與龍山兩種新石器時代文化混在一起,錯誤得出“粗陶器要比著色的陶器早”的結論。
中國第一位專門考古學者和田野考古第一人
梁思永被其父梁啟超稱為“中國第一位專門考古學者”,他的親密合作者吳金鼎則被後來考古學家稱之“田野考古第一人”。吳金鼎著作《平陵訪古記》於1930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四分冊刊出,很生動地敘述了城子崖的發現和調查的經過。兩位年輕考古學者的合作始於1931年春,他們一起到安陽參加殷墟第四次發掘。開始的時候,他們同在小屯發掘,他們有共同發展的遠景,於當年4月16日離開小屯,分別向東西尋找他們的理想之地。梁思永向東,選擇了後岡遺址,吳金鼎向西,選定了四盤磨遺址,隨即主持四盤磨遺址的發掘。
這兩個遺址雖然皆屬殷墟遺址部分,卻因各自帶領發掘團隊,更能體現他們對現代考古科學的認知程度。到了秋天,兩個人又為了共同目標,一起從安陽殷墟來到濟南龍山的平陵城,對城子崖遺址進行第二次發掘,在考古實踐中結下很深的情誼。1933年秋,吳金鼎受山東省政府派遣到英國倫敦大學學習現代考古與人類學,師從著名埃及考古學泰斗彼特里教授,並在巴勒斯坦進行現場發掘。他還到倫敦中央高等工業學校,實習原始製作陶器的方法。87歲高齡的彼特里教授盛讚自己的學生,“吳先生確是一位田野工作的好手,雖不英銳機警,但沉著謹慎,工作罕匹”。和他一起發掘的阿拉伯工人,也都豎起了大拇指,說吳金鼎是“頂好”的。如果說梁思永是“中國第一位專門考古學者”,那麼吳金鼎就是“中國第二位專門考古學者”。
1937年吳金鼎以論著《中國陶器》,獲得倫敦大學人類學(考古學)博士學位,毫不誇張地說,吳金鼎是“第一位獲得人類學(考古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回國後,他先後在“中研院史語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帶領團隊在西南地區的四川、雲南從事考古調查,被譽為“中國西南地區田野考古的奠基人”。抗戰結束後,吳金鼎毅然受邀回到母校齊魯大學,先後擔任文、理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等多個職務,主持齊大國學研究所工作,為齊大復員濟南,重鑄輝煌出力巨多。

曾與吳金鼎在中研院史語所共事多年的著名考古學家石璋如這樣評價自己的同事:“吳先生是龍山文化的發現者,田野考古調查約20次,所得遺址84處,發掘遺址26處,是帶女性員工田野考古的開端者,也是田野考古的先鋒。從山東的史前,到河南的殷周,又到四川彭山的漢、雲南南詔大理的唐宋,以至成都琴臺的五代。時間上下數千年,地區縱橫數萬裡,涉獵經驗之豐,文化貢獻之多,直到現在為止,在田野工作上來說,有哪一個人能比得上他呢?稱得上田野考古第一人。”
1948年9月20日,吳金鼎因患胃癌在濟南病逝,年僅47歲。志達願高,出師未捷,令人惋惜。而他的摯友和考古事業的同路人梁思永,1949年後進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擔任副所長,1954年4月2日因心臟病突發,在北京逝世,享年也只有短短的50歲。兩位考古學英才,共同開拓了影響世界的龍山文化發現、發掘和傳播事業,功莫大焉,書寫一段中國文化史的感人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