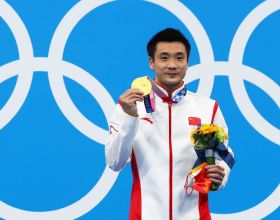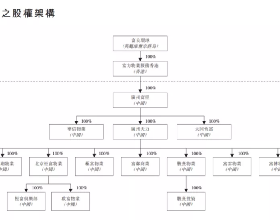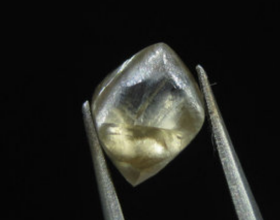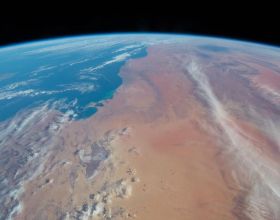敘介中國現代文學史,“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佔有重要一頁;講到左聯,“文藝自由論辯”是一道靚麗的風景;這場文藝論戰既以“自由人”胡秋原的《阿狗文藝論》一文為發端,也因其左右開弓而風生水起。
一
胡秋原(1910-2004)與周立波(1908-1979),當年都是一腔熱血的愛國青年,卻因觀點相左,尤其是書生意氣而結下了樑子。
1931年9月19日,胡秋原正準備在上海乘船赴日本早稻田大學完成學業。忽然,他聽到廣播緊急播報:日軍在東北製造了“九·一八事變”!他毅然決定棄學,留滬以筆為投槍抗日。
此前,胡秋原與十九路軍領袖陳銘樞創辦的新聞出版機構——神州國光社,已經建立了合作關係。那時,胡秋原與王亞南、楊玉清等同學在早稻田大學成立了從事編譯的“白沙社”,翻譯叢書交由“神州”出版。文稿往返,胡秋原與“神州”總編王禮錫莫逆於心。原來他們的思想源頭,均來自大革命中反帝反軍閥的主旨,服膺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普列漢諾夫的文藝理論。王禮錫曾與田漢主編《中央日報》之《摩登》副刊,同時任教於田漢創辦的南國藝術學院,與徐悲鴻、劉海粟、鄒韜奮、郁達夫、歐陽予倩等人交遊;胡秋原則在武漢編輯過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機關報《武漢評論》、主編全國學聯的《中國學生》,交誼於董必武、熊十力、陳望道、魯迅等名流。
王禮錫出任“神州”總編輯後,先後出版了一系列進步的人文社會科學新書。1930年12月初,王禮錫、陸晶清伉儷到日本度蜜月時,又力邀胡秋原襄助創辦《讀書雜誌》。
此次胡秋原在滬,他出任神州國光社及《讀書雜誌》編輯的同時,又於1931年12月25日獨立創辦了《文化評論》週刊,主張在政治上抗日,在文藝創作上“自由”。
二
正當《文化評論》週刊排版就緒,哪知日軍於1932年1月28日夜悍然發動了對上海的侵略戰爭。駐守上海閘北的十九路軍第一五九旅,不待軍命,奮起抗擊,將士們經過一夜的浴血奮戰,一舉重創了入侵的日寇。
胡秋原聞訊立即前往戰地採訪,寫下了軍民協力抗戰目擊記。隨即,他聯絡了一批文化界朋友聚集在王禮錫家裡,講述了他赴前線採訪的見聞,籲請大家討論如何聲援十九路軍將士抗戰、號召全國人民抗戰等問題。
討論中,胡秋原建議由《文化評論》與《讀書雜誌》合辦一份報紙——《抗日戰爭號外》,得到大家首肯。說幹就幹,這份由胡秋原主筆的《抗日戰爭號外》,其內容包括報道十九路軍的抗敵戰績,揭露日寇罪行,批評政府不抵抗政策的錯誤,呼籲全民族抗戰到底等。
1月30日,胡秋原與王禮錫親自到現場指揮,下午2時,數萬份《抗日戰爭號外》遍及上海灘的大街小巷……《號外》首先刊發了他們赴戰地採寫的上海文化設施毀於戰火的實況報告——
商務印書館和東方圖書館的被毀,諸多學校圖書館慘遭厄運,此次遭受破壞的16所高校中,同濟大學、交通大學上海本部等12所學校的圖書損失總數達八十萬冊;39家電影院中的16家遭受毀損;當時實力最強的“聯華”影片公司因戰火破壞而難以維持……
同時,《號外》專門闢“戰地日記”欄目,及時報道戰況。胡秋原還為《號外》寫了短評,籲請人們注意:日軍對於上海文化設施的狂轟濫炸,絕非偶然的或個別的行為,而是其企圖摧毀中國文化、奴役中國國民精神的總體陰謀的重要組成部分。
《抗日戰爭號外》極大地鼓舞了抗戰軍民計程車氣。戰鬥開始後第三天,宋慶齡偕同老友何香凝親往前線指揮部慰問。她們會晤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答應為眾多傷員提供有效的急救服務。而且宋慶齡做這方面的工作很有經驗,在上海醫務界還有很好的關係。她的兩位表兄弟牛惠生和牛惠霖是第一流的外科和內科醫生,他們都幫助她並動員同事們參加工作。
三
那時,由於許多抗日機關和國民黨的報紙,大都被當局封閉,沒有出刊,胡秋原、王禮錫主編的《號外》可謂一枝獨秀,在上海社會各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王禮錫在《戰時日記》中寫道,正當胡秋原與王禮錫白天到戰地採訪,晚上夜戰編排《號外》,連續出刊了五天《號外》之際,時任神州國光社印刷所校對的周立波,以印刷所罷工委員會委員長的身份,要求將《號外》交由他們主辦。(《讀書雜誌》1932年第二卷第4期,神州國光社1932年版)
周立波於1924年秋考入長沙省立第一中學,在師長王季範、徐特立等影響下,思想追求進步,喜愛新文學。大革命失敗後,輟學回縣在高小任教。1928年春隨叔父周起應來到上海,考入江灣勞動大學經濟系學習,參加革命互濟會活動。1930年春因思想激進散發傳單,被校方開除。不久返鄉,從事文學寫作和翻譯。他的叔父周起應1927年5月在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不久即因暑假回家而脫黨。次年,在上海大夏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畢業,同年冬留學日本。1930年回上海,參加中共領導下的中國左翼文藝運動,併成為青年骨幹,又將侄兒帶到上海。
叔侄倆在上海住在一起,周立波主要靠周起應介紹翻譯外國進步文學作品,寫點文章賺稿費維持生活。為減輕生活負擔,周立波拼命自修英文。立波聰慧、好學,很快掌握了翻譯技能,翻譯出版了《被開墾的處女地》等名著。1931年,經人介紹考進了神州國光社印刷所當校對,作為一名激進的革命青年,他暗中從事工人運動,並被工人推舉為罷工委員會委員長。
四
那時,上海文壇形成了左、右翼兩大陣營。國民黨的一些御用文人發起了一場“民族主義文學運動”,把黨派偏見帶入文壇,亮出了反共、反蘇、反對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旗幟,對革命文化進行瘋狂的“圍剿”。1930年3月2日,由共產黨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左聯”以魯迅為旗幟人物,在瞿秋白的領導下,由馮雪峰出任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對國民黨的“圍剿”進行了猛烈還擊,向國民黨政府爭取宣傳陣地。
由於左、右翼兩大陣營大都是奉行“非左即右”的思維定勢,他們均視超然於左、右之外的自由知識分子群體為敵人,將“自由人”和“第三種人”的代表人物胡秋原、王禮錫和蘇汶(杜衡)等列為打擊物件。針對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猖狂,魯迅於1931年10月23日,率先發表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命運》,尖銳地揭露與批判右翼之劣行。
以“自由人”自命的胡秋原,首先響應魯迅起而討伐民族主義文藝運動,他在《真理之檄》中明確指出,今後的文化運動在批判封建意識形態之殘骸與變種、批評各種帝國主義時代的意識形態的同時,“更必須徹底批判這思想界之武裝與法西斯蒂的傾向”,即民族主義文藝運動。按說,胡秋原的這篇文章,理應受到左翼陣營的歡迎。哪知,左聯的《文藝新聞》第45期卻發表文章《請脫棄“五四”的衣衫》,對《真理之檄》提出的繼承“五四”的反封建傳統的要求,進行吹毛求疵的挑剔。對於胡氏反對民族主義文藝運動這一戰鬥任務,則不置一詞。對於《阿狗文藝論》對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討伐,更是不屑一顧。繼而,胡秋原受到左、右翼兩個陣營的攻擊;一場沒有硝煙的戰鬥——“文藝自由論辯”,從1931年底持續到1933年初。
針對爭奪《號外》主導權事件,胡秋原與王禮錫以為,周立波是左聯骨幹周起應的代言人,他們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內應外合發難,自然斷然拒絕。周立波則認為自己是堅持左聯立場,立即組織印刷工人罷工,造成編輯好的《號外》不能如期印刷。勞資雙方就此產生了衝突。2月6日下午,周立波正在張貼罷工宣言時,被暗中監視的工頭抓住,一下子打落了眼鏡。年輕氣盛的周立波毫不示弱,揮舞拳頭與工頭對打,終因眼睛近視、寡不敵眾,被工頭扭送到巡捕房拘留,擬於三天後轉至上海提籃橋監獄。
胡秋原曾在《中華雜誌》1982年11號上的《論魯迅並說周揚》一文回憶:得知侄兒一行被捕後,周起應因曾與胡秋原有一面之緣,即代表親屬與左聯前去找胡交涉,希望“神州”能夠出面保釋侄兒與工人。按說,此時雙方各退一步,周立波可免除牢獄之災,罷工風波即可平息,《號外》可繼續出版。可是,正在氣頭上的胡秋原認為,如果周氏叔侄同他光明正大地協商合作辦報,此事尚有調停餘地。而周起應作為印刷所罷工委員會的“總後臺”,他們叔侄串通一氣,分明是在給自己下套、耍陰謀,此事沒得談!遂當面拒絕了周起應的要求。
周起應對胡秋原如此無情十分氣憤,拂袖而去,雙方從此結下樑子。而風行幾天的《號外》,也就此流產了。沒辦法,周起應只好找律師為周立波辯護。請辯護律師要花很多錢,周起應為此東挪西借花了三四十塊光洋,對旅居上海的他來說,這是一筆鉅款了。潘震亞是有名的紅色律師,儘管他義正詞嚴進行辯護,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周立波還是被判了兩年半徒刑。周立波被判刑那天,周起應很難過,從法庭出來後沒有回家,而是沿著黃浦江畔走了一夜,以平復心情。
《號外》停刊後,為了集合力量抗日,胡秋原與王禮錫分頭聯絡上海著作界,並於2月7日集會,發起成立了“中國著作者抗日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