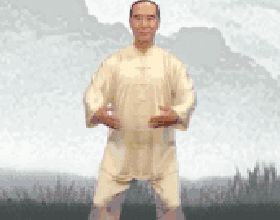九一八東北淪陷始末(十一)
從1928年12月至1929年7月,因為得到了錯誤的情報,張學良採取了對蘇強硬政策,試圖強行收回中東路,這自然引起了蘇聯方面的強烈不滿。不過由於蘇聯在前期採取了步步退讓的做法,導致蔣張的態度愈發強硬起來。
這自然讓蘇聯方面大為惱火,終於蘇聯決定採取斷交措施,直接召回了駐華使節、商務代表以及中東鐵路的蘇方人員,並且斷絕鐵路交通,同時要求中國駐蘇使節離開蘇聯。而向來對外軟弱的南京國府,卻將此誤判成對方不會動手的標誌。蔣張這兩位新科兄弟如同乳虎嘯谷一般,在國際社會上表演了一回什麼是“初生牛犢不怕熊”。
一、蘇聯前期多次進行了退讓
和當時很多欺負中國的列強不同,蘇聯對於中國方面強硬收回中東路的行為,在一開始是採取了忍讓和剋制態度的。這就使中國方面做出了嚴重的誤判,以為蘇聯真的是虛弱無比,反而變本加厲起來。
東北當局首先是在1928年12月24日,派人當局強行接收了中東路電話局,當時蘇方未作出反應。後來又強制接收了文物研究會和哈爾濱氣象臺,也沒有遇到多大阻礙。據張國忱回憶:
我一到廳,就向廳內負責人員表示,堅決執行奉蘇協定,接收文物研究會和氣象臺,希望蒐集材料,供給意見,當有廳內原有白俄督學們自告奮勇,去摸索文物研究會內部情況回覆後,請準上級,屆時由翻譯人員偕警察,到會宣讀了上級命令,經該會蘇聯領導人請示了他的上級後,所有蘇籍員工均皆退出,於是安然無事地把哈爾濱文物研究會給接收過來。
看到蘇聯人不反抗,東北各部門爭先效仿。當時東三省電政監督蔣斌不甘落後,亦請準張學良把自動電話局接收過來。隨後教育廳也跟著摻合,驅逐了教育廳的蘇聯科長菲利博維赤出境……一時間東北掀起了“驅蘇”的高潮,各部門紛紛驅逐蘇方人員。曾任東鐵理事會職員的王澤久回憶說:
“東鐵蘇方負責人員對此並無反應。代表蘇方權益的蘇方理事們,態度也比較和緩。我方遂又另提出些要求,如東鐵路款一向存在蘇方遠東銀行的,要求改為存在遠東銀行和中國銀行各一半。東省特別區教育經費,得由東鐵提供,在我方的壓力下,蘇方也忍讓照辦。這給蔣、張和東鐵造成了假象,竟真相信蘇方軟弱可欺。”
可以說,如果把事情分成一步步來,在這個時候見好就收,那是很可能兵不血刃地收回部分權益的。但是因為進展順利,就讓東北當局進一步誤判了形勢。在1929年3月1日,張學良又命令中東路督辦呂榮寰,要他向中東路蘇方副理事長齊爾金提出收回在中東路應得權益等要求,然後不出意外地被蘇方所拒絕。5月27日,哈爾濱特區警察管理處處長米春霖又搞出了大事,他使用金錢、利用白俄督察、買通某些歹人竊取的情報搜查了領事館,逮捕了蘇方總領事以下官員39人。這一下子,徹底把毛子惹毛了。
這就好比班裡有個窮孩子,強壯些的同學經常對他非打即罵,沒事就欺負他一回。這時候突然有個強壯同學和他講道理,這反而會讓他無所適從,以為這個同學是家裡出了事,可以反過來看看能不能佔到便宜了——1962年的印度和1979年的越南,估計就是這個心理。如果在一開始就採取堅決反擊的態度,把每次挑釁都堅決打回去,是可以像前段時間對印那樣,避免最後的大規模衝突的。
二、老蔣慫恿小張動手並承諾援助
而既然小張這個小弟衝在前面,而且取得了不少進展,老蔣這個大哥自然也不能處於下風。當時的南京國府不僅對東北當局的做法加以限制,而且還大加讚賞。1929年7月5日,蔣介石電張學良,謂堅決收回中東路主權,不得已時可絕交,並囑東北邊境戒嚴。
7月9日下午,蔣介石、張學良進行了會見,達成了協調一致行動的意向。然後把兄弟二人在北平西山又和閻錫山等舉行正式會議,議定在統一之後,地方應服從中央政府,但需分片負責,東南由蔣兼領,東北責成張學良負責,西北責成閻錫山負責——也就是說,各大軍閥瓜分了自己的勢力範圍,成為自己地盤的霸主。而除此之外的外交問題,則不可擅作主張,應與中央協商解決。當時三方達成的一個重要意向,就是東北外交上要對蘇應取強硬態度,由張學良負責辦理,具體方案與外交部長王正廷協商。
到了7月10日下午,蔣、閻、張等與剛抵北平的外長王正廷、亞洲司長周龍光、駐蘇代辦朱紹陽舉行會議,蔣介石在會上以最高領導的身份表明態度,主張對蘇取強硬態度,武力接管中東路,甚至為此付出與蘇聯斷交的代價也在所不惜。
為了慫恿張少帥出手,老蔣還大開空頭支票,承諾一旦中蘇開戰的話,他撥幾百萬現大洋的軍費,並且可以出兵10萬——當然了,當時北方是馮玉祥和閻錫山的地盤,老蔣的部隊是不可能繞過他們開往東北的,因此這只是紅口白牙說白話而已。而且即使閻錫山真的“深明大義”,允許蔣軍“借道”,那也可以趁機搞個“假途滅虢”之計。最後如果蔣軍能夠藉機開入東北,那不僅能夠消除蘇方威脅,而且還能賴在東北不走,可謂是一石二鳥之計。這老蔣可真的不愧是老謀深算之徒。
國民政府的這種態度,自然是觸及到了北極熊的底線。蘇方於7月18日宣佈斷絕中蘇關係,召回蘇聯在華人員,請中國駐蘇使、領人員迅速離境。並宣告保留1924年“北京、奉天中俄協定之一切權利。”
而直到7月18日下午,蘇方絕交照會到南京後,蔣介石仍然沒有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決定對蘇來照不予答覆,準備發表宣言,請各國主持公道,並公佈前從哈爾濱蘇領事館所獲之檔案——從歷史來看,每次北極熊的咆哮似乎都得不到對方的退讓,而只有熊爪揮到身上,才會讓人真的知道疼。
三、蔣介石的真實居心
如果說當時張學良一味對蘇強硬,是有點“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意思,在錯誤的情報下誤判了形勢,那老蔣作為一個老謀深算的政治家,而且是受蘇聯支援上臺的。他應該是深知蘇聯實力,和蘇聯人底線的。那麼他這一味地打了雞血,不停鼓動小張往上衝那就有點耐人尋味了。在這方面,其實當時的人就有分析。
時任東北當局顧問顧維鈞的回憶錄稱:“很可能張之所以捲入對俄問題乃是南京對付不聽號令的所謂四大集團軍的不同戰略的一部分”,即以財政手段對付馮玉祥,政治手段對付閻錫山,軍事手段對付李宗仁,外交手段對付張學良。
馮玉祥缺錢,就在軍費上卡他。閻錫山好名,就用政治上的頭銜穩住他。桂系實力最弱,那就直接派兵武力鎮壓。而東北軍財雄勢大武器先進,那就利用他們深處蘇日夾縫之中的機會,挑撥外國人對付他。
顧維鈞先生是民國著名外交家,對國際形勢是洞若觀火,對老蔣又非常瞭解。他的分析自然是入木三分,對局勢的把控精準無比。當然了,要說老蔣是有意推東北軍入火坑,那也是過於陰謀論了。當時五大軍閥之中馮閻桂隱隱結盟,只有奉系還是可爭取的盟友,在可能的情況下,老蔣還是希望能夠順利收回中東鐵路的。所以在中東路事件中,老蔣只是煽風點火順水推舟而已,更何況老蔣的判斷是蘇聯人未必敢打:
“詳察牒文末句,有蘇俄政府宣告保留1924年中俄所訂協定之權利一語,是其意在保守,或不敢用兵……”
當時國府高層對列強的無知,由此也可見一斑了——毛熊那也是國際知名扛把子,要是被小小的中國人駁了麵皮,那以後還怎麼在場子上混?怎麼在小弟面前耍老大的威風?
而在另一方面,顧維鈞先生也分析了萬一開戰的可能:“政府打算把少帥誘入圈套,因為少帥妄自尊大又無外交經驗;吳鐵城、張群甚至李石曾可能設法使他陷於對俄的困境,使之必須依賴南京,這樣中央政府就能控制他了。”
這東北軍實力太強,如果說真的被俄國人教訓一通,損兵折將之後更有利於被自己控制,這恐怕也是老蔣的真實想法。說句最白的話,那就是打死俄國人除外患,打死東北軍除內亂。在挑動別人消耗實力方面,老蔣從來是不遺餘力的。
四、中東路事件的惡劣後果
當然了,老蔣和小張進行的這次軍事冒險,毫無疑問會受到重擊。1929年10月2日,蘇軍炮兵、騎兵和坦克在飛機掩護下,猛攻東北軍滿洲里陣地。戰爭正式打響。幾個月後原本被寄予厚望的東北軍就連連潰敗,被打的抬不起頭來。戰爭的細節我們在這裡就不復述了,只說一下此戰造成的幾大不良後果:
1.東北軍內部大分裂
當時少帥本就上臺不久,又因為年輕識淺導致諸將不服。其後擅殺了楊宇霆、常蔭槐更是搞得人心惶惶。如今初出茅廬第一戰,就被人打得灰頭土臉,諸將更是不服。自那以後是各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盤,元老派、士官派、講武堂派、滿人復辟派的鬥爭更為激烈。而在見識到蘇軍的威風以後,有不少軍官對自己失去了信心,認為只能“以夷制夷”,借東洋人的力量來對付西邊來的毛子。所以當時在東北出現了很奇特的現象,對日本人有國恨家仇的少帥麾下,卻有很大一部分軍官傾向於日本。當時不僅東北軍內部有不少親日派,東三省兵工廠的生產被日本人把持,就連東北空軍都被日本人控制。
2.東北軍上下都對南京國府寒了心
在東北易幟歸順南京的時候,其實東北軍內部就有不少反對之聲,只是被“楊常而去”事件震懾住了而已。老蔣這次在事前大加慫恿,並且開了大量空頭支票。結果真打起來的時候,那是沒派一兵一卒一毛錢,坐看東北軍打生打死。自此之後,東北軍諸將就對老蔣寒了心,認為他純粹就是個大忽悠。而這也是後來九一八事變以後,東北軍面對打過來的日本人,抵抗並不積極的原因之一。
3.失去了日蘇之間的制衡
東北原來是日蘇兩家對峙的局面。中東路事件的另一後果,是讓日蘇之間失去了制衡。本來能夠讓日本人有所顧忌的蘇聯人,因為中蘇交惡已經不可能出手。甚至原本在爭奪東北上利益對立的日蘇雙方,會在中國有意收回權益的時候進行聯手。本來是俄國熊和日本狼互相牽制,如今是狼熊聯手而自己又在內鬥,這怎麼搞得定嘛!
4.在國際社會造成了惡劣影響
而在國際形勢上,中東路事件也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張學良、蔣介石悍然撕毀條約動用武力,讓當時和中國都有不平等條約,而且遵守華盛頓體系的列強全部站在了蘇聯一邊。感同身受之下,當時的國際輿論是一面倒地抨擊中方。
而在九一八事變時,日本關東軍就特意設計了栽贓中國軍隊炸燬日本南滿鐵路這一安排,就是想把九一八事變打扮成中東路事件的翻版,使世界輿論認為是中方再次撕毀條約武力收回鐵路,以欺騙國際輿論。不得不說鬼子的這個詭計,在執行上是獲得了非常成功效果的。
5.嚴重打擊了蔣張的對外信心
在發動中東路事件之初,蔣介石和張學良都是自信滿滿,自以為憑著自己的幾十萬大軍和先進武器,加上蘇聯人內部問題不斷,是很有可能勝利的。但是事實卻嚴重打擊了他們的信心,讓他們從“對外打雞血”的亢奮狀態,一下子變成了“對外必敗”的失敗主義者。
而從那以後,不僅本來就有“恐日症”、在濟南事件中慫得不如狗的老蔣症狀加重,就連這之前自信滿滿的熱血青年張少帥,也是被打出了嚴重後遺症。中東路的慘敗讓他們嚇破了膽,從此以後,對外要“避免衝突”,就成了整個國府高層的共識。再後來,“避免衝突”就變成了“不抵抗”,一步步釀成了九一八事變的惡果。
勿忘國恥,治史銘記!
參考資料:
《論1929年中東路事件的發動》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張學良與東北軍》
《1929年中東路事件內幕》,
《東北王張作霖》
《張學良傳》
《張學良年譜》
《二戰步兵戰術》
《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
《九一八後國難痛史》
《中國近代兵工史》
《關東軍》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