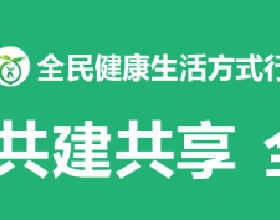患者李先生,50歲。素有肝炎及胃竇炎病史多年,中脘痞脹,形寒便溏,面色淡白少華,肢軟乏力,脈細,舌淡苔薄膩,投平胃散加減無效。處方:升麻,半夏,佛手,沉香曲,陳皮,枳殼,大腹皮,婆羅子,香櫞皮,蒼朮,白朮。7付。二診時藥後腹脹已消,諸症遂減,再以升清降濁,鼓舞中州,升麻重用,續進7劑,諸症皆除。
此例重在脾陽不升,清濁升降失常,津液不得正常疏布,在脾不在胃,所以平胃散無效。用升麻以昇陽;蒼朮、白朮健脾燥溼;半夏、陳皮以祛痰;香櫞皮、大腹皮、佛手乃清靈之品,善疏肝理氣,消脹除滿。
將風藥運用到調理脾胃,李東垣可謂發揮得淋漓盡致,驗證於臨床中,則是要注重升清陽。《脾胃論》曰:“脾胃不足之證,須用升麻、柴胡苦平之薄者,陰中之陽,引脾胃中陽氣行於陽道及諸經”,脾宜升則健,喜燥惡溼。但最易感溼,用風藥則能勝溼,振奮脾氣;而且土得木而達,借風藥之升散,應肝木條達之性,發揮正常疏洩功能。《素問·經脈別論》雲:“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若脾虛溼困,則不能散精,出現清濁升降失常的現象,或頭暈,或洩瀉。
東垣認為“諸風之藥,皆辛溫,上通天氣”,“味之薄者,諸風藥是也,此助春夏之升浮者也”。所以升清陽是治療洩瀉的一重要方法。如痛瀉藥方,是治療清晨痛則瀉,瀉後痛減的方。清晨乃肝升發之時,用白芍養肝之陰,防風助肝升發,使脾氣健運,陳皮、白朮健脾,所以我認為與其說是“培土瀉木”不如說是助肝升、健脾運以止瀉。
(常見證候)
水飲內停大便溏:大便稀薄如水樣,伴腹中腸鳴,有振水聲,或口渴不欲飲,口中涎唾,嘔惡,舌淡紅苔滑,脈弦滑。
脾胃氣虛大便溏:大便稀薄不成形,食後即欲大便,脘腹痞滿,納可,疲倦乏力,舌淡苔白,脈沉細。
中氣下陷大便溏:大便稀薄,四肢欠溫,舌淡苔白,脈細弱。
腎陽衰微大便溏:大便稀薄,白,脈沉細。
(鑑別分析)
或有下墜不舒感,兼見面色觥白,氣短語怯,脫肛甚時下利清谷,畏寒肢冷,汗出,小便清長,舌淡苔水飲內停大便溏:水液的飲入、輸布、排洩的代謝過程,由肺脾腎三髒共同完成。
而肺失宣降,脾失運化,腎失氣化,則水液代謝障礙,失於敷布,不能營養五臟六腑,而鹹水飲留滯胃腸,順勢趨下而致便諧。(索閹·經脈別論);“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臟明陽,撰度以為常也。”
病屬本虛標實,肺脾腎虛弱,功能失調為本,水飲中阻為標,以標為主,治宜化飲和胃,方選苓桂術甘湯。
脾胃氣虛大便溏與中氣下蹈大便搪:脾胃為後天之本,主運化水溼,脾主升則清陽發腠理,實五臟,胃主降則濁陰下腸遭,通六腑。脾胃乃氣機升降之樞紐,關係到氣血、陰陽、津藏、水谷精微的敷布與代謝。而脾胃之氣又稱為中氣,脾胃虛弱,運化失職致水溼內停而下利腸道則便溏。因此,脾胃虛弱大便溏與中氣下陷大便搪臨床表現相近,除大便稀薄外,常見疲倦乏力,少氣懶言之症。而中氣下陷大便塘又兼見大便下墜不暢,脫肛,四肢欠溫等症,可資鑑別。(夏樞·口同):“中氣不足,溲便為之變,腑為之苦鳴。”
前者治以健脾和胃,方選參苓白朮丸,後者治以樸中益氣,方選補中益氣丸。
腎陽衰徽大便溏:腎為先天之本,主水液氣化,又司二陰。因此,腎陽不足、命門火衰則不能氣化水藏,溫煦脾陽,充養後天,厚腸道,司二陰,故見大便稀薄,甚則完谷不化,下利清谷,較之脾胃虛弱大便溏,病位深,病情重。治以溫腎健脾為主,方選四神丸合理中丸加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