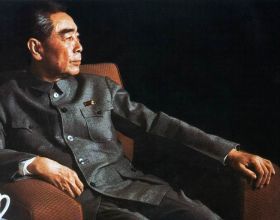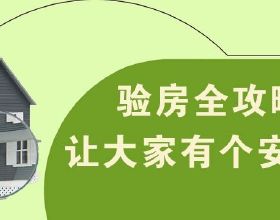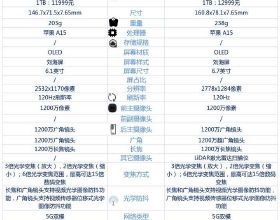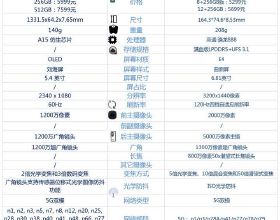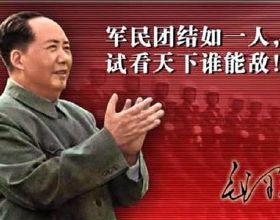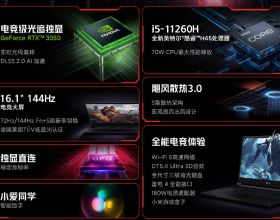美國曾經做過一個調研,90%的人認為自己的智商在平均水平之上。這顯然不符合實際。即使從經驗看也可以知道,智商的分佈應該是一個正態分佈,極端聰明的和極端不聰明的都是少數,絕大多數人都在平均值上下。
自我感覺良好的現象不光美國有,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也常見。比如在幹部提拔的時候,很多人覺得自己素質足夠優秀,成績足夠大,比某某要強得多。如果被提拔了,那是早就應該。如果沒有被提拔,可能就是懷才不遇,或者是因為沒有背景,或者是組織不公平。再比如人們和自己的親朋好友知己聊天的時候,自覺不自覺地會對別人品頭論足一番,上至王侯將相、偉人賢達,下至販夫走卒、平頭百姓,好像自己也可以和偉人比肩,彷彿世界就是以自己為中心。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
首先,有一個認識的角度問題。再聰明智慧的人,後腦勺上也沒有眼睛。柔韌性再好的人,脖子也不能轉360度。即使身體轉360度,也依然存在著看不見的盲區,或者看見了新的區域,又造成了新的盲區。人對自己的認識也同樣如此。別人都在自己眼裡,別人和別人的比較也在自己眼裡,但是自己不在自己眼裡,自己對自己的認識往往是透過反觀內心來實現的,透過別人對自己的反應來實現。人們常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於角度引起的。
其次,有個人對自我認知的態度問題。
魯迅先生就說過:“我確實不時解剖別人,但更無情地解剖自己。"有的人像魯迅先生一樣,經常無情反思自我,所謂一日三省乎己。但有的人從來是隻做手電筒,只照別人不照自己。有的人對自己比較寬容,有的人對自己比較嚴格,但律己寬、律人嚴的情況多於律人寬、律己嚴。極端的一些人把自己的缺點錯誤看成芝麻一般,而對別人的錯誤和不足往往看得比磨盤還大,甚至上綱上線。這種態度很難客觀地認識自己。
其三,有自我認知的能力水平問題。人的文化、閱歷、知識、經驗、視野等因素,都會影響一個人的自我認知能力。人們在上述方面的不同,也造成了自我認知能力的不同。某種意義上,認知外部客觀世界的能力和自我認知能力有比較緊密的關聯性。總體來說,一個人認知客觀世界的能力越強,認知自我的能力也就越強,但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的情況也是有的。
其四,和我們的文化有關係。我們的傳統文化有為尊者諱的特點,也有為人前諱的特點,或者叫做戴高帽文化。當然,這種文化在西方也是存在的。人們出於與人為善的動機,或者出於人情世故,在人面前的時候,總是傾向於說人的優點和好處。這樣做當然不完全是消極的,畢竟或多或少給人正能量。但是當事者應當清楚,別人除了有當面說的話,也許還有背後說的話,當面的話和背後的話未必一樣。除了當面說話的人,也還有沒有說話的人,他們不說,不等於沒有看法,而且往往因為有看法,所以才不說。兼聽則明,不多聽聽不同人的看法,就做不到“明”。而對於當面誇獎的話,應該至少打一半的折,甚至打一折;而對批評的話,得放大三倍五倍乃至十倍來看待,可能才接近於客觀實際。
其五,和我們現在的生活環境有關。人們都是有圈子的,在同一個圈子裡的人價值觀大體是相同的。因此,一個人的觀點總是容易得到同一圈子裡人的點贊。如果換一個完全不同的圈子,情況可能完全不一樣。在社交媒體上,比如微信裡面,正在快速發生圈團化。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圈子也是一樣。你很可能已經被踢出了某些群,或者你們的群裡已經把某些人踢出去了。天長日久,你瞭解的所謂群眾的呼聲,社會的呼聲,很可能只是你圈子裡同一類人的呼聲。人生活在社會中,你對自我的認識,就是對客觀世界認識的一部分。對客觀世界認識的客觀性,影響著、制約著你對自我認識的客觀性。
此外,人的社會地位,往往也是影響人認知的一個重要因素。一般說來,一個人官越當越大,周邊讚美之聲就會越來越多,不要說對自我的認知會不準確,即便對於工作中的問題也往往不容易瞭解實際情況。但需要指出的是,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觀原因主要在於為政者本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愛細腰,宮中多餓死,自古就是這個道理。
某省公安廳常務副廳長寫了一本《平安經》,一時成為輿論的熱點。實話說,專業水平談不上。但從寫書的醞釀到出版、到輿論炒作,也並非一天就能完成,難道作者就沒有覺察自己的這本經很可能就是一個笑話嗎?難道他就沒有聽到一聲刺耳的話嗎?但很可能他早已經生活在一個資訊壁壘之中了。就像是網際網路上,某些演算法已經框定了你的愛好,給你傳送的資訊都是量身定做、投你所好的。你瞭解的所謂客觀情況其實已經是按照你的主觀愛好給你篩選過的。
自我認知很複雜,很重要,也很難,不可不察,但並非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觀。“兼聽則明,偏信則闇”,“一日三省乎己”,這些中國人民古老的格言,依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作者:祁金利,中共北京市委統一戰線工作部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