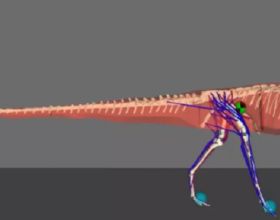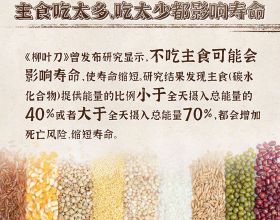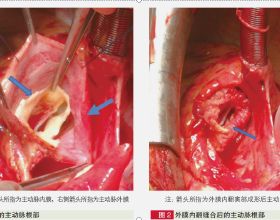1
我出生在河北省的一個小村莊。從我記事起,就感受著農村那種濃濃的人情味,誰家有事,鄉里鄉親的都會幫襯一把,左鄰右舍的關係處好了,比親戚都強,俗話不是說嘛,遠親不如近鄰。
我家左面鄰居是父子兩人。父親60多歲,性格木訥,不愛講話。是老實巴交的莊稼人。他有一兒一女,女兒出嫁了,父子倆過日子,兒子呢,只上過小學,沒文化,快三十歲的人了,說話做事從來不經過大腦,就是人們常說的“缺根弦”、“不著調”。
80年代,我們那兒有很多小型的琺琅廠,也就是景泰藍。景泰藍以紫銅作坯,製成各種造型,再用金線或銅絲掐成各種花,中充琺琅釉,要經過燒製、磨光、鍍金等多項工序製成。他在廠子裡做些雜活,冬天的早晨,天氣冷,不願起床,父親喊他起來上班,他去了迷迷糊糊開始打掃衛生,鍍金用的一桶鍍金液,他愣是當做髒水倒掉了,正好讓老闆看個正著。老闆制止也來不及了,便生氣的質問他:“你幹什麼?有沒有大腦啊?”他一時還沒明白怎麼回事,以為老闆問他冬天穿的棉襖,囁喏著:“沒有大襖,家裡有個小襖。”在我們老家的方言裡,腦與襖是同音的,這以後成了人們的笑柄,大家給他起個外號“小襖”。別看他智商不高,卻對電工技術情有獨鍾,電路、電器的簡易檢修他都很在行,誰家換個電燈、電線的,他都願意幫忙。我家和他家,七繞八繞的,還有親戚關係,按照輩分,我應該喊他爺爺,因為嫌他“缺心眼”,每次他到我家串門,我只是喊他一句“小爺爺”,就不再理他,也不給他好臉,他呢,沒心沒肺的,還是喜歡到我家串門。
我家右邊的鄰居是一個40多歲的中年男子,因為小時候調皮,從河邊的樹上往河裡“扎猛子”,結果不小心耳朵進了水,可能是得了中耳炎,家裡沒錢,延誤了醫治,最後耳朵有點聾,需要湊近他大聲和他講話才聽得見,大家都喊他“聾子”。他不種地,把地租出去,要些糧食,自己就是放羊,每天早晨趕著一群羊出去,晚上回來,羊少的時候,他就和羊在一間屋裡,羊多了,屋裡放不下了,才壘了一個羊圈,有的羊下了小羊,他還是把小羊放在屋裡,去過他的屋子人,都說屋裡有羊騷氣的味道,又髒又亂,後來,基本沒人去他的屋子。他愛看書,有一箱一箱的小人書,還有很多厚厚的類似於《苦菜花》、《林海雪原》《野火春風斗古城》之類的書。我小時候去過一次他的屋子借書,一進屋,亂七八糟的,說不上什麼氣味,撞得我頭疼,從此再沒去過,他也並不希望我去,每次看完了書,他就拿回去,換一些給我。父親也喜歡看書買書,他也總是來借,喜歡和父親探討,說話有板有眼,愛講大道理,因為他留了八字鬍,身體瘦長,我背地裡喊他“老夫子”。父親和母親可憐他一個人,對他總會多些照顧,有了好吃的總會讓我拿一些給他,冬天母親還幫他做身棉衣。他知道感恩,我家有什麼活計,總是過來幫忙。
2
這兩個人家裡都很窮,自身條件又這麼差,自然沒有人上門提親,也許這兩個人一輩子也找不到媳婦,甚至今生與女人無緣,可是,生活就是這樣充滿著偶然,每一個偶然也許都會在生命裡留下最難忘的記憶。
1989年秋天,“小襖”的父親因病過世,剩下他一個人,越發的不知道怎麼過日子了,整天閒的昏天黑地,什麼工作也幹不長,他姐夫是搞裝修的,也是嫌這個小舅子不著調,不用他,他姐姐也心疼他,好說歹說,最後姐夫沒辦法,就帶著他,看他還有電工的技術,就讓他做些接線之類的工作,他對姐夫倒是很害怕,小心翼翼的幹活,一個月竟掙了1500元,那時在我們農村,這可不是小數目了,我那時17歲,高中沒考上,在村裡任代課教師,一個月才60元。“小襖”神氣了,發了工資,就到我家串門,一進門大聲說:“侄媳婦,你猜,我這個月掙了多少錢?”媽媽說:“掙錢多了自己攢著點,等回頭娶個媳婦。”他嘿嘿笑著,“一個月1500,兩個月3000,錢多了,我先蓋房子”。說完興高采烈的走了。後來一段日子,我就總見村裡的一個小媳婦,妖豔的,花枝招展的總往“小襖”家裡去。人們風言風語的,說那是個“破鞋”,“破鞋”是對女人最具侮辱性的髒話,指亂搞男女關係的女人,農村的女人們,最恨的就是這種放蕩、不檢點的女人,一旦有了上嘴的物件,大家會堅決的反覆的使用它。我起初還將信將疑,“小襖”雖然不著調,到還不止於亂搞吧,後來,看見過他買女式的新頭巾、新衣服,還以為給他姐姐買的,過不了幾日,那新衣服、新頭巾就穿在了那女子身上,我是徹底的對“小襖”嗤之以鼻,再來我家理也不理了。忽一日,“小襖”急急忙忙跑來,跟我媽媽說他放在櫃子的3000元錢丟了,媽媽問,“最近誰上你家去了,誰知道你的錢放在櫃子裡?”。我心裡瞬間明白了,小襖也回過神來,但也沒有證據,也就作罷了。沒幾日,那女子竟暴病身亡了,大家一是忌諱她年輕,二是又是個傷風敗俗的“破鞋”。只說是爐灶的灰可以辟邪,就都掏出來,灑在屋門口,竟看見“小襖”圍著他的房子撒了一圈,大家心裡暗笑。
有一天,我晚上回家晚,見“小襖”拉著窗簾,屋裡各種顏色的彩燈一明一暗,他在窗前一扭一擺的,跳著奇怪的舞,窗簾上映著他拉長的影子,像個鬼魅。
這個秋天,“聾子”也領回一個女人。那天,“聾子”帶那個女人到我家幫著剝玉米皮,那女子身材高挑,面板黝黑,眼窩深陷,鼻子高挺,一看就不像當地的女子。“聾子”說,他早晨放羊,見這個女子穿的破破爛爛,坐在路邊,看樣子快暈了,問她話,也聽不懂,他就把他撿回來了。我削了一個蘋果給她吃,她先看看“聾子”,“聾子”點點頭,她才接過來吃。我問她話,她嘴裡嘀咕著,也聽不懂說的什麼。“聾子”對這個女人照顧的很仔細,給她買新衣服、做好吃的,一個月下來,那女子面色紅潤起來,村裡的人們有的跟“聾子”開玩笑,“聾子,你有媳婦了,晚上摟著睡吧,多美啊”,隨即哈哈壞笑著,“聾子”紅了臉,嘟嚷著,“還不行,她身子虛著呢,養胖了再說,養胖了再說。”“聾子”有一天帶著她到我家串門,拿了一張小紙條,上面寫著幾行類似於符號的文字,“聾子”說:“我覺得這像朝鮮族的文字,你幫我看看,要不你幫我問問別的老師有認識的嗎?”。我拿過來,左看右看,看不懂,隨手遞給他說:“這沒人看得懂”。
沒過幾日,那女人失蹤了,整整三天,聾子走遍了四周的村子尋找,沒有找到,最後他只是說“希望他遇到了好人,別凍壞了”。從此看他,越發的孤單了。
3
後來,“小襖”在姐夫的裝修隊也不好好幹了,氣的姐姐、姐夫也不管他了,他又開始過混一天算一天的日子;“聾子”依舊放著他的羊,早出晚歸。再後來,我嫁到了天津,斷斷續續的從媽媽那兒聽到他們的訊息,聽說“聾子”生病了,也不放羊了。“小襖”每天就是打零工,有錢就換手機,幾乎每個月就換一個。有次回老家,我看見“聾子”了,病怏怏的,說話有氣無力。一晃幾年過去了,去年冬天,媽媽打電話說“聾子”死了。說他病重的時候,每天就是出來買一天的饅頭,就不再出屋,有一天沒有去買,小賣店的人覺得不好,去敲門,他已經死在屋裡了。因為沒有親人,父親和村裡的人幫助料理了後事,父親拿回幾本他的書作紀念。我心裡很不是滋味,覺得他的一生很淒涼,但是誰知道呢,也許在他心裡,曾有一個女子讓他有了溫暖和牽掛,也就足夠了。
近日回老家,“小襖”來串門,明顯的老了,還是一副嬉皮笑臉的樣子,說:“你看看,我又換了手機,大屏的,你說,我是不是比我爸那時強多了。”我氣了,脫口而說:“你爸還有你呢,你有什麼。”他不言聲,眨巴眨巴眼睛,也不知聽沒聽懂,悻悻的走了。看著他的背影,覺得他又可氣又可憐。
我翻看爸爸拿回來的“聾子”的書時,發現了他曾給過我的那張紙條,紙條都泛黃了,字跡模糊,透過上網查詢,那的確是朝鮮族的文字,也許當時那女人想起了什麼,寫的是她記憶裡零散的片段。她因何流落至此,不得而知,也許她走了,就是要去找回家的路。後來,我一直在想,如果當初我能夠幫“聾子”問問別的老師,多方查詢一下,寫的什麼,然後留住她,問清楚一些,事情會不會變成另一個樣子?這個問題讓我感到很累,現在,看見這張紙條,我心裡依然感到非常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