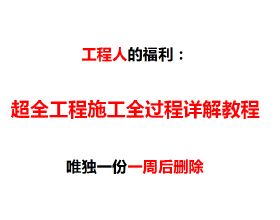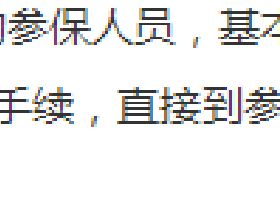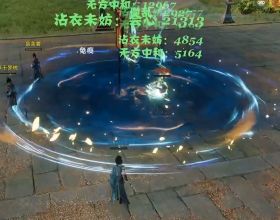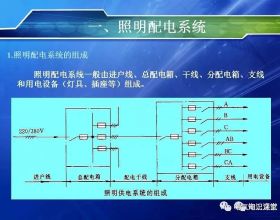工作氣壓(或氣體分壓)是濺射鍍膜中最重要的引數之一。沉積速率、均勻性、粒子能量以及殘餘應力都受到工作氣壓的影響。其原因是氣體分壓直接影響濺射粒子以及背反射粒子的輸運過程。粒子輸運過程非常關鍵且複雜,可以採用蒙特卡洛模型模擬輸運過程中粒子的運動方式、粒子能量、角分佈以及沉積均勻性。
首先,工作氣壓顯著影響沉積速率。Nakano 等發現直流濺射 Al、Cu、Mo 時沉積速率隨工作氣壓增加而增大,到1Pa達到最大值,超過1Pa後濺射速率反而下降。沉積速率受限於氣體分壓的原因是∶①濺射靶流改變;②熱電離區域分佈改變。假設靶材的有效電流密度為j,則j=ne·q·v,其中ne為電子濃度,q為電荷,v為電子速率。氣體分壓增加會提高電子濃度,從而提高原子離化率。原子離化率提高,會增加刻蝕速率和沉積速率。當濺射原子與環境氣體分子碰撞頻率增大到一定程度後,會導致濺射沉積速率發生轉變。該轉變點與靶材原子質量有關。原子質量之所以影響沉積速率轉變點,原因在於原子質量決定了熱電離發生之前的原子運動距離。熱電離是指等離子體中濺射原子與反射 Ar 離子透過碰撞達到執平衡的狀態。熱電離距離與靶材原子質量成正比。當氣壓較低時,大部分濺射原子都可以攜帶足夠高的能量達到基材表面,沉積速率隨氣壓增加而增大;當氣壓增加時,濺射原子的碰撞平均自由程降低,這導致熱電離區域向靶材收斂,此時沉積速率達到最大值並開始降低。
濺射原子與氣體原子的碰撞也會影響殘餘應力。氣體分壓對殘餘應力的影響已得到廣泛而深入的研究。最早的工作是由 Hoffman 和 Thomton在19世紀 60年代開始的。他們研究了濺射薄膜的微觀結構以及殘餘應力的起源,發現殘餘應力強烈依賴於氣體分壓。低氣壓導致高殘餘壓應力(最高達2CPa),隨著氣壓的增加殘餘應力會向拉應力轉變。圖5-7中,由壓應力到拉應力的轉變是在非常窄的氣壓範圍迅速完成的。如果氣壓低於0.266Pa,將很難維持等離子體放電,膜內殘餘應力將很大,導致薄膜剝落,故沉積氣壓一般要高於0.266Pa;但如果大於1.33Pa,膜內將存在較大的殘餘拉應力。因此,知道壓-拉應力的轉變臨界點是非常必要的。
研究發現,該轉變臨界點受濺射系統配置、電流、電壓等引數的影響由於柱狀靶比平面靶電流增加更加顯著,這導致膜系在更低的氣壓發生壓一拉應力轉變。低氣壓時膜內殘餘壓應力可歸因於到達基體表面的原子和背反射中性氣體原子攜帶足夠高的動能。氣壓越低,轟擊效果越明顯,產生所謂的"原子噴丸"效應,原子在強烈的撞擊下偏離平衡位置並有可能發生級聯碰撞,最終導致一定體積範圍內的結構損傷。Hoffman和 Gaertner給出了令人信服的"原子噴丸"證據。他們測定了蒸發鉻(Cr)膜的內應力,發現其為殘餘拉應力。當在蒸鍍時輔以惰性氣體離子轟擊後,膜內形成壓應力,而且這種效應在低氣壓中非常明顯,這就表明濺射膜內的殘餘壓應力是以動量和能量驅動過程。從此角度看,高氣壓時沉積原子與環境氣體原子碰撞後能量損失,膜內出現殘餘拉應力也就不奇怪了。
氣壓越高,粒子流中的低能組分所佔比例越高,導致離子的能量和動量衰減。當粒子能量被氣體分子散射耗散,會發生熱電離過程。到達基材的粒子能量是由氣壓以及靶—基距離決定的。大多數的濺射系統中靶—基最小距離為5cm,故幾乎所有濺射及背反射粒子在,1Pa 以上時都會熱電離。濺射原子能量降低意味著到達基材表面的原子運動能力降低。
以上討論了濺射過程中壓—拉應力隨氣壓變化情況。實際中,不同的濺射方式下,氣壓對內應力的影響也會存在差異。Aissa研究了不同工作氣壓下直流磁控濺射(DC-MS)和高頻脈衝磁控濺射(HIPIMS)製備 AIN 薄膜的結構效能和殘餘應力變化,發現 HIPIMS製備薄膜更緻密,且殘餘應力隨氣壓增加而降低的幅度更加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