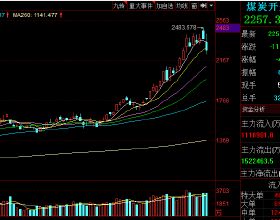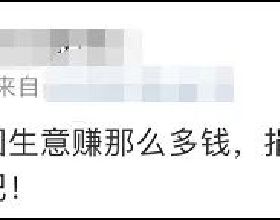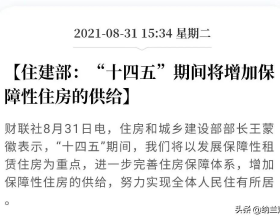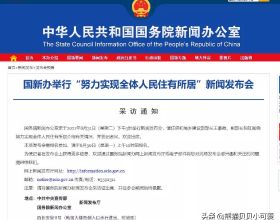我國作為十大文明古國之一,其歷史文化源遠流長,古往今來無數人都想揭開東方文明的神秘面紗,考古事業應運而生。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考古學更是進入了全新的發展階段。
雖然考古學家們有豐富的考古經驗,但並不意味著在每件文物出土時作出的判斷就是完全正確的,是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了解。
甘肅曾發掘了一處少數民族的古墓,當時的考古學家們認為裡面出土的文物都是些“爛大街”的貨色,沒想到這些文物在幾十年後竟被奉為國寶,引來無數人參觀。
多處發現少數民族墓群
我國一直以來都深受“祖先崇拜”和“入土為安”等傳統觀念的影響,致使人們格外看重人死後的葬身之所,而且其中還涵蓋些風水之說,所以也被稱為墓葬文化。
早在舊石器時代,人們用天然洞穴作為住所,自然也能用它作為安葬屍體的庇護所。如今位於北京周口店龍骨山的山洞頂人遺址,就是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主要墓葬代表。
而我國的墓葬文化自古以來就堅持著“事死如事生”的傳統觀念,也就是人死後,身邊的陪葬品必須是主人生前的物品,這樣的文化形式為考古學家們研究某段歷史時期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方向。
20世紀初,我國考古學家們在陝西太原境內發掘了隋代虞弘墓和北齊許顯秀墓,出土了大量的石質屏風和風格迥異的壁畫。
考古學家們對儲存其中完整的壁畫進行研究,發現上面竟然記錄著一個外來民族的日常生活起居。
與此同時,陝西西安也出現了北周康業墓和史君墓等多處少數民族的墓群,其中出土的文物中不止有石質屏風,還有石棺床。
兩地的考古學家們聯合推斷,這些應該屬於同一個外來民族——粟族的墓葬群。
這驚人的發現令全國的考古學家們振奮不已,有些專家還親自趕往挖掘現場,想要深入瞭解古人類的生活方式和墓葬習俗。
其中一位專家見到這些出土的石質屏風和石棺的第一眼,竟然莫名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他回去後仔細翻閱了自己曾參與過的文物發掘記錄簿,發現它們與30年前在甘肅境內出土的17件石質屏風的材質相同,圖案花紋也相似。
專家喃喃自語:“難道當初挖掘的那個古墓,是屬於粟族人的墓葬嗎?”他不敢細想,決定對當時出土的石質屏風再進行研究。
專家立即趕到存放出土文物的甘肅省天水市博物館,將自己的推斷告訴館長。館長不可思議地對專家說:“按你這樣說,那我們可就犯大錯了。”
原來,當年那處古墓中出土的所有文物不僅沒有在公開區域展覽過,甚至都沒有進行相關的保護措施,就被工作人員扔進了地下室。
專家稱:“無論如何,都要把它們找出來。”之後,博物館的工作人員連忙整理了堆積在地下室裡的雜物,將17塊石質屏風翻找了出來。
專家們將這些石質屏風與之前拍攝的粟族人墓中出土的石質屏風的照片進行比對,基本確定了這些石質屏風就是少數民族——粟族人的墓葬品。
但它們遺落在地下室的時間太長,石屏風表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損傷,上面的壁畫全都模糊不清,根本推斷不出是哪個時期的。
博物館館長得知後,立即派專人對這些文物進行修復,耗時兩年才完成。
國家文物鑑定會專家們第一時間對這些石質屏風們進行研究,最終確認了它們是隋唐時期的粟族人貴族墓葬品,並將其認定為一級甲等文物,也就是所謂的國寶級文物。
石質屏風上還原出來的壁畫不僅具有非常高的考古價值,還對研究粟族的生活習慣、文化習俗和宗教信仰具有非常高的研究意義。
但如果可以早點發現這些石質屏風上的資訊,或許我國對於少數民族的研究可以少走些彎路。
而這一重大失誤,令所有考古學家們既震驚又懊惱,因為當時人員的判斷失誤,導致沒能更早發現粟族人珍貴的生活軌跡,而且對文物也造成了一些不可逆的損失。
比如,1961年秦兵馬俑被發現時,由於當時的考古專家經驗不足,導致第一批被發現的兵馬俑剛出土就被氧化,沒有了光澤的表面,後期也無法進行修復。
隨著全國各地發掘工作的開展,考古學家們逐漸弄明白了粟特人的生活時期和文化習俗,並在《魏書》《隋書》等大量史料中發現了有關粟特人的相關記載。
少數民族發展史
粟特族是一個非常古老的民族,最早生活在中亞阿姆河和錫爾河附近,有人說他們是伊朗系統的中亞古族,也有人認為他們是中亞康居國的後裔。
粟族人作為中亞大陸上一個小型群居生活的民族,在一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一直飽受著周圍政權的壓迫和奴役,直到絲綢之路的出現,才徹底改變這一少數民族的生存現狀。
因為粟特族部分族人生活在絲綢之路的附近,所以他們的族群自然而然地成為了重要的中轉站,而粟特人為了獲取更多的利益,也漸漸參與在絲綢之路的貿易中。
他們不僅在絲綢之路沿線尋找地方定居,還擴張了更多的商業網路,企圖控制絲綢之路的中轉貿易權,以求完全壟斷絲綢之路的貿易。
漢朝時期,粟特人遷移到了我國新疆和甘肅一帶,開始了長期的定居生活,將粟特族的文化風格與中原文化進行了融合。
隋唐末期,又有一大批粟特人沿絲綢之路來到了中國的內陸地區,他們逐漸融入了當地的居民生活,娶妻生子,世世代代地生活在這裡,所以我國很多地方才會陸續出現粟特人的墓葬。
像江蘇、遼寧、江南等地都曾發現過粟特人生活過的足跡,而隨後發掘出來的少數民族墓葬群也成為了寶貴的歷史證據。
當初被擱在地下室“吃灰”的17塊石質屏風是如何被髮掘出來的?又為何沒能受到考古學家的重視呢?
盜墓賊猖獗,出土文物有限
1982年,甘肅省天水市石馬坪的一處山丘上,一支施工隊正在修建水利工程,工人們鉚足了勁幹活,只為早日完成任務。
突然,一名工人發出了驚呼聲:“這是什麼東西?”眾人紛紛聚集過來,看見下方土地上出現了一行青磚,他們徒手挖開後,發現下面有一個深坑,周圍還有雕刻精美的磚石。
當時國家大搞建設,各地曾出現過文物遺蹟,工人們紛紛猜測這會不會是個古墓啊!
工地領導聞訊而來,迅速將現場保護了起來,並上報給了市博物館。
很快,博物館派出考古隊趕到了現場,為了避免損壞珍貴文物,對這座古墓進行搶救性挖掘
所謂搶救性挖掘,主要是因為某些基建工程的需要,不得不對文物遺址進行清理,這也屬於被動型挖掘。
而我國在一般情況下,是不允許主動性挖掘的,一方面是因為相關專業知識和技術有限,容易對文物遺址和遺蹟造成損傷,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給子孫後代們留點東西。
經過幾天時間的挖掘後,古墓的概貌完全展現在眾人面前,考古專家發現這座墓葬的整體方向是坐北朝南,屬於豎井單室磚墓,而且還有幾條墓道。
墓室的正中央擺放著一個巨大的石棺床,但裡面的棺材和墓主人的屍骨都受到了損害,只有旁邊的17塊石質屏風儲存完整。
而石質屏風和石棺床都是用砂頁岩製成的,質地非常鬆軟,更難得的是,它們歷經千年時間都沒有被腐蝕,屏風上的圖畫色彩絢麗,依稀可辨當年繁榮的街市交易景象。
另外墓中還有胡人形象的石俑,手持多種樂器,有琵琶、箜篌和橫笛等。
當時的專家們學疏才淺,又沒有更多的資料參考,只能根據墓葬風格初步推斷出這是隋唐時期的異族墓葬,其墓主人精通中西方文化,可能還是位頗具浪漫主義情懷的商人。
令人惋惜的是,雖然這座古墓的構造儲存完整,但裡面的大量文物都被可惡的盜墓賊偷光了,只留下了銅鏡、金釵、釉陶燭臺等文物。
由於出土文物有限,再加上這些只是尋常陪葬物品,所以這座古墓並沒有引起考古學家們的研究興趣,甚至連古墓的發掘報告都是10年後才公佈出來。
而那些出土的石棺床和石質屏風自然也被博物館當成價值不高的文物,隨意擱置在倉庫裡。直到多年後,各地相繼出土了同類文物後,這些石質屏風才被考古學家重新拾起。
雖然當時考古學家們的專業知識有限,無法看出17塊石質屏風的珍貴价值,但隨著考古學的發展,我國出現了很多經驗豐富的專家們,他們自然也能從全國的考古動向上發現這些文物的些許端倪。
除了這17塊石質屏風被誤判外,我國也有大量珍貴文物都毀在了學藝不精的考古專家手中。
1956年,中國著名文學家郭沫若等人堅持發掘明定陵,但因為沒有相關經驗,竟毫無準備地打開了陵門,導致裡面大量珍貴字畫和絲織品接觸氧氣受損,輕則成了碎片,嚴重的直接碳化。
還有些沒有考古經驗的隊員,竟然裸手拿取文物,導致墓中3000多件文物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壞,只有一小部分完整儲存了下來。
他們絲毫不懂得尊重帝王帝后的陵寢,在收集完文物後,將屍骨隨意地扔在了地上,著實令人痛心,國家也因此出了新規:“全國範圍內,禁止發掘帝王陵。”
如此不負責任的考古行為在我國還是少見的,但還是有很多不被重視的文物突然被認定為國寶級文物。
而當初參與挖掘和研究石質屏風的考古學家們得知了自己的誤判後也非常後悔,他們公開承認是因為自己學識淺薄,才會導致珍貴的石質屏風被無視了三十多年,他們還表示:“我們的確犯了大錯!”
其實出現這樣的問題,也不能完全怪罪於第一批發現研究的考古學家們的身上,畢竟每個人的知識都是從書本上得來的。
即便考古學家們的知識儲備要比尋常人豐富,但並不意味著他們不會錯,尤其是在面對新奇陌生的歷史文物時,往往都是靠直覺、經驗和判斷能力對這些文物進行認定,很有可能造成誤判。
如今,我國仍然有大量文物的價值都沒被發現,但隨著考古技術的不斷髮展,考古學家們會對文物遺址進行更加仔細地挖掘研究,讓那些埋沒的珍貴文物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