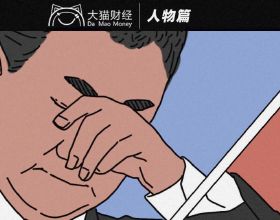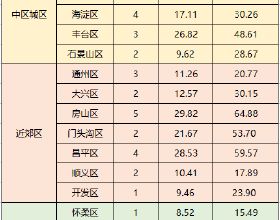前言
1950年4月28日,一名美國女作家在術前寫下一份遺書:
我唯一的信念和誓言,就是那些貧苦的,被壓迫人民的解放,而中國革命的成就,已經是這一解放事業的中流砥柱........
由我著作獲得的全部收入,不管來自於哪,全歸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將軍所有,按照他的願望處理......
火化我的遺體,將骨灰送交朱德將軍,埋在中國,葬禮上要演奏國歌《義勇軍進行曲》.........
這名美國女作家名叫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她的一生,傳奇、多彩,並與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
來到中國
1892年2月23日,史沫特萊出生於美國密蘇里州北部一戶貧困的農戶家庭中,她的父親為謀生路,輾轉去到科羅拉多州東南部的礦區做工。
因為常年呆在陰暗無光的地下,父親逐漸變得易怒憂愁,常常酗酒解憂。她的母親則是一個善良溫柔的婦人,平時做些零活,賺取微薄的收入來貼補家用。
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史沫特萊很早就懂得了生活的艱辛,小時候,她就當過報童、傭人,後來還是在姨媽的資助下,才勉強讀完了大學。
在底層品嚐過酸甜苦辣的她,充滿強烈的反抗意識,這時,也正是革命運動盛行的時候,她義無反顧地加入了其中。
在一次支援印度流亡者爭取獨立的活動中,史沫特萊被“親英”的美國當局,以煽動英國統治罪逮捕,隨後被判入獄。
出獄後,為避免再次遭到迫害,史沫特萊離開了美國,她去到德國,成為《法蘭克福日報》的一名記者。
在德國做記者的日子裡,史沫特萊一直關注著印度反抗英國統治的進展,在一次研究亞洲史的時候,她看到一個對自己來說非常陌生的地方——中國。
1927年冬,史沫特萊在柏林大學發表題為《亞洲的反抗》的演講,其中,史沫特萊提到:
亞洲民主主義和歐洲帝國主義的攤牌很快就要發生了,而中國,會是這場鬥爭的中心。
後來,史沫特萊去跟報社負責人商議,希望派自己去中國,負責人同意後,史沫特萊成為了《法蘭克福日報》駐中國的一名記者。
1928年11月,史沫特萊出發了,從歐洲經蘇聯後進入中國,後又一路向南,到達上海。
一路上,史沫特萊看到了舊社會下中國老百姓的生存之難,豪橫冷酷的地主豪紳,無賴潑皮的散兵遊勇,還有日本侵略者聞所未聞的兇殘暴行。
在北平,史沫特萊看到了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卻連飯都吃不飽的工人,其中有不少都是農村買來的孩子,兩隻胳膊瘦得像是火柴桿,工頭拿著鞭子在過道里來回走動,看到有人停了一下,便會一鞭子抽上去。
種種所見所聞,讓同為貧苦出身的史沫特萊意識到,中國革命勢在必行,也必須有這一把“火”,將中國舊社會的腐朽、黑暗、壓迫、殘暴燒個乾淨。
然而,在到達上海的一刻,史沫特萊失望了,當時的上海正處於“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反動派大肆捕殺共產黨人,街道上隨處可見革命者的鮮血和遺體。
不過,史沫特萊並沒有放棄,她冒著被特務殺害的風險,堅持報道國民黨反動派製造的白色恐怖,在此過程中,她還因機緣巧合結識了宋慶齡。
宋慶齡成立“中國民權保證同盟”後,史沫特萊成了她的英文秘書,“民盟”向國民黨反動派發出的抗議,被史沫特萊用英文傳向世界,愛因斯坦、蕭伯納、羅曼·羅蘭等人紛紛簽名聲援。
後來,她又透過宋慶齡,認識了不少革命同志,其中包括時任粵贛邊區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周建屏。
當時,周建屏從蘇區來到上海治病,宋慶考慮到他的安全問題,便將他安置在法租界史沫特萊的寓所。
周建屏在這裡居住了一個月左右,史沫特萊天天都纏著他問這問那,從周建屏口中,史沫特萊瞭解到了一個真正的蘇區。
她開始嚮往這個遙遠的紅色根據地,她對周建屏說,
“我心裡有種隱隱的感覺,那裡好像一直在等著我。”
隨著“民盟”日漸壯大,國民黨反動派將屠刀伸向了這些民主人士,他們當街刺殺了“民盟”元老之一的楊銓。
送別楊銓的那一天,史沫特萊感覺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悲哀,宋慶齡站在她旁邊,輕輕地說,“這裡黑暗透了,看不到任何希望”。
來到延安
楊銓遇刺後,“民盟”一蹶不振,《法蘭克福日報》也迫於國民黨反動派的壓力,解僱了她。
屢受打擊的史沫特萊垮了,為了治病,她不得已離開中國,回到美國休養。可是,她發現自己已經融不進美國社會之中了,美國人所沉溺的浮誇虛假幻想,令她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於是,她決定再次回到中國,1934年的中國,日本人越發囂張,愛國人士頻繁上街遊行,呼籲國民黨政府積極抗日,而國民黨政府卻不予理睬,反倒盯死了共產黨。
史沫特萊回到上海後,發現很多老友已經離開了,留下的只有魯迅、宋慶齡等人,可大家狀態都不是太好。
史沫特萊很孤獨,也很迷茫,不知道自己何去何從,就在此時,她收到了一封來自西安的信件,發信人是她曾經掩護過的革命者——劉鼎。
劉鼎以張學良副官的身份邀請她來西安,史沫特萊立刻就答應了,隨即啟程去往西安。
西安的氛圍比上海要好很多,有很多抗日愛國活動,當局也給予了最大的寬容和支援。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一時間,國內外湧現了大量的真假訊息,混亂得讓人搞不清真相。
而西安,已經在國民黨軍隊的包圍下,與外界失去了聯絡。為了讓世界瞭解自己的抗日主張,張學良主動召見了史沫特萊,委託她主持對外英語廣播,向世界播報“西安事變”的真相。
史沫特萊欣然接受,她坐在廣播前,用感冒未愈的嘶啞嗓音,向世界播報著“西安事變”的最新程序。
1937年1月,史沫特萊收到了來自延安的邀請信,信中表示歡迎她去延安看一看,這封信徹底點燃了史沫特萊的激情,四年了,她終於要踏上自己嚮往已久的紅色土地了。
趁著“西安事變”的混亂局勢,史沫特萊不顧國民黨“不準外國記者進入紅色根據地”的禁令,坐上了延安派來的車。
到達的當天,史沫特萊就見到了國民黨報紙上“殺人不眨眼”的“赤匪頭子”——朱德。
朱德穿著一身打著補丁的灰色制服,看見史沫特萊,便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臉上還帶著憨厚和藹的笑容,猛地一看,就跟村子裡隨處可見的老大爺差不多。
在之後的談話中,史沫特萊對朱德有了新的瞭解,比如他並不是出生在富有的地主家庭,而是一般的佃農家庭,他的母親還需要幫有錢人洗衣裳掙錢。
和朱德聊得越多,史沫特萊越是對他感興趣,他的每一個回答都真誠大氣。突然,她萌生出一個想法:想要為朱德寫一部傳記,讓世界瞭解真實的朱德和中國革命。
因此,在朱德詢問她在延安有什麼打算時,史沫特萊告訴她,“我希望你能把你一生的經歷全部講給我聽。”
朱德不解,詢問緣由,史沫特萊說,
“因為你是農民,中國人十個裡有八個都是農民,而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人向世界談到過自己的經歷,如果你把你的身世告訴我,也就是中國農民第一次開口。”
“我的經歷只是中國農民和士兵生平的一部分,沒什麼值得你寫的,請你到各地走走,和別人見一見,談一談,再做選擇吧。”
史沫特萊接受了朱德的建議,和很多紅軍將領接觸了,然而,再跌宕起伏的經歷也敵不過最初的好奇,最終,史沫特萊還是決定為朱德撰寫一部傳記。
1937年3月,史沫特萊正式實施寫作計劃,她和翻譯以每週三次的頻率,去和朱德交談。
一般是由史沫特萊提問,朱德回答,再展開思路盡情發揮,有時說著說著,史沫特萊就會熱淚盈眶,朱德問她怎麼了,她說她想到了自己的母親。
朱德嘆口氣,“世界上的窮人原是一家”。
除了採訪朱德,史沫特萊還遇到很多有趣或溫暖的人,她經常走著走著,就有人過來握著她的手哭。
原來,這些人是她在西安救助過的人,那時候,她經常去給滿身瘡痍的政治犯們擦藥包紮,後來,這些政治犯們大都來了延安,一眼就認出了史沫特萊。
在延安,史沫特萊感受了乾淨和真誠,這裡的人們對革命抱著令人無法理解的熱忱和信心,她想,
“我喜歡這裡,我也應該在這裡。”
4月,史沫特萊向黨組織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不料,她的申請遭到拒絕。史沫特萊嚎啕大哭,她只能用這樣放肆的方式抒發自己的難過。
後來,宣傳部部長向她解釋被拒絕的原因,因為史沫特萊是外國記者,她留在黨外反倒會起到更大的作用。
儘管如此,史沫特萊依舊深受打擊,這也成為她一生的憾事。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朱德即將率部奔赴抗日前線,臨行前,他問史沫特萊打算怎麼辦。
史沫特萊也拿不準主意,便去請示了毛澤東,毛澤東跟她說,“這次戰爭,比過去歷史重要得多。”
確定了想法,史沫特萊便收拾好行李,等著出發了,結果她一個不小心從馬上摔了下來,把背脊給摔傷了,因此,整個夏天,她都只能在延安的窯洞中養病。
兩個月後,史沫特萊實在待不住了,她向毛澤東請求去前線採訪,毛澤東送給她一把藤椅,還配了兩名警衛和一名勤務員。就這樣,史沫特萊跟隨戰地服務團一起去到山西。
10月下旬,史沫特萊再次見到朱德,朱德滔滔不絕地給史沫特萊講同日本侵略者戰鬥的故事,勾得她心癢癢。
當她知道自己的朋友獲准隨軍前往抗日前線的時候,她向朱德提出要求,希望自己能夠同去。這要求當即就被朱德和任弼時給否了。
朱德說上前線的人得是有打仗準備的人,史沫特萊說自己在美國西部長大,可以打仗。
朱德還打算用其他理由拒絕她,“可你是個婦女......”
話沒說完,史沫特萊就打斷他,“我並不是因為想當婦女才成為婦女的,是上帝把我造成這樣子的!”
聽了這話,朱德和任弼時都笑了起來,而康克清還記得,那一天,史沫特萊噘著嘴,還委屈地掉了淚。
最終,朱德還是同意了她上前線的請求,但規定她只能和部隊一起行動,在之後的一段時間裡,史沫特萊近距離觀察到了朱德指揮戰鬥的樣子。
史沫特萊撰寫了幾十篇戰地通訊,也跟著八路軍總部輾轉多地,1940年史沫特萊積勞成疾,而且病症越來越嚴重。
這一年夏天,史沫特萊被送到重慶治病,但國民黨對她的一舉一動都進行著嚴密的監視,沒辦法,史沫特萊去到香港。
魂歸中國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後不久,史沫特萊返回美國,她本打算在美國休整一段時間後,再回到中國完成傳記,結果內戰爆發,美國參與其中,史沫特萊想要回到中國的希望沒了。
她只能奔走於美國的大街小巷,為中國抗日奔走疾呼,當時的美國報紙稱她是:日本黑名單上最想除掉的六名外國人之一。
然而,這種情況隨著二戰接近尾聲時戛然而止,因為美國政府支援的並不是中國共產黨,因此史沫特萊受到打壓和詆譭。
她被汙衊是蘇聯的間諜,行動被監視、經濟被打壓,生活艱難,還有一些好友與她反目成仇。
1945年,史沫特萊搬到耶德莊,開始潛心撰寫朱德的傳記,為了充實原有材料,史沫特萊還給朱德寫了信。
朱德按照史沫特萊的要求,寄去了大量資料及自己發表的文章,同時,還有兩枚嵌著朱德和毛澤東肖像的別針和一塊延安工人制作的披肩。
1949年,史沫特萊完成初稿,可她的文章不能發表,更不能演講,本來簽訂好的出版所臨時要求,讓她在文章最後加上反共的內容,史沫特萊斷然拒絕,出版計劃就此擱淺。
史沫特萊也考慮過出國,但是她的護照始終辦不下來,護照局堅稱她的共產黨,因此,她哪裡都不能去,中國更是想都別想。
10月1日,史沫特萊在收音機中聽到了新中國成立的訊息,困頓之中的她趕緊給朱德寫了一封信,
“我將支援新中國到死去的那一天,我要盡一切力量支援中國.....
我活著親眼看見我最大的願望實現了,能夠這樣講的人是不多的,這件事情本身就足夠我一輩子受用了......
如果有一天,我能夠重返中國,我一定要親一親它的土地。”
10月底,經過多次鬥爭後,美國政府終於勉強給史沫特萊簽發了出國護照,不過護照僅限於英國、義大利和法國。
11月15日,史沫特萊坐上開往英國的客輪。
到達英國之後,她立刻參加了英中友協成立大會,在會上,史沫特萊慷慨激昂地講述了自己在中國的所見所聞所感,後來,只要有與新中國相關的活動,史沫特萊一定會參加。
可是,她的身體越來越差,1950年4月,史沫特萊迫不得已住進倫敦牛津醫院。
醫生告訴她,她的病情不太樂觀,三分之二的胃要被切除,這是一個大手術,不過對生命沒有太大威脅。
在病床上,史沫特萊卻莫名地對這場手術感覺悲觀,好像冥冥之中已經意識到了死亡的臨近。
4月28日,她給自己的好友瑪格麗特.斯洛斯寫了一封信,信中交代了她的身後事:
我唯一的信念和誓言,就是那些貧苦的,被壓迫人民的解放,而中國革命的成就,已經是這一解放事業的中流砥柱........
由我著作獲得的全部收入,不管來自於哪,全歸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將軍所有,按照他的願望處理......
火化我的遺體,將骨灰送交朱德將軍,埋在中國,葬禮上要演奏國歌《義勇軍進行曲》......
5月5日,史沫特萊接受了胃部切除手術,第二天,因手術不治不幸逝世,年僅58歲。
10月,史沫特萊的骨灰被運回中國,1951年5月6日,史沫特萊逝世一週年之際,她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朱德在墓碑上親筆題字:
中國人民之友,美國革命作家史沫特萊女士之墓。
10天后,中國駐德使館就史沫特萊在德國德底茲出版社之版權、 版費如何接收的問題電告外交部:
“德底茲出版社請使館轉告朱總司令,該社接獲史沫特萊死前來信稱,她在該社之版權及版費交朱總司令。現在有6萬餘馬克,今後每年約有10萬餘馬克,版權如何接收,版費如何處理,請示。”
接到電文後,外交部直接向朱德報告並請示,並提出兩條由史沫特萊生前好友丁玲和沈雁冰所提建議,
“用於中德友好活動,版權由駐德新華分社制定專人管理”。
隨後,朱德批覆,“此件是文委主辦的,請與文委商議,與史沫特萊有關即可。”
1955年,《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以日譯本問世,很快,英文版及德、俄、法、西等各種譯本也相繼出爐。
1958年,中國駐德國使館再次請示,“朱德副主席在我館存稿費95008.30馬克,此款如何處理?”
朱德沉思良久,提筆批示,“買自然冶金科學新書、化學新書寄回”,隨後,大使館買了大量國外最新科技書籍,全部分給各大圖書館和有關科研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