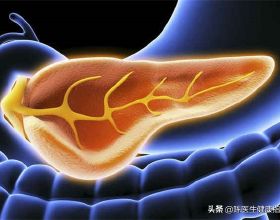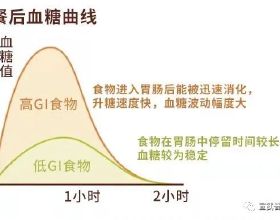“到了英國,我才發現我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彷彿沒有一個人認識我。”
離家多年,早已物是人非。
父母親及兄弟俱已不在,剩下的親人唯有生活窘迫的兩個妹妹和侄子。
重新回到人群中,魯濱遜依舊面臨著同一個問題:如何在這世上安身立命。
經過一番周折,魯濱遜拿回了屬於他種植園的一大筆財富。
他記得那些曾經對他施以援手的人,他寬厚,感恩,力所能及地回饋葡萄牙船長和那個善良的寡婦,他接濟他的妹妹,收養兩個侄子,他自己也結婚生子,日子彷彿安定了下來。
在兜兜轉轉了一圈後,似乎,他終於過上了父親曾經期望他過的生活。
此時的魯濱遜雖然早已不是那個不諳世事的少年,但對於出海卻依舊有一顆蠢蠢欲動的心。
這個習慣了漂泊生涯的人,在安穩了七年後,再一次遠赴重洋,航向未知的旅程,在漂流的迴旋中,魯濱遜依舊漂泊在海上,而那——又是下一個故事了。
只要英語還存在,他的名聲也將流傳下去
沃爾特·司各特曾這樣評價笛福:
“作為《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只要英語還存在,他的名聲也將流傳下去。”
在笛福的墓前,至今儼然矗立著一塊顯眼的紀念碑,碑上的銘文是:
丹尼爾·笛福
生於1661年
逝於1731年
《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
笛福一生閱歷豐富,他曾用這樣兩句話總結自己的一生:
沒有人像我這樣經歷過如此不同的命運,
一生中多少次富貴,又多少次赤貧。
笛福不只是一個文學家,同時在政治和社會活動領域也建樹斐然。在社會政治和宗教信仰的立場上,笛福有著“堂吉訶德式”的理想。他說:
“捍衛真理,我視死如歸。”
他因堅持原則而備受折磨,被投進監獄,以枷刑示眾。但他始終堅信,無罪而受罰對一個人並不能損害分毫,就像他在《枷刑頌》中寫下的:
“美德藐視人間的一切譏嘲。”
被囚禁的笛福
不論在哪個年代,如果一個人足夠正直的話,那他一定是個勇敢的人,笛福便是。
笛福到了晚年才開始創作小說,浮沉跌宕的經歷彙集在他的筆下,出乎意料的不是慷慨激昂的亂世悲歌或刀光劍影的嘲弄怒罵。
他以一種冷靜、剋制、緩慢的語氣“平鋪直敘”,他文風樸實,但並不意味著他止於瑣碎,而是在對人性、生存睿智地洞察中,用細節填滿每個人物的生活,不刻意在微妙或感傷之處大肆渲染,而是平靜地一筆劃過,化唏噓處為稀鬆平常。彷彿命運自有暴風雨,而生活亦有一飲而盡,將之化解的力量。
在這樣一種雲淡風輕的坦率中,他自然而然地將評判的權利,讓渡給了每一個願意瞭解他筆下人物的當下和未來的讀者。
這是一個寓言,卻屬於每一個人
笛福曾說:
“用另一種囚禁生活來描述某種囚禁生活,用虛構的故事來描述真實事件,兩者都可取。”
的確,在小說的創作中,笛福以一種虛構的真實描摹了某種現實的真實,不可避免地融入了自身經歷的烙印。伍爾芙說:

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1882年1月25日-1941年3月28日)
“在他每部小說的開頭幾頁,他總是讓男主人公或女主人公陷入孤立無援的悲慘境地,以致他們的生存必須是不斷的掙扎,能否活下去完全憑運氣和自己的努力。”
《魯濱遜漂流記》便是一個例子。
作為“魯濱遜三部曲”,笛福在《魯濱遜沉思錄》中終於不再對《魯濱遜漂流記》的主題諱莫如深。
魯濱遜的經歷在象徵著笛福自己被逮捕、囚禁、釋放、躲藏、流浪的一生外,更主要的是笛福認為,這是生而為人的普遍境況,每個人都是這樣延展自己的生活道路,併為生存而奮力掙扎。
這是一個寓言,卻屬於每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