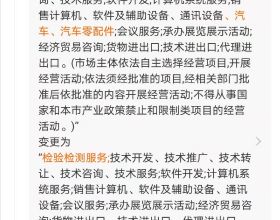我至今還清晰記得,那一夜的戈壁灘很冷。爐膛的火苗跳躍著,把鐵皮做的煙管燒得通紅,坐在爐子上的鋁壺在夜裡依舊歡快地唱歌。
臨睡前,我將一壺冷水坐在爐子上,無煙煤在爐膛裡呼呼地燃燒。無人搭理的水壺自己在後半夜燒開了,便自顧自鳴唱,四周水蒸氣瀰漫。在戈壁灘上寒冷、乾燥的冬夜裡,一壺滾開的水就是房間的加溼器,這是我的發明創造。我洗漱完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卻聽到隔壁女兵們在唱熟悉的軍歌:“十八歲,十八歲,我參軍到部隊……生命裡有了當兵的歷史,一輩子也不會感到懊悔。”
我也是十八歲參軍來到河西走廊的。後來我在團裡的軍人俱樂部當主任,手下四個年輕女兵,住在我的隔壁。每晚臨睡前,我像幫助小妹一樣,幫她們加好煤,封好爐子,再在爐子上坐一壺水。女兵們不明白箇中道理,向我抱怨那個鋁壺半夜鳴叫,她們一夜沒有睡好。我說,鋁壺在夜裡唱歌就是媽媽的搖籃曲。她們卻笑著說,自己已經不是流鼻涕的小孩了。
那晚直到後半夜,我依舊迷迷糊糊聽見有人在唱歌,歌曲一首接著一首,朦朦朧朧。後來愈來愈真切,是女兵們在夜裡唱歌,是壓低聲音在唱的。
天亮後,住在我隔壁的女兵們就要退伍回老家了。那夜是她們在團裡的最後一晚。
陡然,鋁壺停止歌唱,已經老朽的壺底傳來“咯嘣”一聲。我醒了,知道壺裡的水快要燒乾了。我起來加水,聽到那若有若無的歌聲依舊執拗、倔強地從隔壁屋子傳過來。我用火鉗子勾開一圈一圈的爐圈,“噹啷”的聲音很響,“哐裡哐啷”加煤,用火鉗子捅開爐子。房間裡的鋁壺續了新水不再鳴唱了,隔壁屋子的歌聲也戛然而止。
我默默喝水,猜想隔壁屋子的女兵們這會兒也許在聽我房間的響動。過了一陣,她們聽見我房間沒有動靜,歌聲又響起來,還是那熟悉的軍歌。
我一個人靜靜坐著,看爐膛裡的火苗慢悠悠躥上來,紅紅的火焰舔著烏黑的鋁壺,沉沉的鋁壺開始有了響動,“吱”的一下,接著慢悠悠扯開了嗓子。歌聲和著鋁壺的鳴唱,又開始清晰地送進我的耳朵裡。
那一夜女兵們的歌聲有點特別,和站哨計程車兵夜裡用粗糙的嗓子唱歌不一樣,柔軟牽腸,如一泓清泉慢悠悠流淌,一朵潔白的雲彩緩緩飄移。
我坐起來在屋裡踱步,儘量不發出聲響。看來,今夜,我肯定是睡不著覺了。讓她們盡情唱吧。
我用手在黑暗裡打拍子。女兵們唱的是《當兵的歷史》:“十八歲,十八歲,我參軍到部隊,紅紅的領章印著我,開花的年歲……生命裡有了當兵的歷史,一輩子也不會感到懊悔……”
儘管隔壁屋子女兵們唱歌的聲音壓得很低,但在夜裡我還是聽得真切。差不多也是十八歲的年紀,這些女兵們移防到塞外軍營,當時是我去接站的。她們一下火車,就被祁連山下十月的寒風打了一個跟頭。女兵們住在我隔壁房間裡,夜裡爐膛的火滅了,凍得她們蜷縮著不肯出被窩,幾個人在夜裡唱歌,拼命用手擂我的牆。我披著軍大衣頂風過去給她們引火。
第二天,我教她們如何在臨睡前封爐子,才不至於爐火在半夜熄滅。她們學會了,但年輕人瞌睡多,一覺到天亮,因為沒人加水燒壞了幾個水壺後,她們便不願再在爐子上坐水。她們的藉口是,她們已經聽慣了我在隔壁房間裡咳嗽、喝水、看書、朗誦,聽我房間的鋁壺整夜的鳴唱,不需要再放一個壺在爐子上面了。
後來,女兵讓家裡寄過來一個加溼器,放在房間裡。那夜臨睡前,加溼器已經送給我了,她們說這是分別時送給我的禮物。
天開始泛白,女兵們在唱《戰友之歌》,歌聲非常整齊:“戰友戰友親如兄弟,革命把我們召喚在一起。你來自邊疆,他來自內地,我們都是人民的子弟。戰友,戰友!這親切的稱呼,這崇高的友誼,把我們結成一個鋼鐵集體,鋼鐵集體……”
我在屋子裡和著女兵的歌也在低聲地合唱:“戰友戰友,目標一致,革命把我們團結在一起,同訓練,同學習,同勞動,同休息,同吃一鍋飯,同舉一杆旗……”
隔壁的女兵歌曲接龍:“戰友,戰友!為祖國的榮譽,為人民的利益,我們要並肩戰鬥奪取勝利,奪取勝利!”
我的淚水掛在腮邊。
是的,這些移防過來的女兵們,很快就適應了戈壁灘上的惡劣氣候。她們也愛美,偷著改肥大的軍褲,讓我訓得滿臉淚花。她們的堅強與樂觀超出了她們的年齡。
她們也經常向我抱怨,面板粗糙了,嘴唇乾裂了。當真正要離開的時候,她們卻萬般不捨,一夜未眠,唱歌到天亮。
清晨,歡送老兵的火車站臺上歌聲一片。軍歌嘹亮,聲音大得讓人聽不見火車的汽笛聲。哭紅眼睛的女兵們向我敬禮,然後和男兵一起唱軍歌。火車站的軍歌和昨晚女兵們唱的軍歌不太一樣,有男兵加入的軍歌顯得雄壯激昂。
四個女兵站在月臺上,大方地唱起《相逢是首歌》:“你曾對我說,相逢是首歌,眼睛是春天的海,青春是綠色的河……”
這件事情已經過去許多年了,現在想起那夜女兵們唱了一夜的軍歌,熟悉的旋律彷彿就在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