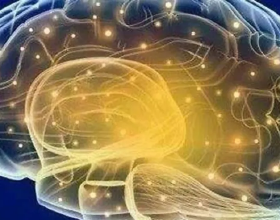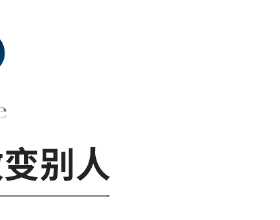方言要傳承,在適當的場合,使用恰當的方言,這就是傳承。
《新民晚報》“夜光杯”上眾多美文,尤其是長三角作者的美文中,時不時會出現方言詞語,作為方言研究者,我一直關注著,也一直把這些版面當作方言資料庫。同一方言小區中的這類詞語,是我需要收集的書證,有的還是難得一見的。這不,張勤的《抹桐油》,標題妥妥地就是方言特色動詞。從文中記敘到“佘山”看,作者是松江區人,這是上海方言源頭地區的原住民後代在說方言老詞。
《抹桐油》寫的是父親為自家房子門窗上抹桐油的事,這讓我感到熟悉而親切。可以這樣說,凡在滬郊農村待過的人,都懂“抹桐油”是怎麼回事。以前在老宅上時,每年都有人家會“抹桐油”,我也經常在家裡“抹桐油”。“抹”的物件既有張文中的門窗,也有木製品,如傢俱農具中的提桶、糞桶等。“抹桐油”的“抹”字,其義是“揩”,即用布頭蘸上桐油後揩到門窗上,但又和“揩”不完全相同。《抹桐油》中也寫到了要“反覆塗抹”“重複多遍”,以我的體驗來說,似乎還可加上“抹”時手指要“稍用壓力”,桐油才會充分滲入。這就是與“揩”的區別,也是使用“抹”字的理由。新的門窗、新的農傢俱,這些木製品長期暴露在空氣裡,容易乾枯開裂,影響壽命。糞桶是農民幾乎每天都要用的,各家買來後板要“抹”上桐油;過仔幾日後,再抹一次,至少要“抹”三次。抹上去的桐油,好似在其表面布了一層保護膜,這時它的顏色是金黃色。當然,桐油不是一“抹”了事的,每年需要“復抹”,有了三頭五年的重複“抹”和日曬夜露,表面的金黃顏色會逐漸變成黑色。經過桐油的滋潤,所抹之處可保雨水打勿溼,日頭曬勿枯。這種老祖宗使用過的技術,連同方言詞,一代一代,一起傳到了我們這一代。為此,拙著《莘莊方言》列有“抹桐油”詞條,釋義是“往木器、木料表面抹上桐油”,還特別強調了“‘抹’和‘揩’詞義有區別”。
我一直有個看法,方言中的動詞比起官話來,一是數量多,二是分類細,使用它們可使語句表述更準確。只要你理解某個詞義,就會感到,它的使用,幾乎到換一個動詞就不能、或大為遜色的地步,我把它們稱為特色動詞。“打”字在官話中功能巨大,包打天下。但官話中的“打水”一詞,在滬(吳)方言中,會根據不同的工具、不同的動作,生成許多詞語。如到田裡澆水,先要挑仔兩隻糞桶到河裡取水,農民說的動詞叫“抓水”。不放下擔子能抓滿兩桶水是有技術難度的,而當你學會了這個動作,就會感到此時此地,“抓水”二字最確當。拿了提桶去河中取水,方言叫“挽水”。用瓶子、特別是細長的瓶子河中取水呢?則稱“搵水”。它的動作是先將瓶子“沉”下去,“沒”過瓶口,讓河水“咕嘟咕嘟”進去。就是這個“搵”字,在一千九百年前的《說文解字》中就有,讀音是烏困切,詞義是“沒也”,音、義都同滬語中一樣。三個特色動詞,完全符合各自的實際動作,也是不能替換的。
《新米飯斷想》是嘉敏友的新作,文中有另一型別的特色動詞“鹽瓜幹”,“鹽”本是名詞,這裡作動詞用,詞義是“醃”。“鹽”的書證材料在明清文獻中很多,文長不引,日常生活中用到的更多,不僅有“鹽瓜幹”,還有“鹽鹹魚”“鹽鹹肉”“鹽鹹菜”等,表明這也是一個流傳有序的方言老詞,至今活在民間。邵文中使用的方言還有很多,如癟塘、真生活、凝頭、淘、半夜飯、行灶、鹹酸飯等,有的可能已比較陌生了。“癟塘”是指金屬器皿表面的凹陷。我的電腦資料庫中,儲存有“夜光杯”上“癟塘”的另一書證:“這隻原本草綠色的軍用水壺……壺身上已有了幾個癟塘。”(徐慧芬《尋找》)同邵文中“那個處處癟塘的鋁皮飯盒子”詞義完全相同。重要的是,這裡似乎也不能換用其他詞語,這就是方言的魅力。
媒體上經常談論方言傳承問題,鄙意是,在適當的場合,使用恰當的方言,這就是傳承。(褚半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