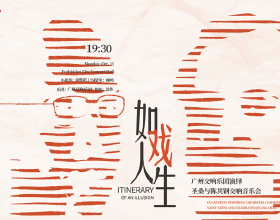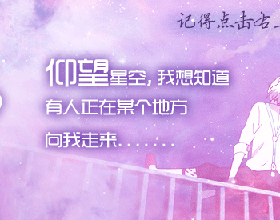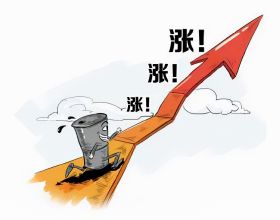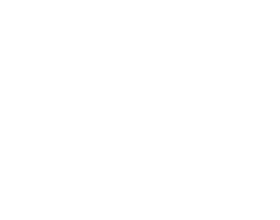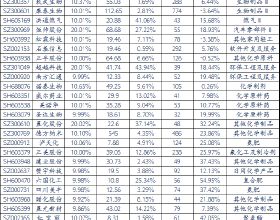有人說,聖彼得堡是俄羅斯的終極女神。這座位於波羅的海沿岸、涅瓦河口的城市於1703年脫胎於一片荒蕪的沼澤,從1712年彼得大帝遷都至此一直到1918年的200多年裡,她始終是俄羅斯文化、政治、經濟中心。如今,她以輝煌建築、閃光尖塔、鍍金穹頂以及舉世無雙的藝術藏品吸引全球遊客,而當地人喜歡滿懷深情地稱呼她為“彼傑爾”(Питер)。
歷史上的聖彼得堡是革命之都,俄羅斯波瀾壯闊的近現代史在此跌宕起伏,與時代共舞的傳奇人物也在此際會風雲。從彼得大帝在此建起一座新首都,向歐洲其他國家開啟門戶;到1905年數萬工人遊行請願,在沙皇官邸冬宮遭軍隊開槍鎮壓;再到1917年列寧領導布林什維克黨發動革命,建立蘇維埃政府,都是如此。
100多年前,也是在這裡,旅俄華工的“政治領袖”劉紹周開啟了自己的精彩人生……
同情華工的大學生
劉紹周,後用名劉澤榮,廣東高要人,1892年出生。與同時代中國人相比,他是幸運的。五歲時,隨其父劉峻周來到高加索喬治亞的巴統定居。隨著父親茶葉事業的成功,一家人日子紅紅火火。
身為長子的劉紹周自幼聰慧,從小接受良好教育。1909年,17歲的劉紹週考入聖彼得堡大學數學物理系學習。1914年畢業後,他來到位於北高加索、風景如畫的小城基斯洛沃茨克(位於俄羅斯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庫馬河畔,地名直譯為氣泡水城),當了兩年中學數學老師。1916年,劉紹周重回首都,選擇到聖彼得堡工業大學建築工程系深造。
劉紹周為什麼重回聖彼得堡,已無從知曉。不過,從歷史學家鮑里斯拉夫·博戈亞夫林斯基對百年前這座城市的講述中,似乎能猜出幾分。他是聖彼得堡的一位歷史人文學家,對百年前聖彼得堡的風貌、民俗、建築等頗有研究。透過旅居聖彼得堡多年的老同學黃建民,我知道了這位年輕學者。健談的博戈亞夫林斯基說,1913年美國《時尚》(VOGUE)雜誌曾將聖彼得堡評選為全歐洲最時髦、最有文化的首都。當時,這座城市以其美麗的風物景緻、不俗的人文環境,深深吸引著俄羅斯各地的文化群體。
然而,這次重返聖彼得堡(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不久,在愛國主義浪潮下,這個有濃重德國色彩的城市名稱改為更俄羅斯化的彼得格勒。1924年列寧逝世後,改名為列寧格勒。1991年蘇聯解體後,經過公投後列寧格勒恢復使用聖彼得堡的城市名稱),卻讓劉紹周計劃好的潛心求學之路扭轉了。在這裡,他從一名學生轉變為政治活動參與者,進而成為最早活躍在共產國際舞臺上的中國人。
這一切,要從彼時越來越多華工出現在彼得格勒說起。
博戈亞夫林斯基是聖彼得堡電視臺78頻道的常客,曾應邀參加訪談節目“1915年中國華工修建彼得格勒到摩爾曼斯克鐵路”。1914年一戰爆發後,俄羅斯男人們都上了戰場,很多工作崗位不得不用外來勞工接替。1915年,由於建設彼得格勒到摩爾曼斯克鐵路的需要,大量華工出現在彼得格勒。大多數華工雖然沒什麼文化,從事著薪水很低的底層工作,但態度認真、不喝酒,頗受市場歡迎。
博戈亞夫林斯基為我提供了一條線索。經他查證,市區的格拉茲諾夫9號是政府蓋的出租樓,是華工聚集點之一,街道名稱現改為康斯坦丁·扎斯拉諾夫街9/4號。在當時,整棟樓裡住的都是中國人。百餘年前有記者深入採訪後曾發文報道,稱出租樓里居住條件非常艱苦,床都沒有,都打地鋪。華工工作辛苦,薪水很低,連回家路費都不夠。然而,華工跟當地居民之間相處甚安,住在附近的小姑娘們不時給他們送食品,鄰居們也竭力幫助這些中國人。
與當地朋友一道,我按圖索驥地找到這棟外表十分普通,甚至顯得破舊的黃色6層樓房。與景象繁華的城市歷史中心區相比,附近街道狹小、凌亂。從位置看,這裡鄰著先納亞區,先納亞因曾經廢棄的乾草市場得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聖彼得堡的中心。那時的先納亞是這座城市的髒亂之所,初來城市的窮苦工人和農民彙集於此。
劉紹周1916年重返時,這座城市的華工已經為數不少。1917年二月革命爆發後,華工更是不斷湧入。他們的情況各自不同,其中不乏因戰爭和二月革命引發的動亂而失去工作的人。這些人來自俄各地,在失去生活來源的情況下,忍飢挨餓、長途跋涉來到彼得格勒,希望這裡的中國駐俄國公使館能幫助回國。
家庭條件優越的大學生劉紹周與掙扎謀生的苦難華工,原本屬於兩個不同的世界。然而,兩者之間發生交集,卻有一定的必然性。在父親劉峻周的影響下,劉紹週一直心繫祖國、關注時事。
1917年二月革命後,大概3月某天,他從報紙上讀到一則訊息,知道大批華工被拐騙到俄國當苦力,很多人受到剝削和虐待,成為“黃奴”。有人失業又回國無望,被迫到處流浪。其中有的華工來到彼得格勒,希望能得到中國駐俄國公使館的幫助。這則訊息讓劉紹周震驚,他決定去公使館找劉鏡人公使瞭解情況。
涅瓦大街是這座城市的主幹街道,寬敞而時尚。3月的彼得格勒依然寒風冷冽,地上的雪沒有融化,天陰沉沉的,冬日裡常見的灰白色讓人心情壓抑。裹著厚大衣的劉紹周走在這條去往公使館的必經之路上。繁華的街道旁,猝不及防映入眼簾的是那些正在乞討的同胞,衣衫襤褸、瘦弱不堪。這一幕深深觸動了劉紹周。不久後,這位年僅25歲的熱血青年做出了自己人生的重大決定。
輟學,為華工服務
在中國駐俄國公使館,劉紹周從劉鏡人公使那裡聽到的是一番訴苦。劉公使說,他已經多次給北洋政府發電報,但均無指示。送華工回國需大筆經費,公使館無力承擔。由於經費短缺,公使館也無法就地救濟華工。公使館能做的事情就是為那些沒有護照、來館申辦身份證件的華工簽發國籍證明書,否則他們無法在此久居。
幸運的是,我的老同學黃建民不久前偶然參加了一位當地作家舉辦的講述柴可夫斯基街老故事活動,從中得知這條街百餘年前名為謝爾蓋耶夫街,其22號曾是中國駐俄國公使館。於是,在老同學的陪同下,我很快就在市中心的柴可夫斯基街22號找到了當年中國駐俄國公使館的舊址。
柴可夫斯基街歷史悠久,雖比不上涅瓦大街寬敞,但並不窄小,兩側佇立著頗有年頭的歐式小樓,古典、雅緻。沒有22號門牌,但依據兩旁分別掛出的20號和24號,我們很快就確定22號的入口所在。
站在公使館舊址前,凝視著入門處典型的俄式拱形小門廊上的雕花,想象著,當年滿腔熱情的劉紹周從公使館出來時,是何等的憤懣。
意識到無法透過公使館渠道幫助華工同胞後,劉紹周並沒有氣餒,他開始和中國留學生一起尋找解決辦法,儘管那時留學生屈指可數。據劉紹周後來回憶,當時算上他和自己妹妹,中國留學生總共只有8個人。大家一致認為:必須立刻開展救濟華工的工作。
在劉紹周的帶領下,這些年輕人分頭聯絡了二月革命上臺後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中國駐俄國公使館中的熱心館員以及華僑商人。經過醞釀,在彼得格勒創辦一個華僑團體來救濟華工的想法和思路逐漸清晰。
1917年4月18日,“中華旅俄聯合會”在彼得格勒召開成立大會,通過了《中華旅俄聯合會規則》,推選劉紹周為會長、留學生劉雯為副會長。選舉了15名幹事組成幹事會。這些幹事有的是留學生,有的是使館官員,有的是僑商。“中華旅俄聯合會”,這個由愛國青年自發組織的救濟華工團體就這樣誕生了。
從4月成立到十月革命爆發短短的半年中,在人手少、經費不足、環境惡劣的情況下,劉紹周帶領聯合會成員,為華工事務奔走,進行了大量細緻、繁瑣、艱難,甚至是危險的工作。
為了解俄國各地華工的真實情況並取得其所受虐待的證據,以便向俄國臨時政府交涉,聯合會一方面與各地華工,尤其是邊遠地區華工直接聯絡,獲取詳細資料;另一方面,派人進行實地調查,為此還設立了莫斯科分會。作為會長,劉紹周與俄國政府多家機構一再協商,力爭改善華工待遇。他還提議修改華工合同,並自己動手起草、統一合同細則。
在安置彼得格勒華工方面,聯合會頗有成效。4月間,俄國臨時政府內務部召開專門會議討論華工議題,劉紹周作為聯合會代表參會。這次會議決定成立華工安置委員會,成員由俄國政府各機關、中國公使館及聯合會派代表組成。會議還決定在彼得格勒設立華工棲留所,由市自治會出資7萬盧布、聯合會出資1萬盧布。
5月初,棲留所開始接待“流浪”華工。聯合會依據其具體情況分別處理,有的送回國,有的介紹工作,還將患病華工送市立醫院免費治療。聯合會成立了招工所,截至1917年9月,共為1000多名華工安排工作。有的進入工廠,有的打掃城市街道或給住戶送木柴等。關鍵的是,聯合會努力幫助華工爭取享有與俄國工人同等的權利和待遇。
為了讓一些傷殘華工免費乘坐火車回國,劉紹周直接求見臨時政府首腦——部長會議主席克倫斯基。或許是這位中國年輕人的執著和熱情感動了俄國官員,他最後同意撥出專車、免費送華工回國。不過,回國人員必須由聯合會擔保。統計資料顯示,透過這種辦法,聯合會到1917年9月1日共送回華工1000餘人。
劉紹周從無到有建立起聯合會,全身心投入到幫助苦難華工的事業中。為此,他放棄了學業。在這一過程中,他表現出極大的愛國熱情,淵博的跨領域知識以及高超的組織協調、溝通和號召能力。
歷史的舞臺正在為這個年輕人徐徐拉開大幕。
文/韓顯陽
素材來源/韓顯陽
責編/林風
編輯/千里、海哲
插圖/千里
統籌/南客
來源: 破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