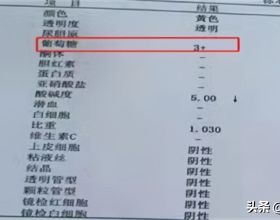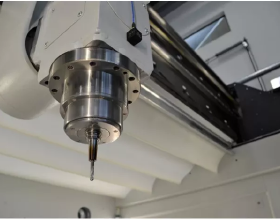夜讀·開卷有益
陶淵明也煩惱。煩惱什麼呢?怎麼教孩子。他甚至為此寫了一首著名的詩《責子》。
《責子》
陶潛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
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
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
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
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慄。
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讀到陶淵明如此焦慮自己的孩子“幹啥啥不行,吃飯第一名”,簡直讓人笑噴飯了。
自古至今,教育是所有家長共有的煩惱。古代文學博士、副教授黃曉丹對此深有感悟。她教授中文系的中國古代文學課,也教小學教育系的兒童文學課。她說,關於傳統文化,有些問題幾乎每週都要被問,比如“幾歲應該看四大古典名著?”“孩子不愛看《紅樓夢》只愛看《哈利·波特》怎麼辦?”。
於是她靈光一閃,把這些最常見的問題蒐集起來,以“陶淵明也煩惱”為題寫了一本書。這本書的有趣在於它故意“反彈琵琶”,不想教育兒童,反而想要先“點撥”一下家長。
今晚我們就來讀一段書裡的文章,作者的觀點非常有意思。
下文經出版社授權,摘自《陶淵明也煩惱:給家長的傳統文化啟蒙課》。
童年噩夢:給叔叔阿姨背唐詩
文|黃曉丹
小朋友童年都有一個噩夢——給叔叔阿姨背一首唐詩。這件事情實在是太讓人習以為常了,在我自己是個小朋友的時候,也經常被爸爸媽媽拉出來給叔叔阿姨表演背唐詩。但是你如果現在問我,這樣做對小朋友好不好?我會說不好。
為什麼不好?從我自己的記憶來說,當我是一個小朋友的時候,我並不是任何時候都想要背唐詩,也不是對著任何人都願意背唐詩。當眾表演背唐詩這件事情,其實會給我帶來很大的壓力,哪怕背完之後大人會說這個小朋友真聰明。
在我還是一個小朋友的時候,我就很明確地知道,一個想聽我背唐詩的大人,並不想和我真正地交流。我之所以不得不背,只是因為年紀還小,沒有辦法拒絕大人的要求而已。
當我漸漸長大,我就發展出了自己的一套策略,把我會背的那些詩詞分成兩部分,一部分屬於表演用的,一部分屬於我自己。對於表演用的那一部分,其實我關閉了對它的感覺,所以叫我揹我就背,就好像在背乘法口訣表一樣不帶感情。而屬於我自己的那一部分,我就不讓大人知道,以免他們讓我表演。那些我小時候表演時背得最多的詩詞,到現在我都對它們沒有感覺。
我的師兄鍾錦,一位華東師範大學的副教授,有一篇採訪稿的名字叫作《他說太精妙的古詩詞,不要讓孩子過早接觸》。為什麼呢?他在裡面講到,小時候他的父親會逼他背許多詩,雖然他到現在也能背得滾瓜爛熟,但是情感上很難產生共鳴。他還說,他整個小學都在背詩,背一首就會抄在本子上,雖然抄了四五本,但是用處並不大。
最後他援引我們的老師葉嘉瑩先生的話說:“人的心靈大概也和肉體一樣,是可以因日久摩擦而起繭子的!”
所以如果在孩子的感悟力還沒有完全自主的時候向他們教授詩詞,即使之後感悟力日趨成熟,孩子也會因為對作品太過熟悉而無法敏銳地體會其中的情感。我看了這個訪談之後就特別高興,覺得“哎原來不止我一個人這樣子,原來我們的童年經驗都差不多呀”。
我和我這個師兄雖然都是從小就背古詩詞,可是我們後來都有一個階段,是重新自主地去閱讀那些古詩詞的選本,然後選出那些對我們自己來說有感覺的詩詞。對我們來說,這一部分詩詞才是開啟古典文學大門的鑰匙,並且這個過程是揹著父母完成的。
後來為什麼我們都選擇了以古典文學為專業?我想是因為古典文學參與了我們的自我的建立過程,它讓我們最初體驗到“我是一個獨特而自主的人”。這個道理就和有些人為什麼選擇計算機為專業一樣,是因為計算機讓他最初體驗到自己是不同於父母的一個獨特、自由的人。
表演
這裡,我想分解表演背古詩詞的過程,看看在這個過程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父母和孩子之間的真正互動又是怎麼樣的。
首先,背誦本身就是一個測試。而且與孩子們在學校裡面進行的考試相比,這種背誦測試是突發的、任意的、公開的。不管這個孩子上一秒鐘在吃什麼飯或者玩什麼遊戲,只要大人忽然想到,就可以把他拉出來表演背誦。這當然會給孩子帶來巨大的壓力。
在約翰·霍特寫的《孩子為何失敗》這本書裡有一章就講到測驗的害處。作者說:
焦慮的孩子經常感到被測試,他們對失敗懲罰丟臉的擔心,嚴重削弱了他們感知和記憶的能力,逼得他們逃離學習材料。
在這位作者的另一本書《孩子是如何學習的》中,他更詳細地解釋了測試的害處:
第一是說測試會給孩子壓力,讓他們去猜測大人要的內容,而不是自己感受到的內容;
第二是說不停地測試,向孩子傳遞了一種“我對你到底有沒有掌握這個知識沒有信心”的感受。
這兩點說得當然對,但它並不是直接針對背誦測試而言的,我們怎樣把這樣的洞識聚焦在當眾背唐詩這件事上呢?
我想可能可以這樣理解,我們都默寫過詩詞,我們知道在默寫過程中,有時記憶會忽然卡殼,有可能要先寫出下句才想得起上句。但是隻要我們能夠透過自己的方式把這一首詩都回憶出來,我們還是一百分。
可是當眾背誦的過程,特別是在一群沒有耐心、隨時都可能把注意力轉向其他事情的大人面前,一個停頓、一句話順序的倒錯都可能馬上被指出、被提示、被更正,從而讓背誦者感到挫敗。
小朋友很可能在這個過程中感到非常沮喪,變得結結巴巴,甚至逃走。對他們來說最簡單的逃避辦法,就是從此之後拒絕背誦一切古詩詞,甚至為了避免當眾背誦,乾脆就不再學習古詩詞。如果我們學習的某件東西,會使我們有當眾出醜的可能,我們的學習熱情一定就不會高。
作為大人,如果有人帶著考考我的態度要求我背誦某一首詩詞,我會感到不舒服;如果有人當眾要求我背誦,我更會視之為挑釁。
既然大人是這樣的感覺,我們為什麼會認為小朋友感覺不到呢?
功能
為什麼當眾背誦古詩詞會敗壞小朋友對於詩歌的興趣?這要從詩歌的功能談起。
詩歌是用來幹什麼的?在中國歷史上對詩歌的功能有很多不同的學說,但有一個大致的共識就是用於自我表達的詩歌更好,而用於表演的詩歌是比較差的。甚至在嚴肅的文學研究中,那些用於表演的詩歌都不太被提及,哪怕有時候提到也是作為反例。
所以在中國詩歌的傳統中有一個最基礎的評判標準,就是你寫這首詩到底是表達你的真情實感,還是用於應酬。
有些用於應酬的詩從技巧上看也很好,比如初唐的應制詩、明代的臺閣體,但是所有的批評家都不會把它視為最經典的那一類詩歌,因為它沒有表達個人的獨特感受,或者說它不夠真誠。這些批評家是說好了的嗎?他們為什麼都這麼看呢?因為“詩言志”是中國文學最基本的一個觀念。
在公元前四世紀的《左傳》中,就提出了“詩以言志”這句話;在大約公元前五世紀的《尚書·虞書·舜典》中,有更明確的表述,叫作“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合聲”;在漢代的《詩大序》中又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行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這幾段重要的文論。都是在講詩歌以及其他藝術形式產生的原因。
大致的意思就是,你心中有所感就會想把它表達出來,不表達出來你就不舒服。而用語言表達出來的真情實感,就變成了詩。
如果你已經把內心的感受語言化變成詩了,但你覺得內在還有東西沒有表達出來,就歌唱它,它就變成了歌,因此歌的源頭也是內心的真情實感。
如果你唱了歌,但你覺得內在還有東西沒有表達出來,那你就用你的身體來舞動,它就變成了舞蹈,因此舞蹈的源頭也是內心的真情實感。
因為中國古人把所有這些藝術形式的源頭都視為個人的真情實感,並認為不是作者先存在了一個想要去寫一首詩、去唱一支歌、去創作一個舞蹈的念頭,而是他們心中有藏不住的情感,這些情感自然流露出來,就成為了真詩。
所以在後來的文學批評中,不但有“言志詩”和“應酬詩”的高下之分,還有“真詩”和“假詩”的天壤之別。
比如大家都知道的陳子昂那首“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登幽州臺歌》)。為什麼這首詩的地位這麼高?因為在那個時代大家都寫應酬詩雖然寫得花裡胡哨,看起來技巧很好,但是當陳子昂寫出這首更真誠、更能表達自己個人體驗的詩時,其他詩就都被比下去了。
感受
我講這些和讓小朋友當眾背古詩有什麼關係呢?
繼續講講我自己的尷尬經歷。在我還是一個小朋友的時候,爸爸媽媽帶我去吃喜酒或者吃人家的壽酒,吃到酒酣耳熱的時候,就會把我抓出來背古詩詞。那時候他們特別喜歡讓我背的幾首詩詞,比如蘇東坡的《念奴嬌·赤壁懷古》《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這就很尷尬了。因為這些酒席的氛圍都是非常快樂的,這樣快樂的氛圍根本不適合這些詩詞。
作為一個詞的背誦者,如果我要忠實於這些詞的真實體驗感受,比如忠實於《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中那種“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的遺憾之感,就等於在說“好花不常開,好景不長在”,等於在說“別看我們今天歡聚在一起,可是誰知道這一次宴席之後,大家又會經歷什麼樣的生離死別”。
如果一個小朋友在他的背誦中真的把這種感受傳遞出來,那他大概要被打了,因為他實在是太掃興了,而且有可能會被視為“烏鴉嘴”。
如果他背的是《念奴嬌·赤壁懷古》,這首詞更是在結尾處把情緒一下子從高潮降落到很低的低谷,最後得出人生如夢、早生華髮的感慨。也就是說,這是一首懷疑人生到底有沒有意義的詩詞,這個意思小朋友不一定說得出來,可是這種感受小朋友是可以感覺到的。
這時他就遇到了一個兩難選擇:如果他忠實於自己從這首詩詞中真正感受到的東西,那他的背誦就是不受歡迎的;而如果他選擇滿足大人們的期待,把詩詞背誦得像大人們喜歡聽的那種歡快的樣子,他就得遮蔽自己對這首詩詞的真正感受。
按照我們前面所說中國人對詩歌以及一切藝術形式的定義,當你遮蔽了對作品的真正感受時,這個作品的意義對你就已經不存在了。所以這似乎會帶來一個悲劇,就是你當眾表演背誦哪一首詩詞,你就會失去那首詩詞。我和我師兄的經歷都佐證了這個定律!
有些家長可能要問,孩子們真的能夠理解詩詞中這些微妙的感受嗎?我覺得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它涉及我們對語言的認識。我相信語言不僅僅傳達了認知資訊,還傳達了情緒資訊。
在中國的詩論和詞論中,有一部分講詩詞作法,講詩詞的用韻和節奏。在這部分理論中講得很清楚,說某些音節、某些韻腳就自然傳通某種情感,比如李清照的《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慼戚”連用七個人聲的疊詞,傳遞了非常妻涼的情感,這種情感是靠聲音而不是靠內容來傳遞的。
我們都知道寫詩的時候,最好在聲音和內容上都比較合拍。所以我懷疑在閱讀詩歌,尤其是中國詩歌的時候,小朋友們可以在不完全瞭解詩歌內容的同時,僅僅從聲音上就可以感受到那種情緒。而且事實上我們倡導學習中國古典詩歌,本身就是希望透過這種聲音和形象的直觀感受來增加對漢語的敏感性。所以如果你堅持認為小朋友不能懂得這些詩歌所傳達的情感,那你也就沒有必要來讓他學習詩歌了。
再次回到讓小朋友在公眾場合表演背誦詩歌這一個主題上。
公眾場合既然是一個場,它就有這個場自身的強大情緒。而小朋友為了符合這個氣場對他的期待,就只能遮蔽自己對這首詩歌真正的情緒感受。這會使得他離自己的情緒很遠,離詩歌的本質也很遠。因此這樣的方式對他的詩歌學習是有百害而無一益的。
詩歌教學最重要的價值不是提升學生的修養,讓他從表面上看起來像個能夠引經據典的有文化的人,而是把詩歌作為一個媒介,讓他學會更好地感受和表達自己的體驗,同時理解他人的體驗。
因此,當一個孩子能夠當眾背誦詩歌的時候,他和詩歌建立的關係未必是真誠可靠的。只有當他在自己的日記本里,或者在他的心裡暗暗藏下一首詩歌的時候,他才和詩歌建立了一種真正親密、永恆的關係。如果你們觀察到自己的孩子願意閱讀詩歌,但是不願意當眾背誦詩歌,這其實是一件好事,這是他們在捍衛自己和詩歌之間的真誠的關係。
摘自黃曉丹《陶淵明也煩惱:給家長的傳統文化啟蒙課》,樂府文化出品。讓孩子得到真正的傳統文化薰陶,成為一個終生學習者。插圖來自攝圖網。
【現貨包郵】陶淵明也煩惱:給家長的傳統文化啟蒙課 詩人十四個
¥48
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