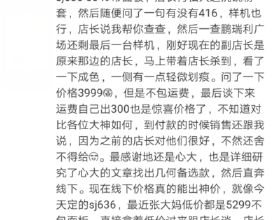我喜歡養花,喜歡養各式各樣的花,後來更著迷於小巧憨態的多肉,曾一度逛花卉市場,見著沒養過的多肉,就買。甚至,還記了好幾頁稀奇珍貴多肉的名字,想找機會都買都手。
我還在陪丈母孃到百貨批發市場上貨時,專門到瓷器店鋪門口,蹲在那裡,從一箱箱便宜處理的過時瓷器裡,挑選合適的碗罐,回來當花盆用。
我為此專門在網上買了手電鑽,和特殊的鑽頭,來給這些瓷器的底兒打上個眼兒,洩水,讓這些瓷器不僅外形看上去,連內在的功能都更像花盆。
我買的多肉太多了,加上我老婆從網上直播裡買的,堆滿了花架和所有的窗臺。一次問自己,竟發現沒幾盆花能叫的上來名字。這哪行?哪怕叫“大毛、二毛、三毛、……截住”,也要有個名字呀。連忙在手機上下了軟體,挨個拍照、搜尋、對比、辨認。終於它們都有了自己的名字。說實話,記不住,到現在還是有一半的花,一張嘴叫不出它們的名字,不過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我還在手機裡都給它們立了資料夾,都建了檔,寫清楚每種花的學名,別稱,原產地,喜好,禁忌,等等。
我還專門到建材市場,買來木頭,買的或借的工具,在陽臺,在露臺,打了兩個很大很結實的架子,讓這些花,不用都憋屈在窗臺上,可以舒舒服服穩在架子上,悠哉地沐浴陽光。架子用料很實在,也很結實,不誇張地說,能放幾盆花,就能摞幾個人。只是我沒敢試,怕架子受得了,陽臺扛不住。
我還從網上買了各種專用的土,養多肉的,通用的,甚至自己粉碎各種葷素廚餘,和從花壇挖來的土摻和在一起,發酵一年,自做有機土壤。
我怕伏天多肉夏眠,被強光曬著,找來工人,在陽臺安裝了滑軌,裝上紗簾。
我能想的都想到了,能做的也都做到了。
我滿心歡喜,疼愛地看著這些花時,就像在看著自己的孩子。
有的花很開心,可有的花似乎並不開心,甚至有的好像在倍受折磨。許多花莫名的枯萎死去,一些花活著,卻無精打采,像只吊著半口氣,如同急診病房躺著打點滴的病人。有幾盆養了許多年的花,枝繁葉茂,只一次水大了,就尋死覓活,非要整個動靜出來,來不來先把一身的葉子落光。
我著急,更莫名其妙,明明為它們該想到的都想到了,能做到的都做到呀。
有時,真想和這些花好好聊聊,相互溝通理解一下。可我說的話它們聽不懂,它們說的話我也聽不懂。我不能理解它們,它們也理解不了我。我走不到它們心裡,它們也走不到我的心裡。數十億年前,我們發軔於同一個單細胞,可如今已是分屬兩個世界的生物,能做的只是默默相對,按照自己的認知與邏輯,在揣度和回應對方。
靜下來時,也恍惚過,做了那麼多,到底是為花好,還是自己在過癮,尋得欣慰?也曾試想過換位思考,可我哪能跟花一樣,戳在裝滿泥土的陶盆裡,站那麼久?沒有花的生活,焉能得花之悟?
往大里說,花有自己的生活選擇和生存邏輯,人也有自己的生活選擇和生活邏輯,只是中間隔著物種。往小裡說,我們這輩人有我們自己的生活選擇與生存邏輯,我們的父輩有他們的生活選擇和生存邏輯,我們的子輩也有他們的生活選擇和生存邏輯,只是隔著時代和歲月。即便是同輩的人,在生活選擇和生存邏輯上,也會大相徑庭,中間還隔著秉性和經歷。許多時候,我們自己與親人、朋友之間,無論怎樣的相互理解、相互關愛和相互給予,就像分屬兩個世界的花和人,遊走在彼此的生活選擇和生存邏輯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