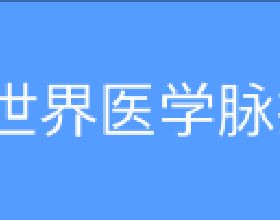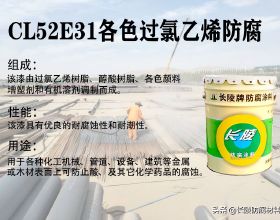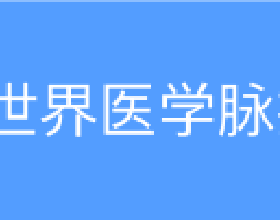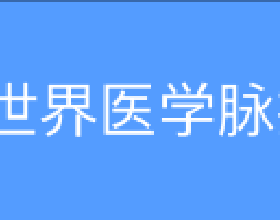在《明史》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往往會引起人們對於明太祖和明成祖對貴州經治方略的討論。
太祖於平滇詔書言:靄翠輩不盡服之,雖有云南不能守也,則志已在黔,至成祖遂成之。
後世諸多學人據此認為,明太祖已有開設貴州之意,僅是時機不成熟而設省未果,直至明成祖才完成此大業。但反覆研究相關史料,始終未能發現太祖已有設定貴州之念。
《平滇詔書》既言“靄翠輩不盡服之,雖有云南不能守也”,據此可知,明太祖經治貴州方略的目的全在於“守雲南”;而要守住雲南,就必須使貴州土司對明廷心悅誠服,而並不是一定要盡廢土司設定行省。
再觀明太祖訓戒田仁智之詞:“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歸善撫之,使各安其生,則汝可長享富貴。夫禮莫大於敬上,德莫盛於愛下,能敬能愛,人臣之道也。”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明太祖訓戒田仁智時,句句不離敬上愛下,長享富貴,絲毫未見俟機罷廢之端倪。豈料田仁智後人不遵法度,私相仇殺,明成祖才得以俟機以計謀抓捕。這顯然不符明檄詔討的祖制,而是靠陰謀取勝。
谷應泰記其事言:“上(明成祖)密遣鎮遠侯顧成率校士數人,潛入二境。執琛、宗鼎去。二人既就執,城中猶寂,無知者。忽一日,使出揭榜,諭諸羅曰:‘朝廷以二凶日構殺,荼苦百姓,故特遣使執問。狀首惡既擒,餘一無所問,敢譁者,族。’諸羅帖然。琛、宗鼎到京師,俱斬。”成祖此舉實在有損於朝廷的威嚴,也顯然有違太祖之本意。
明太祖處置土司逋賦之辭,更覺太祖之意並不在乎賦稅錢糧之多寡,倒是百般體恤土司完納賦稅之艱難。查《明實錄》得知,太祖關於有關蠲免土司賦稅的言論非此一端。資引數則補正。
洪武九年三月己卯(1376.4.14))詔曰:……思南宣慰等司今年夏、秋稅糧盡行蠲免。(見《明實錄·太祖洪武實錄》卷105 第3頁)。
洪武十八年正月癸酉(1385.2.20))四川永寧宣撫使祿肇遣弟阿居來言:比年以來,歲賦、馬匹皆已輸足,惟糧不能如數,緣大軍南征,蠻夷驚竄,耕種失時,加以兵後疫癘,死亡者多,故輸納不及。上命蠲之。(見《明實錄·太祖洪武實錄》卷170)
洪武二十三年閏四月丙戌(1390.6.7))戶部奏:湖廣、江西、廣東先因叛寇竊發其府、縣,經剽掠者,民散地荒,租稅逋負。及四川、貴州、芒部、馬湖土官積年所欠糧亦多。詔皆免之。(見《明實錄·太祖洪武實錄》卷201,頁6)
上引各則更足以佐證太祖經治貴州的方略從不在乎稅收的多寡,而其實在於收服土司之心。收服土司之心完全是為確保赴滇驛道的暢通。
觀明太祖處置清水江之亂賊首一案,明太祖竟然不連坐藏匿賊首的宋宣慰,反而說“蠻人鴟張鼠伏,自其常態,勿復問。”這絕不能理解為縱容姑惜。而只能理解為,明太祖意在收服土司之心,有諸葛亮七擒七縱的風範。要收其心,自然不會無端損害其利,更不至於僅因其有罪過而俟機罷廢。
觀明太祖斷然拒絕奢香請兵報怨一節,其言辭也有深意焉。太祖處置原則之堅定如泰山之矗立,但爾後太祖對靄翠奢香依然恩寵有加。處置土司之過失,原則堅定與收買土司之心恩德並濟,明太祖可謂能兩全其美矣。龍場九驛開闢後,夷務幾乎全委之於貴州宣慰司。並無俟機收回管理權之念,這種做法同樣與成祖有別。成祖開設貴州以拓土開疆為喜。同樣有違太祖本意。
總而言之,明太祖經治貴州的方略務在安邊通驛,固守雲南,謹防元世祖偷襲雲南的故事重演,以此捍衛中原安全而已。而明成祖經治貴州的方略則在於開疆拓土,成一世之偉業。故在理解“靄翠輩不盡服之,雖有云南不能守也,則志已在黔,至成祖遂成之”,不得言明太祖已有開設貴州之念,實際上開設貴州的成敗功過全系明成祖所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