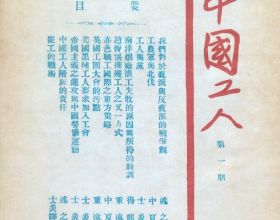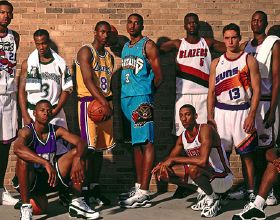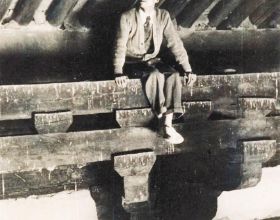(二)中國陰曆起源及其置閏問題
我們知道,中國二十四節氣陽曆能夠準確地標記時令季節變化,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採用平氣法的陽曆,雖然各月曆日數為30日或31日,相對固定,但是,人為將全年時長分為24個等分得到的二十四節氣時點,畢竟不是日地執行自然規律的真實體現,兩者之間自然存在一定差異。而採用定氣法的陽曆,用等距黃道經度標識二十四節氣,能夠更精確地標記時令季節變化,但是其各月曆日數在29-32日之間,相差較大,也不方便規律性排歷和日用。於是,中國遠古曆法學家很早就想到了一種獨具特色的解決方案:日地加月亮的歷法系統。
中國遠古曆法學家在對月球執行規律的長期觀測中發現,月亮朔日和望日最易觀測,而且一個朔望月長度(月球繞地球公轉平均週期)相對固定,月亮執行週期平均約29.53天,一個月行週期日數可為29天或30天。於是,中國古代很早就有了根據月亮陰晴圓缺相對固定的週期制訂的陰曆系統。據記載,中國最早的陰曆產生在神農氏時代。南宋羅泌《路史》記載,神農氏“三朝具於攝提,七曜起於天關,所謂《太初曆》也。”其注曰:“神農之歷自曰太初,非漢之太初也。楊泉雲,疇昔神農,始治農功,正節氣,審寒溫,以為早晚之期,故立歷名。”這裡,“三朝”指年月日,“攝提”即攝提格,是指地支中的寅,“七曜”為日月及五星。這說明,神農創制《太初曆》與日月相關,起始日那天為寅年寅月寅日,日月五星會聚在一起,並且是從“天關”星開始。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科學家趙永恆根據這個記載,透過天文年代學的計算和分析,確定神農《太初曆》的起始日為西曆前4951年3月28日,此日為庚寅年戊寅月庚寅日(三朝具於攝提)。透過高精度天文軟體Stellarium回溯查證,該日清晨,透過連續觀測,七曜(日月金木水火土)確實連續起於天關星(金牛座ζ星)。從黃帝作《調歷》到神農創《太初曆》,相距574年。
現在,現行陰曆從朔日子時(23時至1時)開始,首日定為初一,月望時到達月中,月小二十九日,月大三十日。一個農曆年,常規年有12個陰曆月。陰曆也和中國傳統陽曆一樣,是一種自然歷,根據月象變化起止,不是人為設定。但是,由於一個陰曆朔望月平均只有29.5306天,一個陰曆年十二個月就只有大約354天,比一個陽曆年365.24219天少了大約11天。可見,大約每過三年,陰曆總時長就會比陽曆總時長要少30余天。於是,遠古曆法學家就想到了用陰曆置閏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開始,每三年置閏一次,多一個陰曆月。後來發現不精確,又採取五年兩閏法。還是不精確,又透過尋找閏餘最小誤差辦法,找到了更為精確的“十九年七閏法”。直至最後,找到了科學的“無中氣置閏”法。
關於中國陰曆置閏問題,在現代,對三年一閏、五年兩閏、十九年七閏乃至無中氣置閏的起止時間以及是年中置閏或還是年末置閏存在爭論。從實際曆法上講,古六歷置閏方法沒有明確記載,直到漢初(西曆前104年)《太初曆》才明確記載採用“無中氣置閏”法。但事實上,成書於戰國時期的《逸周書•周月解》早就明確提出:“中氣以著時……閏無中氣,斗柄指兩辰之間。”可見,“無中氣置閏”起源很早。我們對馮時《殷歷武丁期閏法初考》一文提供的殷商武丁時期四段甲骨卜辭所隱含的置閏方式展開了進一步的研究,我們用卜辭可能存在的閏月與按照“無中氣置閏”和建寅建正編制的《中國天文歷表》進行查對,結果發現:除了其中一個卜辭存疑無考外,其它兩段卜辭均在武丁時期找到了卜辭記錄事件所發生的閏月和具體日期,另外一段卜辭也在武丁兒子祖庚六年找到了卜辭記錄事件所發生的閏月和具體日期(詳見後表)。這就說明,至遲在商代,中國傳統曆法就採取了無中氣置閏法,且都是年中置閏,即採取“閏前月”的方式置閏。現在,一般認為,採用十九年七閏辦法始於顓頊歷,無中氣置閏法起於何事,尚無定論。不過,依靠現代科學的天文計算和精確的星曆資料,我們可以上溯還原遠古天文曆法,再結合歷史天象考證,神農氏時代應是陰曆置閏方式的逐步應用和逐步精確的時代,十九年七閏辦法應當至遲在這個時代被發現,並用於曆法實踐,無中氣置閏法至遲可追溯到黃帝時代。
趙永恆,《炎帝神農氏“七曜起於天關”的年代》,重慶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
馮時,《殷歷武丁期閏法初考》,《中國歷史文物》,2004年第2期。
這裡,武丁甲骨記載日期確定我們用的是建寅曆法,沒有使用傳說的殷商建醜曆法。也許,殷商建醜曆法是殷商青銅銘文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