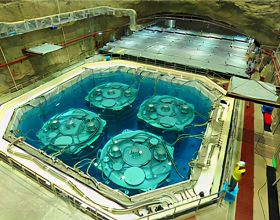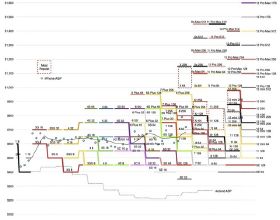風波之來,固自不幸,然要先論有愧無愧,如果無愧,何難坦衷當之,此等世界,骨脆膽薄,一日立腳不得。爾等從未涉世,做好男子,須經磨鍊,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千古不易之理也,孟浪不可。一味愁悶,何濟於事,患難有患難之道,‘自得’二字,正在此時理會。
知勇辨力,爾等不足,謹厚朴拙,爾等有餘。夫知勇辨力四者,皆民之秀傑,然不能惡衣食耕鑿以自養,反不如謹厚朴拙之安分而寡過也。吾家先祖,百年頌佛兒不衰者,正謂其謹厚朴拙耳。多一分智巧,損一分元氣,爾等培此樸拙之心,便是真能守祖之孝子順孫。
——摘自《菜根譚》卷2
人生於世,從生至死當經歷無數之事,有盡興於心者,有哀大於心死者,然無論興歡與悲慼皆人生之遇者也,非恆通如常無變也,切不可以一時之得失哀痛而以為人之終點,抱之以身而無暇拔心令人喪志。當知人生之變乃為常態,人人盡得體驗之。年少輕狂,視萬物之不屑,中年抱恨,悔少年之不及,此人人皆是如此而過,即使聖人亦有如此,非知與非知之過,乃人之心性如是也,故不經歷如此,不得人生之義也。南師曾言:未曾清貧難做人,不經打擊老天真,自古英雄多磨難,從來富貴入凡塵。
人之初,心如赤子,倘如是此心而至老死,近道也!而我等之人,赤子之心染紅塵俗氣漸漸異之也,偶遇煩心之亂則心氣難平,不究赤心之本無,而論世間之不平,失道也。赤子之心,得失不較,隨遇而安,即得即足,即失即忘,養浩然之氣,無煩心之亂,雖刀鋒加於面而渾然不變色,苟臨於淵亦寬於顏。若事事如是為之,人生豈有何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