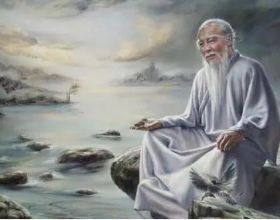季寺,賈敏
法國知識分子是如何變得反動的
法國一直都有右翼思想家,但他們現在比二戰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突出。長達數十年的針對左翼的反革命導致反動的挑釁者重塑了法國的知識分子生活。
法國的右傾趨勢繼續迅速發展。雖然人們普遍預計現任的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將在4月獲得連任,但民意調查顯示,極右翼獲得了近30%的支援率——無論是在老牌候選人瑪麗娜·勒龐還是因種族主義和反穆斯林仇恨言論而屢次被定罪的電視人埃裡克·澤穆爾的背後。左翼仍然軟弱和分裂,民調顯示其主要候選人都遠未獲得第二輪決選的資格。
這種沉悶的氣氛是多年形成的,由勞工運動的衰落、社會主義黨的失敗——特別是弗朗索瓦·奧朗德的總統任期——以及主流媒體和知名知識分子中日益明顯的右翼傾向所驅動。這一點在1月份再次得到體現,教育部長Jean-Michel Blanquer參加了在索邦大學舉行的所謂“反覺醒”會議。

法國馬賽,抗議者舉著橫幅和燃燒火炬,抗議法國極右翼媒體專家澤穆爾的訪問。
為了深入研究法國公共話語的這一轉變,《雅各賓》的Cole Stangler採訪了Frédérique Matonti,後者是一位政治學家、巴黎一大教授、《我們是如何成為反動派的?》的作者。在2021年11月出版的這本新書中,她旨在解釋法國是如何從“一個文化霸權轉移到另一個文化霸權”的。這裡是對採訪的翻譯,有刪節。
你為什麼決定寫這本書?
兩三年前,我看了很多電視新聞。我被我看到的東西震驚了——一種特別反動的、非常簡單的思想路線——這種極其激進的國家世俗主義的觀點,反對面紗,反對布基尼,對學校的看法也非常卡通化。
例如,有這樣一種觀點,即教育水平正在不可避免地下降。還有一種對女權主義的卡通化看法:認為#MeToo女權主義是一種危險的美國女權主義,希望在兩性之間進行戰爭。在經濟方面,偽專家和社論家稱,社會服務是一個問題——它們花費了太多的錢,而且不應該自動獲得,接受者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來換取它們。還有這樣一種觀點,即福利國家太昂貴了,法國人的生活超出了他們的能力。
有一系列的觀點,現在已經強加在公共話語中。當我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讓我印象深刻的也是,我越往下寫,越覺得真實。一年後,事情進一步激化。
我的研究關於1950年代、1960年代和1970年代,我的論文關於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我從事結構主義和所有這些工作。自然,讓我印象深刻的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知識分子和政治霸權與今天的區別。
對你來說,轉折點是從1980年代開始的。你關注四個關鍵主題:這一時期反種族主義運動的失敗;1968年5月的反彈;工人階級和少數族裔之間的錯誤對立;最後,對面紗的迷戀。那麼,1970年代末左翼是如何失去這種“霸權”的?
在1970年代末,有一個叫做新右翼(la Nouvelle Droite)的運動。他們用葛蘭西的術語思考,告訴自己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左翼正處於權力的大門口——正如1981年確實發生的那樣——因此有必要建立反霸權(counterhegemony)。這條路線可以在不太知名的出版物中找到,但也可以在《費加羅》雜誌(Le Figaro Magazine)中找到。它們幫助了從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對這種反霸權的傳播。
1981年,也有左翼上臺。弗朗索瓦·密特朗成為總統,並任命了共產黨部長進入內閣。我在書中沒有這樣說,但值得一提的是,在開始時,有相當激進的措施。某些部門實行了國有化。成千上萬的無證移民獲得了合法身份。媒體從國家監督中解放出來,允許與資訊有不同的關係,與右翼時期非常不同。還有一項由文化部長(最初是賈克·朗)領導的創新的文化政策,試圖給包括爵士樂、嘻哈和街頭藝術在內的文化以重要地位。在密特朗時代的初期,似乎有一個重大的開放,但這也引起了右翼的殘酷的、正面的反對。
首先,在經濟政策上出現了退步。需求方的政策在缺乏邊界的情況下掙扎。法國人在消費,但不購買法國產品,因此這些政策沒有提供預期的刺激。這轉化為選舉的失敗,從1983年開始。然後,在1986年,左翼在議會選舉中失利,造成了一種共處的局面,密特朗不得不與中右翼總理雅克·希拉剋共同執政。
在這裡,你開始看到很多對文化問題非常批評的作家。例如,阿蘭·芬基爾克羅(Alain Finkielkraut)的《心靈的失敗》(The Defeat of the Mind)一書,我經常談及。這本書對文化部長賈克·朗的政策提出了非常嚴厲的批評,認為他在支援一種不合法的文化——比如說,把時尚放在與莎士比亞相同的水平上。他還攻擊了1980年代初的反種族主義運動,這些運動由所謂的“第二代”,即來自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摩洛哥等地的移民的子女領導。芬基爾克羅對此非常批評,特別是其選擇的形式,往往是音樂會。他批評了他所謂的“青年主義”(jeunisme)。對他來說,這也是“社群主義”上升的一個標誌。
這是一個重要的時刻。這些文字被其他人接受並激進化。我不想說得太詳細,只想提一下保羅‧約納(Paul Yonnet,社會學家)在1990年代初發表的一篇文章。在提到一個猶太人墓地被褻瀆時,他說,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並不是來自那些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的人,而是反種族主義運動的錯。這是一種想法,即最終真正的種族主義者是反種族主義者——這是你今天經常發現的。
在法國有這樣一種想法:“共和國看不到民族差異”。任何談論它的嘗試都被看作是一種非法國的觀點,看作必須來自其他地方。但你在書中所展示的是,情況並不總是這樣——這種話語真正發展於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 然後,更具體地說,你用了一整章來討論工人階級和少數族裔之間的這種所謂的對立。有這樣一種觀念,如果你過多地談論差異——無論是宗教、種族還是性——就會疏遠工人階級。這是你在右翼和左翼中經常聽到的東西。
這種話語是在[社會主義者]萊昂內爾·若斯潘失敗後出現的,他[在擔任總理後]未能進入2002年總統選舉的第二輪。對此提出的解釋之一,特別是在左翼,是由於他為少數族裔進行了改革,但沒有為工人階級進行改革。對少數族裔的改革包括同性伴侶的民事結合和政治平等[規定各黨派在選舉名單中提出同等數量的男女候選人]。1997年後,若斯潘擔任總理,與[總統]希拉剋共居(若斯潘率領社會黨贏得國民議會選舉勝利,組建左翼內閣,希拉剋其後任命他為法國總理,是為第三次“左右共治”),若斯潘領導了所謂的“多元左翼”政府[得到了社會黨、綠黨和共產黨的支援]。
確實有堅實的經濟增長,而且他本可以進行更重要的經濟改革。當時的部分說法——他在左翼改革方面走得不夠遠——無疑是真的。但問題是,我簡單說一下,就是這種反對意見的產生,好像工人階級只是自動的白人、異性戀男性。很明顯,它也包括男女同性戀者、婦女和有移民背景的人。所以,這種反對沒有意義,如果左翼想在這樣想的同時重建自己,那就走錯了路。它需要進行經濟改革,但也需要進行打擊歧視的改革。
我還試圖表明,當左翼進行這些改革時——公民聯盟、政治平等、同性婚姻——它是在深刻的分歧中進行的,而且不容易。例如,奧朗德在同性婚姻方面取得了進展,但在輔助生殖技術或代孕方面卻沒有進展。
在最後一章,當你試圖解釋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轉變時,你提出的一個有趣的論點是,今天在法國,成為電視上的小組辯論者(panelist)比成為大學教授更容易[因為各種改革使該系統資金不足]。你還關注了媒體格局的變化和傳統政黨的衰落。
是的,媒體集中在少數公司手中,這些公司主要是為了追求利潤。而且,這不僅僅是政黨在衰落。對左翼來說,無論如何,他們與知識分子、工會和公民社會的聯絡越來越少。這是更重要的一點。
在序言中,你寫道,最終的目標“不只是批評[這種轉變],而是準備一個新的文化霸權”。左翼應該如何做到這一點?
當你今天是一個左翼知識分子時,你就有點處於防守狀態了。
在左翼,人們經常說“這個或那個人是法西斯”,這很好,但只說“這些想法來自極右翼”,就能打敗他們嗎?
既然我們面對的是澤穆爾,知識分子的任務之一就是不要和澤穆爾辯論,因為這沒有任何作用。你不會說服任何追隨他、崇拜他或想為他投票的人。另一方面,我認為某些歷史學家正在做的事情——拆解他的論點,表明它們是錯誤的,表明它們是來自捍衛貝當主義(Pétainisme,即1940-44年的納粹合作主義維希政權)傳統的不實之詞——非常有用,因為它可以幫助說服那些可能被動搖的人。
但也有希望的理由。年輕一代中的一部分人被環境問題和女權主義深深吸引。如果要對左翼進行重建,那將由這些年輕一代領導,他們的話語比他們的長輩要堅定得多。
同樣重要的是,當你做了很好的民意研究——而不是民意調查——你會發現,很大一部分法國人相信重新分配,更多的權力的水平狀態(horizontality)。換句話說,大多數人不相信我們正在談論的反動言論。目前,他們在政治市場上沒有找到能夠代表他們願望的人。
這就是今天法國更大的問題。有很多對政治感興趣的聰明人,他們選擇不投票或決定不註冊,因為他們找不到代表他們的候選人。選舉是由那些登記最多、投票最多的人推動的——也就是老年人,他們一般來說也更右翼。
需求在那裡,但沒有供給?
一部分需求是存在的。我借用Vincent Tiberj(法國社會學者)的話說,他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部分公眾輿論是非常保守和仇外的。這當然存在。但對更多的平等、更多的水平狀態、更多的再分配和對福利國家的捍衛的需求也存在。問題是它還不能找到有組織的形式。
加密貨幣和NFT是一場騙局嗎
近日,一則美國名媛Paris Hilton做客“今夜秀”與主持人Jimmy Fallon談論兩人收藏的NFT作品“無聊猿遊艇俱樂部(BAYC)”的影片片段在社交網路上病毒式傳播(後者為該作品支付了21.6萬美元),引發了眾多對於加密貨幣以及名人為NFT背書的討論和擔憂。
2022年2月5日,《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一篇題為“加密貨幣反對聲浪日隆(The Crypto Backlash Is Booming)”的文章,該文作者Kaitlyn Tiffany認為,我們正處在被和“豆豆公仔泡沫(Beanie Babies craze)”、“網際網路泡沫(dot-com bubble)”和“鬱金香狂熱(tulip mania)”等類似的投機熱之中。今天各大全國性報紙幾乎每天都會談論以加密貨幣和NFT為代表的Web3,大多數文章會附上很多人由衷相信Web3是龐氏騙局、詐騙、傳銷和欺詐的警告。

Web3這個概念是由以太坊聯合創始人Gavin Wood於2014年提出的。Web3從根本上想象了一個從透過臉書、谷歌等中心平臺接入網際網路,向透過一個據說不可收買、不可編輯、防故障的系統進行交流、資訊儲存和支付的規範的大轉型。可以想見這將使普通人對個人資料和互動結果有更多的控制權,然而由於多方面的原因到目前為止這似乎是一場鬧劇。而人們每次提到這個新詞時都會爆發出尖酸刻薄,因為這樣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覺,即Wood等人對於未來的願景是無可避免的,無論誰持保留意見,無論它看起來多麼像一個騙局。如今投機的狂熱遭遇了反狂熱的怨恨。
Kaitlyn Tiffany指出,反對Web3的隊伍正不斷壯大。“Web3是龐氏騙局”被作為迷因、在廣為引用的宣言以及廣泛傳播的部落格帖子裡傳播。或許很快就將成為一個政治口號。那些特別反感NFT的人已經採用了“右鍵點選者”(right-clicker,意指右鍵單擊就可以儲存價格高昂的NFT作品——譯者注)的綽號。Web3和龐氏騙局的不同之處在於,後者很容易被理解,我們都知道龐氏騙局是壞的,但即便我們不懂什麼叫區塊鏈,但我們還是覺得應該成為受騙者,因為有一種要麼加入要麼去死的壓力存在。至於Web3究竟是不是騙局則取決於你談論的是廣大新技術生態系統的哪一塊,騙局顯然大量存在(聯邦貿易委員會甚至於公開宣佈存在大量騙局)。
文章進一步寫道,那些說Web3是騙局的人對這個概念充滿了各式各樣的仇恨。上個月當美聯社宣佈將部分照片作為NFT出售時,該決定被描述為“沒骨氣、不道德”,有人叫這家新聞機構“吃屎”。去年秋天,當NFL明星Aaron Rodgers說他將以比特幣的形式支取部分薪酬時,他被抨擊參與了相當於為“洗錢”背書的事情。當“球迷代幣”平臺Socios涉足英超聯賽時,水晶宮隊的球迷在賽場上拉橫幅,上面寫著“道德破產的寄生蟲Socios不受歡迎”。近來反Web3群體在推特上傳播19世紀報紙風格的電子海報,頭條標題是以花體字書寫的NFT糟透了等字眼。在區塊鏈上投資加密貨幣的人被認為是憎恨地球以及支援“一切人類存在的過度金融化”。或者被說成是活該浪費幾百萬美元買數字猴子肖像讓馬克·安德里森變得更富有的貪婪蠢貨,如果不是為了找個掩護討論同意年齡相關法律的怪胎的話。但Web3是個騙局的簡單指控仍然是最常見的批評。在金·卡戴珊因在她的照片牆上宣傳可疑的加密貨幣投資機會而被起訴後,2000年代初出生的青少年肥皂劇明星Ben Mckenzie和記者Jacob Silverman一起為Slate網站寫了一篇文章主張推廣加密貨幣的名人“也可能推廣發薪日貸款或是讓他們的觀眾坐到被操縱的21點牌桌上”。
Kaitlyn Tiffany認為,對於Web3的憤怒與15年前對於次貸危機的憤怒相呼應。該事件暴露出的噁心行為以及隨後的政府救助激發了早期對比特幣的擁抱,比特幣被言之鑿鑿地描述為基於“證據”的金融系統,不同於剛剛令世界陷入巨大混亂的基於“信任”的金融系統。諷刺的是,同樣的歷史事件如今成為了反對Web3的理由,美國財政部的銀行監管人Michael Hsu去年9月在區塊鏈協會的演講上說:“我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夕目睹了一場愚蠢的淘金熱,而我們可能正處在另一場由加密貨幣(掀起的淘金熱)的風口浪尖。”
文章還提到去年一群Reddit使用者連續幾周哄抬GameStop的股價只是為了惹惱所有人(紐約青年共和黨俱樂部令人困惑地以重演佔領華爾街作為回應),他們回想起了2008年的危機,人們仍然對當年的政府救助感到生氣。活躍在Reddit的r/CryptoReality版和r/Buttcoin版的Web3反對者也是如此。在後一個版面中,加密貨幣愛好者被刻板印象化並被嘲笑為“千禧一代男性版本的傳銷人員在臉書上兜售節食奶昔”。但他們也被描述為可預見的崩潰的邪惡工程師,將我們所有人推向一個歷史重演的未來。一名r/Buttcoin版的匿名管理員表示“加密兄弟”在Reddit上到處發連結以及說和持不同意見的人都是傻子的行為非常惱人,這個論壇是他們的掠奪行為的公開檔案。在他看來,崩潰一定會發生,到時候會有很多人假裝自己是受害者,但反對者們認為不能讓他們僥倖逃脫,他們不應該得到救助。
Kaitlyn Tiffany進一步指出,大流行改變了美國人對詐騙的看法。幾年前,在特朗普的任期內,Theranos創始人Elizabeth Holmes正在等待審判,彼時欺詐似乎是一個建立在自立基礎上的社會中的預設行為方式,《紐約客》作者Jia Tolentino在她2019年的暢銷書《魔鏡:對自欺的反思》(Trick Mirror:Reflections on Self Delusion)中將其描述為“決定性的千禧一代精神”。然而過去兩年的無情苦難和驚人的不平等結果出人意料地帶來了對這種心態的糾正。億萬富翁、與社會脫節的名人以及可疑的影響者激發了新的憤怒,他們無法在他人遭受痛苦時行為合宜,並用源源不斷的金錢將自己與最嚴重的疫情隔離開來。人們開始呼籲打擊所有從絕望中牟利的騙子、偽君子和投機分子。
人類歷史上最廣泛的線上肯定在這一逆轉中發揮了作用。在社交網站上,反詐騙運動透過點贊和分享快速升級,和詐騙運動一樣快。反詐騙者的鬥志被令人沮喪的運作方式以及他們對此沒有發言權所激發。對於Web3也是一樣,憤怒似乎來自於這樣一種認識,即普通人可能無法倖免於一場他們既不追隨也不支援的運動帶來的悲劇性結果。當作者詢問以太坊的聯合創始人Wood是否對最近針對Web3的抵制感到驚訝時,他看起來十分鎮定。他說人們只是害怕改變,這沒關係,Web3將和任何重大的社會轉變一樣一波三折,首先是建造者,然後是一群更廣泛的具有影響力的人深入思考如何過自己的生活,如果第二批人接受了重大社會轉變將對他們有利的論點,他們將在很大程度上將剩餘的人拖入其中。但在作者看來,被拖著走是人們尤為痛恨的事情,而這種怨恨正在成為一股它自己的力量。
責任編輯:朱凡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