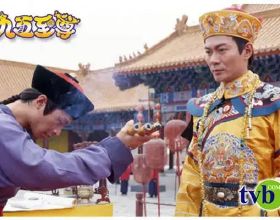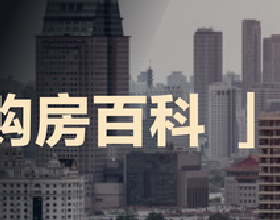真宗朝末年,丁謂趁著真宗病入膏肓,發動政治清洗,將寇準一黨幾乎一網打盡。寇準本人更是被丁謂假傳聖旨,外放至了湖北安州,就在這丁謂權傾朝野、囂張跋扈之時,卻有一人暗自隱忍,等待著扭轉乾坤、澄清朝綱的時機,此人正是王曾。然而在整場寇丁黨政中,始終神隱的王曾為何要與丁謂對立?他又有什麼資本與這北宋的第一位全程對抗呢?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他的父親王兼不懂學問,卻禮敬儒生,並堅定的認為他的兒子是孔子門生曾子的轉世,可惜在王曾八歲的時候,他的父母便早早離世,王曾的叔父王宗元收養了他,待之若親子,王曾也感恩叔父的養育之恩,事之若親父,只是叔父的疼愛也改變不了他們家“出身幽介”的困苦,史載王曾在冬日讀書時,因無錢買棉衣,只能和弟弟背靠背一起通宵讀書,相互用體溫取暖。
上天雖然讓王曾出生在了貧寒的家庭中,卻又給了他異於常人的天賦。王曾拜在鄉先生張震門下學文,張震年過九十,門下弟子甚眾,是當地聞名的經術教授。身經百戰的張教授竟對王曾尤其看重,贊之曰“老矣,未嘗見如是兒,觀其識致宏遠,終任將相。”等王曾長到十五歲時,這天授的才智便能顯現出來,甚至能幫助地方官府妥善調解鄉里之間的土地糾紛,其水準堪比資深居委會大媽,然後王曾就繼續待在老家閉關修煉,直到二十四歲那年破關而出,一舉成為兩宋歷史上第二個連中三元的強者(第一是孫何),這樣的人才出仕,朝廷上下自然要好好地安排起來,宰相李沆和太宗朝狀元呂蒙正,都是識貨的朋友,馬上來了一番熱血的榜下爭婿。真宗、楊億乃至寇準也對王曾投以了極大的重視,先是安排他履任地方,積累行政經驗,王曾歷任將作監丞通判濟州,主判三司戶部案、知制誥。
三十出頭已經是身著紫服的清貴顯官,王曾雖然驟登人生巔峰,卻能始終保持低調作風。他歸鄉時,家鄉地方官要去近郊迎接他,被他婉拒。王曾給叔父寫信時,將自己連中三元的功勞歸功於祖上的功德和叔父的教養,並同時希望叔父不要為此自喜,只當尋常事對待。但過度低調的王曾,骨子裡卻始終是個極有心氣的猛人,翰林學士劉子儀曾調戲他說:“你連中三元,積累的榮耀足夠這輩子吃穿不盡了!”王曾馬上正色回道:“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三十五歲那年,王增先判大理寺,然後又憑藉奇絕的文采和“資質端厚,眉目如畫”的俊美外表,被選為了出使契丹的契丹國主生辰使,契丹方負責接待的是被賜姓耶律的漢人顯貴大臣邢祥,邢祥想要壓宋朝一頭,便自誇遼聖宗經常會賞賜臣子榮耀之至的丹書鐵券,以示君臣協和遠過於宋朝。王曾聽罷,卻是淡淡的回道:鐵券這種東西,難道不是末世限定的道具嗎?一般權臣當朝才會賞賜鐵券,以安定他們圖謀不軌的心思,這東西哪裡會用來賞賜身邊的親近?這番話直接把盛氣凌人的邢祥說得啞口無言,但他仍不甘心,邢祥聽聞王曾是儒者出身,猜他一定沒點武力值,就安排了射箭做餘興活動,又沒料到王曾不但嘴炮好,物理技能也出色,拿起弓箭直接一發直中靶心,四周的遼國大臣盡皆啞然失色。
王曾不但智商高,情商高,連武力值也很不錯,對於這樣的六邊形戰士,真宗當然是當寶一樣對待,拜王曾做大理寺長官時,允許他自闢僚屬,強化了大理寺作為司法部門的獨立性,單獨召見王曾時,怕王曾等久,真宗連衣服都沒換好,就急匆匆接見。大中祥符八年,學士院草詔失誤,把“祭”字寫成了“癸”,在國家下發的檔案上寫錯別字,這不但丟了臉,還引起了大誤會。當時王曾正是翰林學士,結果真宗特意詔劾:“孔目吏決杖,待詔續銅十斤,學士王曾特釋之”皇帝這麼看重,王曾的升官速度猶如坐直升飛機,三十九歲那年便官拜左諫議大夫並參知政事,成為了當朝宰相。皇帝信任,滿朝看重,六邊形戰士王曾眼看著就能主宰乾坤,實現抱負了。但很可惜,他拜相的時間實在不太好。
萬惡的封建社會,皇帝的要素實在佔的比重太大,遇到聖君,能臣自然得展抱負,但遇到昏君,只能抱怨懷才不遇了,王曾是在大中祥符九年九月拜相的,這一年真宗大搞天書封禪已然瞎折騰了快十年,君臣剛相見時,還是明君能成相得益彰,如今時過境遷,臣還是那個能臣,君卻早已暮氣沉沉,迷失在了慾望之中。其實早在真宗封禪之初,王曾便明確表示了反對的態度,甚至上書希望真宗罷造玉清昭應宮,朝中的倖進之人,因此盯上了王曾,他在妹夫孔冕家做客時,竟然遭到了投毒,好在那年頭化學水平不高,本位面的古代劇毒毒性都比較隨緣,王曾沒多久就得到了解毒,孔冕嫌疑極大,但因他是孔子後裔,王曾這個受害者也不願追究,不料大臣王嗣宗卻倒打一耙,反說是王曾愛演,誣陷孔冕,把水越攪越渾,幸得真宗和宰相王旦知曉關節所在,維護了王曾。
其後數年,王曾又因為天書之事被罷了相,接著被外放,王曾認清了自己,他告別了當時已然病重的王旦,出知應天府,只是當時他沒有想到,待他再回來時,朝廷已經物是人非了。王曾在應天府待了半年,正巧當時京中正因一起“冒妖食人”的案件弄得人心惶惶,甚至暗中牽扯到皇子趙受益的儲君之位,向來反感封建迷信的王曾倒能平穩過渡,然後調任天雄軍豐富了一下軍事履歷,就又調回了應天府。
到了天啟四年八月,他便再以禮部侍郎銜重歸參知政事之位,不巧在一個月前,周懷政剛因政變失敗而被處死,寇準等一干太子黨陸續遭到貶黜,王旦與寇準都曾提拔和保護過自己,如今看著這些前輩守護的政治理想將要熄滅,王曾五味雜陳,他自謂可以掌握乾坤,流芳千古,不想重登相位,卻什麼都做不了。寇準和自己擦肩而過,丁謂當著自己的面陷害李迪,王曾也只能默不作聲,勉強自保。就連丁謂趁真宗病重,數度欺君矯詔,他也無能為力。
王曾雖然因反對天書和真宗有了分歧,但君臣間的知遇之情,卻是實打實的。自謂“出身幽介”的他,因“得遇文明”一展宏圖,丁謂卻當著他的面把寇準、楊億、李迪這些曾經提拔甚至看重王曾的當世“文明”一點點碾碎,甚至屢屢欺君,動搖皇太子的地位。王曾雖不比寇準剛烈,但內心的火焰卻從不曾熄滅,他們未竟的事業由王曾來完成,丁謂的命運也將由王增來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