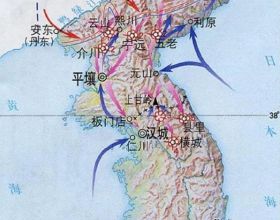出品 | 搜狐健康
作者 | 詹達
稽核|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核醫學科 邱李恆
編輯 | 袁月
這年頭,誰還不趁倆甲狀腺結節呀?
自從龐慧發現自己脖子上有個小疙瘩後,同事們經常打趣她說,不就是上火嘛,撐死了是個甲狀腺結節,這點兒小毛病,有空去看看就是了,實在個頭兒大切了就是了。
……故事好像並沒像龐慧和同事們想象的那樣去發展。2015年8月,龐慧休假時發現,脖子上的疙瘩越來越大了,看著不像上火,該去看病了。
結果讓龐慧目瞪口呆,甲狀腺乳頭狀癌。
癌?是會死的那種嗎?
1.六年前,我只是個甲狀腺小白
龐慧從門診裡出來,像失了魂一樣。排隊準備付費的時候,她才發現自己把錢包落在了門診。
彼時的龐慧對甲狀腺一無所知,一確診就是癌症,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辦。
連著好幾天,龐慧心裡都空落落地,無法接受醫生的診斷。畢竟確診時,龐慧才29歲,在北京的一所高中負責管理宿舍,平常沒有不良嗜好,工作也不會接觸到射線,怎麼會得癌症呢?
龐慧左思右想,突然發覺可能是自己上夜班的緣故。
既來之,則安之。龐慧冷靜下來後開始學習甲狀腺的相關知識,希望能找到最好的治療方式。
甲狀腺是人體非常重要的內分泌器官,形狀像蝴蝶,位於頸前部。甲狀腺病變後,功能受損,會影響激素的分泌,影響到各項器官的正常執行。
甲狀腺癌則是最常見的頭頸部惡性腫瘤,約佔全身惡性腫瘤的1%,包括乳頭狀癌、濾泡狀癌、未分化癌和髓樣癌四種病理型別,其中甲狀腺乳頭狀癌佔比85%-90%,女性患者發病率高於男性。
慶幸的是,甲狀腺乳頭狀癌的惡性程度不高且生長緩慢,術後5年生存率可達90%。
對甲癌有了一定的瞭解後,龐慧揪著的心也慢慢放了下來,更專注地投入治療中。在病友的幫助下選擇醫院和手術醫生,同年9月,她完成了第一次甲狀腺切除手術。
術後,龐慧體內雖然沒有病灶但疑似存留有癌細胞,需要使用碘131進行輔助治療,清除體內疑似存留的癌細胞,避免甲狀腺癌復發。
普通患者術後的治療劑量一般在30mCi(毫居)到100mCi之間。鑑於龐慧的術後指標較高,醫生給她使用了150mCi的碘131進行治療。遺憾的是,這次效果並不理想。
無奈之下,半年後,龐慧再次使用了150mCi的碘131進行治療。
坎的那邊似乎還是坎。龐慧連續使用兩次高劑量的碘131治療仍不見效。
醫生解釋說,這可能是因為龐慧的甲狀腺癌變是基因突變引起的,治療起來更困難。
進行了各種治療後,龐慧的各項指標仍居高不下,這意味著甲癌復發的風險很大。龐慧必須服用劑量更大的左甲狀腺素鈉片來抑制癌細胞的增長,還需要更頻繁地去醫院複查。
每天早上空腹服用兩片半(125微克)的左甲狀腺素鈉片,每三個月複查一次,就這樣堅持四年後,龐慧的脖子還是長了疙瘩。
再去檢查,毫無意外,甲狀腺乳頭狀癌復發了。龐慧不得不接受第二次手術——切除甲狀腺癌復發病灶。
6年間,龐慧經歷了兩次手術、兩次碘131治療,從一個甲狀腺小白成了半個“大夫”,不少病友不懂的也都會向她諮詢。
得了甲狀腺炎,醫生為啥不給我開消炎藥?切右甲狀腺為啥讓我吃左甲狀腺素?查出甲狀腺癌,是不是就活不長了?甲狀腺癌手術後,一定要做碘-131治療嗎?甲癌患者雞蛋能不能吃?肉能不能吃?海帶能不能吃……
病友們的問題五花八門,他們在剛剛確診時,毫無頭緒,有的只是對癌症的恐懼。
患癌6年的龐慧感同身受,她第一次接受手術治療時也是這樣,因為不瞭解甲狀腺癌,所以茫然、焦慮、恐懼、不安。
越慌越亂,越不能解決問題。
每個找來的病友,龐慧都會先安撫他們的情緒,結果怎麼樣不能只看影像學結果,要做穿刺才能定性;給他們科普甲狀腺癌的預後效果;介紹好的治療醫院和醫生;教他們掛號。
在回答病友問題的時候,龐慧漸漸意識到,疾病科普很重要。瞭解疾病不僅能消除恐懼感,還是防治疾病的必修課。
為此,龐慧撰寫了一篇關於低碘飲食的科普文章,向中國醫師協會醫學科學普及分會甲狀腺科普學組投稿。文章中龐慧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訴大家,甲癌患者在碘治療後該如何低碘飲食,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甲癌患者的飲食其實沒有太多的忌口。
2. 一個病房五個甲癌女
2019年年底,龐慧在做第二次切除甲狀腺手術時,結識了四位病友。五個人手術時間差不多,經常聚在一起嘮家常、分享水果、手術前相互鼓勵。
手術結束後,一位病友出現了不良反應。“我當時做完手術也才6個小時,但是夜裡沒有護理,只有我們能幫她。”
手術後需要多喝水。龐慧想起第一次手術剛剛結束時,用吸管喝水還需要有人幫忙扶著吸管,很不方便。這次她便特意為大家準備了運動瓶裝水,放在枕頭邊上,渴了自己就能喝到。
天南海北的五個人,因為疾病相遇。如同姐妹一樣,一起度過了這段特殊的時光。
手術前的一個晚上,龐慧正剝著柚子和她們閒聊著,突然有人提議,我們拍張照片留作紀念吧。
護士說:“哪有在病房裡穿病號服拍照的,多不吉利。”
或許是氛圍到了,五個人笑著拍了她們的第一張合照。
手術後因為疫情,五個人一直都只是在微信上聊天。某天一位病友突然說到:“我們龐老師剝的柚子最甜,每次吃柚子都想你。”
“不如咱們找個時間聚一聚吧。”
時隔一年半,聚會上,五個人以同樣的站位,同樣的姿勢,再次笑著拍了一張合照。
和上次相比,這次的笑容裡多出了一份愜意和一份安心。
“希望我們都能健康地活著。”五人舉杯,為彼此祈福。
3.追問死亡,倒不如想想怎樣活著
“你想過你們其中會有人離開嗎?”
“沒有。”龐慧也擔心過癌症惡化,但擔心是沒有意義的。既來之則安之,如果復發了,去治療就好了。
“與其追問什麼是死亡,倒不如想想怎麼樣才算是活著。”紀錄片《人間世》中,腮腺癌患者王學文的豁達支撐著他在臨終病房裡的五年。
在龐慧與癌共存的這六年裡,樂觀的心態是她驅趕病魔的法寶。
“可能是我太樂觀了,我覺得甲癌對我生活的影響不大。”龐慧甚至覺得自己和普通人的生活沒有什麼區別,就是每天比他們多吃兩片藥,每年多跑幾趟醫院而已。
不過確診後,龐慧的生活作息倒是徹底改變了,變得十分規律。晚上十點休息六點起床吃藥,是龐慧的常態。她還在醫生的指導下透過健身和飲食減重60斤。
現在,龐慧不僅能熟練地解釋什麼是碘131治療,什麼是穿刺,什麼是“清甲”、“清灶”,還能詳細地講出左甲狀腺素鈉片升級後有哪些變化。
這些對龐慧來說,亦是一種收穫。
上次複查時,醫生也說,雖然指標仍不怎麼好,但狀態還不錯。面對隨時都可能復發的癌症,龐慧始終相信著:人在絕境中也要充滿希望,美好的事情就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