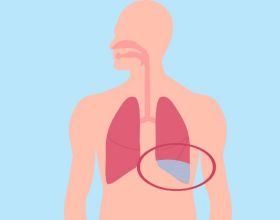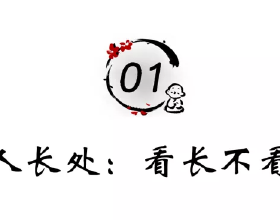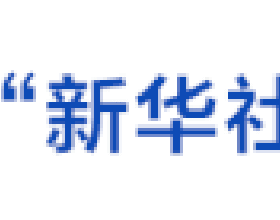從犁芭溝到嘛呢城
說是有一個很遙遠、很蠻荒、很美麗的地方,隱藏著一道神秘的山谷、一條神奇的小溪。那山谷裡,每一塊山石都刻滿了繁複的經書;那溪流裡每一處水流都徜徉著美麗的梵文。
這無疑像某個古老民族的傳說神話,卻確實充滿了誘惑:這會是真的嗎?是誰、又為什麼要耗費如此巨大精力去雕鑿這莫名的工程?
像是被神明昭示,我們為誘惑而苦苦尋找。幾番寒暑,還終於找到了這一處神秘的聖地——那就是青海藏區玉樹州的犁芭溝。
追尋的路誘人而艱難。
汽車在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稀薄的空氣中喘息行進。人和車都顯得疲憊和無助。但窗外的景色令人怦然心動:無垠的草原,天特別藍特別高遠;炊煙、帳篷和散淡的羊群像竹笛吹奏的牧歌,綿長悠遠;瑪呢堆隨處可見,彩色的經幡招搖在太陽下點染著草原亙古的神秘。繞過黃河源頭煙波浩淼的扎林湖、攀越海拔4824米的巴彥喀拉山口,汽車在三江源的腹地彎曲盤旋。就在山窮水復疑無路的時候,轉過山坳,一條大江陡然出現,那就是偉大長江的源頭——浩蕩湍急的通天河。
犁芭溝中清澈的小溪是它不起眼的一條小小支流。走進犁芭溝便像是在翻閱一段遠古的美麗傳奇。
在峽谷的入口,也就是小溪跌入通天河的高坎上立著一座灰褐殘舊的古塔。據傳滿山滿溝都是嘛呢石的犁芭溝就深邃地藏在它的身後。所謂嘛呢石就是那種刻著佛經或六字真言的石頭。這六字真言是“啊嘛呢叭咪哞”,古藏語意即“啊!蓮座上聖佛,奧!”,是一種祈禱和祝福。
入谷口小橋流水很是怡人,但我們在水中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塊嘛呢石,不免有些失望。倒是有一處被經幡圍繞的摩崖石刻,斑駁模糊、年代久遠,令人慨嘆。
再往裡走,則景象漸奇:溪流邊堆砌和散落著大大小小的嘛呢石,有的年代久遠,有的為後人新添;有的形大如鬥,有的小巧精奇。它們散落在溪流邊、灌木下、草叢間,如點點繁星,聖潔璀璨。入谷越深,景象越奇:小橋流水間,野花爛漫處,嘛呢石的體積及密度都驟然增加,令人目不暇接;更有那幾處絕壁摩崖石刻,圓潤的佛像、繁複的經文,令人恍若隔世,不知今夕是何年!
正當我們在流連慨嘆,發思古之幽情之時,前方突起一陣驚叫。我們急切趕去時,知道是犁芭溝的“華彩樂段”出現了。那是在深入峽谷約7公里的地方,兩山夾路,石壁高聳,水流百轉,鳥鳴溪澗。那溪澗中,無數巨大的嘛尼石交錯重疊;那溪流邊的絕壁上,每一處顯露的石頭都齊聲吟哦著“啊嘛呢叭咪哞”。這是一幅無聲勝有聲的壯麗祈禱圖,那裡響徹的是千年不絕的天籟之音。我們雖然完全不明白那些詭秘梵文所昭示的意義,但我們的疲勞被穿越山谷的清風一掃而盡,我們莫名的煩惱被繞過嘛尼石的清流梳爬洗滌,我們浮躁的心在這天籟之音中變得安妥澄明。我們模糊地想,也許這就是信仰的意義。
奇蹟讓我們重新回到最初的探究:是誰、又為什麼要耗費如此巨大精力去雕鑿這莫名的工程?
犁芭溝有一處唯一的小小村落,十數戶人家散落在高山下。我們在村外小溪邊見到了一位石刻老藝人。他雕刻得那樣嫻熟那樣精心,似乎圍觀的我們根本不存在。只有當我們多次提問,他才抬起頭,微微一笑。他的身邊圍繞著大小不等的紅色石頭。他說他給別人刻了大半輩子嘛尼石,今年已經58歲了,該給自己好好刻一套石頭經書了。每一套經書有144章,以他那樣嫻熟的技藝也得花3個多月的時間,刻成後會有大小嘛尼石數千塊,體積大約兩個立方。他說,他的石刻技藝是祖輩傳下來的,這裡的石刻世家遠祖大約可以追溯到唐太宗貞觀年間。
犁芭溝從地理位置上說是青海與西藏的交合處,史稱唐蕃古道,是當年入藏的三大通道之一。當年文成公主和親遠嫁,松贊崗布親往相迎,到玉樹見此地景色優美,便命休整月餘。當時大唐佛教盛行,而藏地無佛,為弘揚大唐文化,弘揚佛法精義,文成公主隨身帶了佛像、佛經、佛塔。休整期間,她讓隨同工匠們在即將穿越的峽谷犁芭溝兩山的石壁上鐫刻佛像及經書,這裡從此成為了藏民們心中的聖地。
這裡曾是唐僧西天取經返回途中晾曬經書的地方,當地的藏民也許是最早親睹佛經的族類,他們在山石上不斷鏤刻下佛經裡的六字真言,鏤刻下自己的虔誠。山崖是那麼的高那麼的陡峭,先輩們就用牛糞冰結成的天梯攀上絕壁鐫刻。一年又一年,山岩上刻滿了,就刻進了溪流裡。一代又一代,這“山嘛呢,水嘛呢”的偉大神秘壯觀便在綿綿無盡的電火石光中誕生了。
關於為什麼要為自己刻一套經書,老人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只是說,你們去玉樹看看新寨嘛尼城也許就不會問我為什麼了,那是一座由25億塊嘛尼石堆砌成的巨大城池。
我們趕到新寨,眼前的景象著實讓人震撼。
這是一座像足球場般大小的城池,城高兩三米,面積不算大,但它全部是由一塊塊嘛尼石圍著一座寺院堆疊而成。這些石塊,也許確實有25億之多;也許應該比這更多,因為我們看到人們還在不停歇地往上堆砌。新寨村的村民幾乎家家以打刻嘛尼石為生,包括外來石刻匠,如今已超過500人日夜雕鑿,仍然供不應求。
據傳自從第一世嘉那活佛晚年定居新寨在這裡疊起第一個小小嘛尼堆起,300年間藏民和信眾們就從未停歇過他們的新增堆砌。他們把自己的祝願、虔誠、希望,一個一個地堆砌,經年累月,從不停息。陽光下的金頂每天都那樣輝煌,寺廟裡酥油燈如繁星閃亮,嘛尼城外轉經的人流心懷虔誠,如鯽魚過江……
生活在高原上的藏民生活簡樸,臉上卻永遠掛著自得的笑容。如今這些以牧業為主的康巴人有些也很富有了:家家百十頭犛牛和羊,許多都成了“百萬富翁”,身上佩戴的瑪瑙一顆就值三、四千塊。但他們樂天知命,不顯擺、不揮霍、不驕奢。他們並不把幸福構築在金錢之上。只要生命不息,他們就永遠在高原上策馬飛馳;只要喉嚨不破,他們就永遠在綠茵間勁舞酣歌。他們有虔誠的信仰:轉動一次經輪便是誦讀過一遍經書;繞著嘛尼城走三圈,你就會吉祥、幸福、平安。他們還借清風翻動經卷,借來流水誦讀經文,借山石鐫刻心願——每一形式的誦讀都傾注著他們的虔誠。在嘛尼堆邊長大的孩子,信仰從小便根植在他們的心靈。老阿爸老阿媽的轉經,清晨第一縷陽光之前就開始了,他們就這麼在佛光中從容地走過一輩子。
關於藏民族的信仰,有這樣一首歌,每次聽到都很感動。
那一月 我搖動所有的經筒,
不為超度,只為觸控你的指尖;
那一年 ,磕長頭在山路,
不為覲見,只為貼著你的溫暖;
那一世, 轉山,
不為修來世,只為途中與你相見。
據傳這是六世達賴倉央嘉措最傳世的一首情歌,他深信逝去的戀人會重生,靠自己的摯情和虔誠便能與她相逢。其情其音宛如西藏雪山的泉水,純淨透明、千廻百轉……
對久居喧囂塵世的人來說,這歌真的就象雪山上的泉水潺潺流進我們的心田,沁人心脾。信仰令人執著、從容。不管外界多麼紛繁複雜,內心始終平靜如砥,愛情始終明澈快意——這是倉央嘉措給予我們的啟示,也是我們愛他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