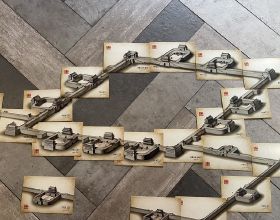千年衛河,溫婉如玉一般地流過浚縣,一路向北。嘉慶年間,衛河之畔,住著一對貧困母子,母親李崔氏,三十來歲,徐娘半老,和年僅六歲的兒子李恆之相依為命。
李家原是城中富戶,家資頗豐。李恆之的父親李存孝是城中有名的浪蕩公子哥,不務正業,貪慕風流。其父母亡故後,他舊習難改,依舊在外和多名暗娼有染。後又沾上賭博,崔氏苦勸不聽,反遭其打罵虐待。總想不勞而獲的他終被人設局欠下了鉅額賭資,五年前留下書信一封,將妻、子、家產全部抵債後不辭而別,只說無顏見人,外出生計,實則是逃亡他鄉躲債,至今音訊皆無,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這崔氏是村中的私塾先生——崔秀才之女,閨名笑梅,清秀端莊,從小受其父薰陶,頗通詩書禮儀。丈夫的無情拋棄,令她肝腸寸斷,本想一死了之,但想起可憐的兒子孤苦無依,終打消了輕生的念頭,恨過、哭過之後,帶著兒子回了孃家。
後由其父出面,聯合縣中諸生員調停,逼迫債主們讓步,李家祖宅、田產,包括崔氏嫁妝在內,全部抵債具結,總算還了崔氏母子一個自由之身。崔氏本可再嫁,但其被男人傷透了心,不聽父母之勸,堅決搬離母家,和兒子租住在這河邊小院,靠幫人縫縫補補為生。
崔氏守寡熬兒,心血全部傾注在兒子身上,小小年紀將其送進外祖的私塾讀書,一心想讓他博取功名,讀書入仕。恆之雖幼,也知人乃父母所生,曾詢問崔氏父親去向,崔氏告之,你父早年病亡。恆之知母親一人艱辛,皆是自己所累,更是非常用功。天資聰穎的他,沒有辜負母親期望,十二歲時,便在童生試中嶄露頭角。道光四年,十六歲的李恆之考中秀才,大放異彩,眾鄰及親朋紛紛道賀,他自己也甚是得意,更成為其外祖一生津津樂道誇耀的資本。
然而,科考對於古代學子來說,其中的艱難遠非常人所能想象的。大多數人,窮其一生連個秀才功名都撈不到,院試中頭髮花白的童生比比皆是。李恆之此時正年少得志,恰又逢三年一次的秋闈,在其外祖的鼓勵之下,李恆之躊躇滿志,滿懷希望地趕赴開封貢院參加鄉試。然而,妙筆生華計程車子多如牛毛,中舉者又能有幾人?李恆之的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乘興而去,灰頭土臉而歸。
歲月和等待最易磨平人的稜角,等他寒窗苦讀三年,再次即將迎來鄉試之期時,其外祖業已去世,再無人誇誇其談為其打氣,他心中焦慮難安,怕自己再次落榜,更害怕母親失望的眼神,整宿整宿地睡不著覺,索性提前半月動身,欲沿途順便散散心。
不想,卻在船上感染了風寒,病倒在了衛輝西碼頭的同福客棧。俗語說“病來如山倒。”一點不假,李恆之頭痛欲裂、發熱昏迷,迷迷糊糊中只覺一雙母親般溫柔的手,為自己不斷地換下額上敷著的毛巾,喂自己吃藥、喝水。原來,好心的老闆娘柳氏知他是應試的學子,病倒在外著實可憐,便吩咐女兒慧娘為其請醫救治、照顧有加。
恆之昏迷兩日,醒來之後,乍見一雙妙目注視著自己,頓覺心跳加速,尷尬不已。恆之長這麼大,第一次和女孩近距離接觸,而且還是如此漂亮的女孩,心底湧起一種難以名狀的甜蜜和喜悅。慧娘見其醒來,始含羞告退。原來,這店主人李同福五年前癆病去世,只剩這母女倆經營這間客棧,勉強度日,柳氏腿腳有風寒痼疾,慧娘便忙裡忙外張羅。古代文獻中常有未嫁之女長在深閨,很少拋頭露面,那是泛指的富貴豪門,市井貧家,待在家中不勞作的話,還不得餓死?
恆之病了十多日,慧娘照顧了十多日,不知不覺中,兩人暗生情愫,大有相見恨晚之感。情之一事,實是令人難以言喻,分開一會兒,便覺牽腸掛肚,四目相顧,便知對方心意。然鄉試之期臨近,李恆之不得不辭別慧娘,定下歸期,赴省城應試。那柳氏是過來人,豈會看不出女兒心意?然自家貧賤,高攀秀才之門,古時又講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不知其家裡人會是什麼態度,不便過多表露。
貢院的考試很快結束,李恆之因病耽擱了些時日不說,科考本就是萬千學子爭搶透過的獨木橋,哪有那麼容易金榜題名?李恆之依然名落孫山,他垂頭喪氣離開省城,趕回了慧孃家的同福客棧。
聽其落榜,慧娘少不了一番細語安慰,恆之像個聽話的孩子唯唯諾諾。躲在樓梯拐角處偷聽的柳氏差點笑出聲來。她對恆之現在是“丈母孃看女婿,越看越喜歡。”遂藉故委婉打聽恆之的家庭情況,並示意自己有意將女兒許之。恆之自是心中高興,但表示要回家稟知母親,再來迎娶慧娘,並取下頸中長命鎖交給柳氏為證,柳氏取來慧娘父親遺留的玉戒一枚回贈。接下來的事,比想象之中順利得多。崔氏怕兒子再次落榜一蹶不振,不料,兒子並沒放在心上,卻提出成婚的打算,並將慧娘之事稟知母親。
兒子已到婚齡,崔氏也正有此意,但看到兒子交給自己的那枚玉戒後,不禁一愣,眼神犀利,臉龐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猙獰。很快又恢復常態,詳細盤問了慧孃家的情況。恆之初見母親臉色有異,又盤問慧娘底細,害怕母親嫌其配不上自己,沒想到母親並無阻攔,很爽快地應下了這門婚事。
道光八年(1828)春,李恆之在其經商的舅舅操持下,和慧娘舉行了婚禮,兩個有情人喜結連理,自是分外甜蜜繾綣。但崔氏的態度卻令人大感意外,自從慧娘進門,常被其無端刁難,動輒責罰打罵。無辜的慧娘無論怎麼奉迎討好,都似乎難解婆婆恨意。恆之為妻鳴不平,母親便罵其仵逆不孝,罵慧娘居家不賢,挑唆滋事,讓其跪在旁邊,用藤條抽打慧娘。事後,兩人相擁而泣,恆之始終想不通,母親何以如此對待慧娘?
不堪其辱的慧娘,終在那年秋天的一個晚上,趁李恆之熟睡之際,穿戴得整整齊齊懸樑自縊。待恆之醒來,已氣絕多時,李恆之椎心泣血,痛斷了肝腸。
訊息報於柳氏,柳氏趕來看到女兒慘狀,號哭著追問女兒死因,恆之無言以對。柳氏怒將李恆之告到了縣衙,懷疑其謀殺了自己女兒慧娘,求知縣大人為自己做主,查出慧娘死因,還自己一個公道。
時任知縣是嘉慶六年進士,年已五十二歲的朱鳳森,接下此案的朱知縣,立即將生員李恆之拘捕,並親到現場勘驗了慧娘之屍。堂審之時,崔氏不拘自到,跪地坦白慧娘是被自己虐待逼迫而死,與兒子李恆之沒有任何關係。朱知縣追問緣由,崔氏始一一道來:兒子二次赴考不第,回來之後和自己商議婚事,交給自己保管和慧娘交換的定情信物,那枚玉戒,本是自己之物,是自己當年送給丈夫李存孝的定親之物,那應是他出走之時,身上唯一值點錢的東西了,自己當時就懷疑所謂的李同福就是李存孝。
他無情無義,用妻子兒子抵債,害自己半生守寡,恨不得生食其肉。但他已死,自己胸中這口惡氣只好出在他女兒身上。自己明知二人極有可能是親兄妹,依然沒有點破,終使慧娘嫁入了己家,聽她所述其父形狀,不是那該死一萬次的李存孝又是何人。自己看到慧娘就像看到了李存孝,所以才對其打罵虐待,只是沒想到她會自縊而死。如今,事已至此,自己抵她一命便了。說罷,不知往嘴裡吞了什麼,李恆之急上前去奪,卻早已順其喉而下。她用手摸著兒子的臉,只說了一句:“兒啊!娘對不起你。”便癱在堂上,七竅流血而亡,李恆之抱著母親號啕大哭。
案子審到這種程度,朱知縣也是無語,李恆之不知者無罪,其母有罪卻已自戕。法不責死人,朱知縣釋了李恆之,命其回家為母辦喪後,將慧娘運回衛輝府安葬,解除這段違背倫理的婚姻,照顧柳氏只到終老。宣告結案。
星君思考:
母愛無私嗎?母愛,是人類一個亙古不變的主題,是世上最博大、最無私的情懷。即便是人心浮躁、物慾橫流的今天,它仍是唯一沒被名利汙染的一方淨土。至於本案中的母親崔氏,亳無疑問,也算是位偉大的母親,只是被仇恨迷失了心智,長期孤獨終使其心理畸形,不顧“倫喪德失,陷子無禮。”而被世人詬病了兩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