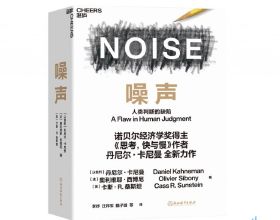瓦房戰鬥一直到天黑才結束
一九三八年七月的一天,大概已是夜裡十二點多了,同志們來到了事戰士。
我們抗聯三軍一師師部和一個連隊原來有七十人,現在連輕重傷員只剩下九人了。
部隊除了部分被衝散或者被俘之外,其餘大部分在激戰中壯烈犧牲了。
這個料想不到的嚴重損失,使得師長和我們幾個僥倖留下來的同志,萬分悲痛。
次日,天剛矇矇亮,常師長領著我們,把戰友們的屍體掩埋起來,圍著新築起的墳墓,肅穆地站著流著淚。
常師長聲調十分低沉地說:“這些戰友們沒有實現‘跨過鬆花江,打到嶺西去’的願望,我們活著的人,一定要踏著烈士們的血跡,跨過江去,參加西征大軍,到小興安嶺西去開闢新的游擊區,消滅日寇,為烈士們報仇!”
我們沉痛地向烈士們行了最後的告別禮,隨即按照軍部的命令,趕往江北西征指揮部。
天陰得很重,大概早上七點多鐘了,還沒見到太陽。然而,七月的北滿正值盛夏,即使太陽被厚厚的烏雲遮住,天氣也還是很熱的。
常師長領著於參謀、趙分隊長等九人,輕傷扶著重傷,沒受傷的揹著戰友們的槍彈,揹包加上在戰場上割下來的死馬肉,每人負重足有七八十斤,一歪一跛地在荊棘中向松花江下游的羅羅密渡口奔去。
天熱,傷痛,負載重,路難走,加上勞累和飢渴,我們走上十來分鐘,就要停下來喘喘,喝點塘子裡的汙水,再支撐著前進。
常師長腰部負傷,流了很多血,又一再拒絕別人扶他走,漸漸地支援不住,昏倒了。
當時我還不滿十七歲,剛上隊四個多月,也許真的是因為“女孩子家心腸軟,感情脆弱”的緣故,見到師長處於這麼危險的狀態,我哭了,不加控制地哭了!
我背向著師長蹲在一旁,邊哭邊想:常師長是抗聯三軍的創始人之一,七八年的反滿抗日鬥爭,在他健壯的身軀上,留下了二十餘處可怕的彈痕,十個腳趾被打掉七個。但是,這絲毫也沒動搖他的意志,削弱他的銳氣。
他常自豪地對同志們說:“我常有鈞雖然腳瘸了,殘廢了,但是我的心永遠不會殘廢的!”十幾分鍾之後,由於同志們的搶救,常師長總算清醒過來了。
為了爭取在規定的時間內渡江,他又命令我們繼續前進。
天越陰越重,我們又走了一段路,便下起了傾盆大雨。這是在遠離人煙的森林裡,我們只有把傷員同志背到大樹下去躲雨。誰都知道樹是擋不了多少雨的。
我和“大力士”趙分隊長,趕忙扒下幾大塊樹皮給傷員蓋上傷口。
雨,整整下了一個下午,天黑時才轉晴。大夥已經一天半沒吃東西了,連累帶餓,真是寸步難行。
常師長便下令就地宿營搞些吃的。我們已經沒有一粒糧食,只好把死馬肉放在鋼盔裡煮煮當飯吃。沒有乾柴,火燃不起焰,同志們便啃起半生不熟的馬肉來。
負傷,淋雨,吃不熟的死馬肉,喝生水,蚊蟲叮咬……種種的折磨,使得師長和所有傷員染上了瘧疾,行軍無法繼續了。
常師長只好派趙分隊長和通訊員到羅羅密渡口去找接應我們渡江的馮仲雲主任帶領的部隊。
趙分隊長和通訊員走了三天還沒回來,同志們的傷病越發惡化,更嚴重的是馬肉已經吃光,而且只剩我一個人沒生病。
於是,我到處去採野白菜、老山芹煮給傷員們吃,晚上就燒水給他們洗傷口。
忽然傷口潰爛最厲害的傷員老劉同志猛坐起來,右手握緊師長的手,左手抓撓著自己的胸膛,央求道:“不要為顧及我而影響革命事業,我請求您一我的好首長,您就舍給我一顆子彈吧!”
老劉同志要求師長打死他,這使人多傷心呀!我們幾個人抱頭大哭起來。
就在我們傷心地哭泣時,我無意中抬頭看見於參謀正在用剃頭刀子,一塊塊削去自己胳臂上因負傷而潰爛的腐肉。
他咬緊牙齒,睜大了眼,皺緊眉頭,滿頭汗水,但是一聲不響。
我心疼加上害怕,立即閉上淚如泉湧的兩眼,用肘頭抵了抵師長,艱難地向師長說:“你看……於參謀!”
師長和老劉同志同時把臉轉向於參謀,投去驚訝和敬佩的目光。
知識分子出身的青年共產黨員於參謀,在血肉模糊的傷口上,抹上點草藥膏,順手扯下一塊衣襟包紮上,然後才抬起頭來,望著常師長和我們,微微點點頭。
師長扶著老劉,在於參謀身邊坐下來,兩眼凝視著老劉。然後,他一隻手按著於參謀的肩頭,另一手握緊老劉同志的手,兩眼望著遠方,語調深沉,但是充滿著力量地說:“同志!我們共產黨員,就要像於參謀這樣經得起殘酷的考驗!我的好同志!讓我們堅持活著吧!活著,我們就能消滅敵人!活著我們的革命事業就能夠勝利!”
然而,我們的老劉同志剛剛點點頭,表示對師長的感激,就昏過去了。
我急忙把僅有的不幾十毫升的急救水,給老劉同志灌進幾滴,又用沾涼水的毛巾給他敷敷前額,他才又慢慢清醒過來。天又黑了,趙分隊長仍然杳無音信。
常師長小聲對我說:“趙分隊長一定是遇到了不幸,如果今天夜裡他還不來,小張(當時我改姓張),那你就得出差了!”
“我!哪去?”
我問,“我走了,你們怎麼辦?”
“到瓦房去拾幾匹馬來,那裡一定還有活著的馬。”
師長嘆了口氣說,“只要你回來得快,我們的生命就有保障!”
已經是深夜了,月亮被一片夜雲遮住,不明不暗。同志們都迷迷糊糊地躺著,只有師長不安靜地翻來覆去。
我拿著手槍坐在師長身旁,警惕地張望著,聽著周圍的動靜。忽然,有腳步聲由遠漸近。
我急忙推了一下師長,告訴他:“你聽,腳步聲!是趙分隊長回來了吧?”
“很可能!”師長振奮起來,但他卻又馬上警惕地說,“不過小張你要當心,這也可能是敵人的‘討伐’隊呀!”
隨著腳步聲的逼近,我發現來者並不像人,而是一個體大如牛的黑糊糊的東西。
常師長一眼就認出這是個“黑瞎子”(熊)。他以釋出戰鬥命令的口吻向我說:“快把子彈推上膛去,這東西禍害人!”
常師長在森林裡過了七八年,他不但有對敵鬥爭的豐富經驗,而且也有與野獸交鋒的高強本領。
他和“黑瞎子”圍著大樹轉了兩圈,便機靈地向著另一株大樹後面一躲閃,乘“黑瞎子”向他迎面追來,對準“黑瞎子”的腦門“砰砰砰砰”連開數槍,這隻大得使人心驚肉跳的黑熊倒在地上了。
我們和“黑瞎子”的這場緊張的搏鬥剛結束,忽然又聽到有馬蹄聲由遠漸近。
我說:“這回可能是趙分隊長帶人來了吧!”
“不!”師長很肯定地搖搖頭說,“這才可能是敵人呢!我們剛才打‘黑瞎子’,讓敵人聽到了槍聲。”
他當機立斷:“轉移!”
我很快地把傷員一個個背到溪邊的深草叢中藏起來。當我來背最後一個傷員時,來人離我只有幾十步遠了,並且喝令我“站住!”“站住!”
來人又喊叫一聲。我聽得出是趙分隊長的聲音,卻又不敢相信是他。
我看反正是逃不脫了,就把傷員放下來,把槍握在手裡,準備著萬一要是敵人,就先幹掉幾個,然後再給自己一槍。
我剛站住,就聽來人說道:“我們是抗聯,你趕快放下我們的人!”
“是趙分隊長!”我激動地自語著。
“你是小張?”
趙分隊長跳下馬來,抓住我的手問:“為什麼剛才有槍聲?師長他們哪裡去了?”
我哪裡還能說出話來呢!只用手指了指那個被打死的“黑瞎子”,然後,不聲不響地把他帶到師長和傷員隱蔽的地方去。
第二天太陽剛出來的時候,我們圍在一起吃著又肥又香的黑熊肉。趙分隊長向師長報告偵察的情形。
他說:“我們不分晝夜地跑到了羅羅密,找來找去,連部隊的影子也沒發現,但是,發現一棵樹上刻著‘此處虎穴,不宜久留!’字樣,接著又有幾棵樹上刻著‘偵察人員對這是不外行的’。我判斷這是自己人在告訴我們,羅羅密渡口一帶很危險,他們已被迫離去,並要我們到了後,也萬不可待得太久!我們又繼續從林子向江邊走去,在一個小木房旁邊,我們發現一個手拄柺杖的五十來歲的獨腿老人,關於這個人師長您是非常熟悉他的。”
“對!他是我們的聯絡員,姓何。”師長又問,“他怎麼樣了?”
接著趙分隊長把老漢告訴他的關於羅羅密一帶的情形詳細地敘述一遍。
原來,我們從羅羅密渡口過江的訊息,在五天前的瓦房戰鬥時,敵人就已知道了。於是,他們就從佳木斯開來一艘軍艦,並有兩三百敵軍,堵住了這個我們必經的渡口。
趙分隊長說:“老何頭信心百倍地讓我們趕快把常師長和同志們領來,說一定設法讓你們過江!”
“這馬是何老爺子送的嗎?”我也插嘴問了一句。
“不!老漢獨自住在那遠離人煙的江邊林子裡,他哪裡有這馬給我們呢?”
趙分隊長說,“我們很快從老何頭家裡往回走,在路上我想起你們沒吃的,傷病一定也更加惡化了,即使我們先到這兒來,也不能馬上讓同志們擺脫危險的處境,於是便跑到瓦房戰場上去,從戰場上撿到了這馬。”
他喘了一口氣說:“不光撿到了馬,而且還撿來不少的藥品呢!”
聽說有藥,大家都高興得幾乎忘掉了傷痛。
師長對藥是不外行的,他一瓶瓶一包包拿在手裡說:“嗬!可真全呀!碘酒、紅汞、盤尼西林、急救水、奎寧和治療槍傷的黑藥膏……全是日本貨!這回同志們算有救了。”
我們趕到江邊林子裡,在老何頭的草垛裡躲了整整十天。
雖然悶熱的盛夏,捂在草垛裡不是滋味,但由於吃得飽、睡得著,傷病有藥治療,晚上還能出來透透風,所以同志們的病很快治癒,傷口也接近痊癒。
七月二十七日晚上,月白風清。何老爺子拄著柺杖從幾十裡以外的屯子趕回來。
已是晚上九點多了,但他仍和往常一樣,不顧勞累地為我們張羅吃的。待他把一切收拾停當,已是深夜十一點左右了。
按照他的安排,只要一遇上陰天下雨的黑夜,我們就要渡江了。
這天晚上,何老爺子懷著惜別的心情,和我們一直嘮到凌晨一點。
最後,他加重語氣告訴我們說:“我們革命者活著的最大希望,就是想親眼看到日本鬼子從我們中國的土地上滾出去。”
我們控制著激動的心情向老漢保證:“我們一定積極勇敢地打擊日本鬼子,讓您很快就看到勝利!”
“我謝謝同志們!”何老漢寬慰地點點頭。
恰巧第二天就是大陰天,夜裡十二點左右風雨大作。不一會兒,兩個漁民老鄉便把小漁船劃到了渡口。我們懷著無限感激的心情,握緊何老爺子的手,向他告別。
常師長還和他緊緊地擁抱,告訴他:“不要多久,我們就會回來看你的!”
老爺子也高興地回答:“我一定等著你們,祝你們西征勝利!”
這隻船隻能載六人,現在連漁民老鄉已經十一人了,為了使小船負載減輕,划行速度儘量快些,我們只讓一位船主給我們掌舵,另一位留在何老爺子家裡等候。
大概是凌晨一點鐘,雨雖小了些,風卻愈來愈大,我們的渡江小船出發了。
小船剛到江心,敵人的小巡邏艇就出動了。我們拼命地向著和敵艦偏斜三里的岸邊劃去。
只聽到敵人在何老爺子家附近“砰砰”打了兩槍。不一會兒,敵人小巡邏艇便朝著我們的小船駛來。
為了減輕小船的負載,加快滑速,會鳧水的同志,都跳進江裡向岸邊游去。
這時,傷勢太重的老劉,兩手支撐著右腿蹲在舢板上,看看追敵已經不遠,他大聲喊道:“為了不拖累大家,同志們,永別了!”
隨著喊聲撲進滾滾的江流,被松花江無情的巨浪捲走了!此刻我們離江岸不足百米遠,船上因為人少,也劃得更快了。
待敵艇逼近並向我們開槍的時候,我們已經鑽到江邊山林子裡去了。
恰好這裡有接應我們過江的一師的另一部分部隊,他們和追敵接上了火。
戰鬥只十幾分鍾就結束了。接應我們的部隊,把一個剛從江裡上來的人帶過來,原來他就是那位留在何老爺子家等候的漁民老鄉。
常師長焦急地問:“何老爺子呢?”“他……”
漁民抹去眼淚說,“敵人在何老爺子家發現你們丟下的東西,就毒打了他幾巴掌。老何頭遂破口大罵日寇和漢奸,並且舉起柺杖狠狠地揍了那個打他耳光的敵人。敵人就開槍打死了他。我是乘機跳進江裡逃過來的。”
這時常師長和同志們都站起來,脫掉帽子,看著滾滾的松花江水,望向何老爺子那座立在松花江邊的木房子,很久很久默默無語。
邢德範,抗聯三軍被服廠戰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