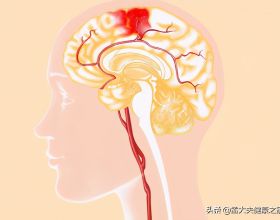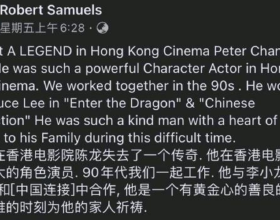以往的每年,我都是在家裡度過這個於我家而言最有儀式感的節日,在我心裡,其他所有節日似乎都比不上春節重要,因為它在我們家最像是一個節日。我們總是說不記得自己有多少年沒有怎麼怎麼樣了,我卻清楚的記得自己那年在讀初一,弟弟比我小兩歲,他該是還在讀五年級。在此之前,我們的家庭不算富裕卻還算“和諧”,父母雖有爭吵甚至急了也會幹架,但是沒心沒肺的我卻依然是快樂的。
那時,過年是快樂與希望,到處都是年味。每年過年前一個禮拜,母親便會把家裡裡裡外外都清掃一遍,儘管她是一個有潔癖的傳統中國婦女,家裡總是保持的乾淨整潔,但是年關前一個禮拜的大掃除,依然每年雷打不動。後來經濟條件好些的時候,每年過年還能得到一套新衣服,有一年我得了一件牛仔外套,現在衣服已經找不到了,但是我卻依然記得它大致的款式;到了除夕那一天,我們一家人總是整整齊齊地看聯歡晚會,小孩子熬不了夜,總是早早就睡著了,連晚上十二點的鞭炮聲都不能將我吵醒;第二天的大年初一,我早早便起床了,從房間外弧形的小陽臺一眼望下去,街上紅紅火火,雖無一人,卻感覺熱鬧極了,偶爾下雪的年份裡,紅色的鞭炮屑更是夾雜在一片雪白裡,街上連綿一片,那點綴著“紅梅”的雪景就成了春節獨有的景緻。那時候的房子是租來的,但是那個小小的陽臺卻給了我極大的歡樂,我愛陽臺外昏暗的路燈,它照耀著我的房間,給我安全感,那時車少,昏暗的光線與靜謐的夜晚直到現在還讓我時常懷念。我更愛站在陽臺上感受下雪天裡雪花向下飄零,一片連著一片,在黑夜裡路燈的照射下散發耀眼的光芒,似星星般將我包裹起來,幼稚的我總是喜歡張開雙臂,享受雪花飄落帶給我似仙子般飛昇的快樂;記憶裡,大年初一上午開始,等到了大人陸陸續續都起來剷雪的時候,我的父母或帶著我們姐弟回鄉下過年,或等到近中午時分開始走親戚,那時候總是各家去一整天,我們表兄弟姊妹見面,總是打打鬧鬧,那時我們四五個年齡相近的孩子,愛完捉迷藏,愛完大富翁,今天在你家玩,明天去我家玩,每一天晚上十一二點大人們打完麻將結束這一天的時候,我總是不忍分別,等到了假期過了,更不忍年這麼快結束了。
後來過年,母親依然會大掃除,吃的穿的都比以前好了許多,由於家裡有了自己的房子,我失去了那個小陽臺,搬到了城郊住,沒有了“明晃晃”的路燈,黑夜總是讓我缺乏安全感。由於父親的關係,他不再跟母親這邊的親戚往來,於是每年大年初一,當母親要去舅舅家的時候,父親不去,有時甚至阻止母親去,而母親卻總是堅持要父親去,兩個人誰也不讓步,而每年總是以母親的失敗告終,從此以後,“年”在我心中彷彿就代表著母親的不快與失望,代表著父親的固執與無情。那時我已開始慢慢懂事,父親的行為讓我感到自卑,雖然舅舅們沒有和我的父親計較,我卻依然覺得自己抬不起頭來,再加上我們表兄弟姊妹們相繼上初中了,年齡、課業與我自己心態的轉變,記憶裡再也沒有一起打鬧的場景了,我們姐弟更加沉默寡言,總是匆匆吃完飯,便嚷吵著要回家,於母親心中而言,我們姐弟的做法可能也讓她心寒吧。自此,年味便淡了許多,甚至再後來更多的是害怕與恐懼,因為知道每年這個時候,家裡少不了一場大戰,將母親的希望落實為失望。
今年一人在外,父母問了幾次什麼時候回家過年,等我終於拿起手機給他們說不回家過年的時候,眼淚便再也止不住,心中多年的委屈一湧而出,委屈於我們姐弟在家的時候從沒好好過年,我們不在的時候,他們卻希望我們回去。但我又深感自己不孝,心裡更是覺得自己怕是越來越無情了。我覺得自己心裡住著善良與無情兩個小人,以前那個善良的小人,會看到奶奶辛苦提著西瓜來看我們的時候,在心裡說自己願意少活十年,讓奶奶身體健康多活十年。現在這個無情的小人總是“自私”地指使我逃離原生家庭,不厭其煩地嘗試擠走我體諒父母艱辛的良知。無情小人一遍遍嘗試打敗善良小人,我不敢問問母親今年是否依然大掃除了,我害怕自己破壞了家裡僅存的一點年味。
然而,在所有的傳統節日裡,我最愛的還是春節,因為在我們的傳統文化裡,它意味著辭舊迎新,我始終認為這是一個忘記過去,重新開始,努力獲得新生的契機。就像我的母親,明知父親不可能去她那邊的親戚家走動,卻每年依然不放棄,甚至不惜以吵架和打架為代價,以期希望成真。於我而言,遊子在外,今年我卻希望有自己的“年味”,精心裝飾的出租屋,紅紅火火的掛件,辭舊迎新。我更希望往後的每一年,單身的時候有單身的“年味”,成家後有家庭的“年味”,再貪心一點,給原生家庭帶去“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