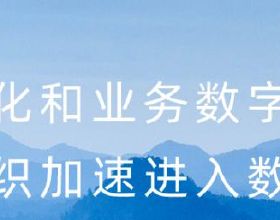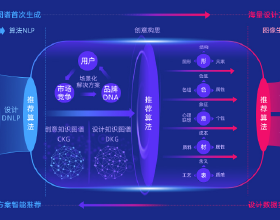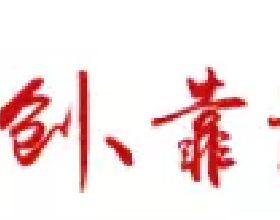這幾年的每一次過年,都有些大事發生。
前年,奶奶去世了,去年,我爆發了一場大抑鬱。
每一個都鬧得聲勢浩大,每一個到最後都莫名結束。
今年年前我就等著這場年,顯然我已經發覺了這七天假期的不普通,認真盤了最近能引起情緒風暴的幾個點,好像也沒啥。
今年這個年過得毫不感知,幾乎是一眨眼就過去了。年味越來越淡這一點,也不贅述了吧。
過完年之後依然能發現自己的年後綜合徵十分嚴重,主要表現為無心工作,無精打采,無力生活。
每天早晨一睜眼,想的是早餐吃什麼,略想到早餐後要面對的長時間的坐班以及從前天堆到昨天再累積到今天的工作,那種絕望,無法言說。
到底是為什麼呢?沒想通。看到一個說法,是因為春節熱鬧、隆重,家人環繞讓人重回孩童身份。吃完飯理所當然地甩筷子走人,不開心就撒嬌,不滿意就耍賴,幸運是父母長輩皆在,放心做無賴。
另外,也是因為回家本身就是一件讓人心中暗潮洶湧的事,雖然人沒變,但景變得太快。
我家所在的小區已經幾經變革,幼兒園變成了居委會,老人聚居區變成了新公寓,陪伴我20多年的菜市街坊通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整齊重新整理一致的街區,老小區改造這個事,在我從小長大的地方實行得很好,可以讓每個在外的年輕人回家時恍惚很久,這是舊時的美夢,還是新時代的噩夢?
譚伯伯的粉店消失這件事情,每每讓我坐在車裡默默悵然。
現在回家都是坐車了,車直接開到家樓下,剩下的動作就是開車門,上樓,進家門,出家門,下樓,上車。
甚至連在小區裡走走的動作都被省略了,每次都是坐在車上隔著玻璃望。望見原先粉店的位置變成了健身區,原先總有賣魚攤販的位置變成了嶄新的磚砌路口,原先每年過敏都要在那裡打一星期針的藥店,只剩下一幢舊樓的入口。
聽說譚伯伯的粉店早就關門了,家裡出了一些事,自己身體也不好,開了十幾年的店就這麼關了。
她應該也沒想到,她走了,連粉店的舊屋都被夷為平地,她應該也想不到,吃她家粉長大的孩子,深夜還在敲字緬懷那些洗不乾淨油膩的餐桌,那些雪白的舊瓷碗,還有熱乾麵附贈的小碗清湯。
(奶奶去世的時候,連著幾天辦喪事,來幫忙的人都被媽媽安排在譚伯伯粉店吃早飯,一群人認識的不認識的都因為奶奶聚在這裡嗦粉,守完夜的我和弟弟也在這裡嗦粉,還有剛剛失去伴侶的爺爺也在,一邊吃粉一邊啜泣,後來爺爺就經常哭了,死亡變得如此具體,讓一個上過戰場的老兵也變得脆弱了。)
總之就是很多記憶都沒了,改造老小區的人太殘忍了,連每棟樓的樓道及窗戶都要翻新,都要改造,窗戶都一律換上了廉價鋁合金,樓梯一律刷白,扶手一律刷紅,我的童年、少年一律被清空、消失。
汪曾祺一輩子都在懷念高郵,寫高郵的鴨蛋、年節、工匠、孩子。
我30歲都沒到,就也在懷念我的家了,我知道我永遠回不去那個地方,但沒想到一切來得那麼快。它們也沒有等等我,等我有能力書寫、有能力緬懷的時候再去拆去毀,我每次回家,都只能是被這一切的幻滅重重擊打。
看,原因來了,平時忙於工作,哪有時間注意這些情緒暗礁,當幻滅來了,我又不知道用何種方法留住過往,留住記憶,我是多麼健忘的人啊,每活一秒,我心中那個地方就少掉一個角。
叫人怎能不焦慮。
汪曾祺寫得真細,記得真牢,連小時候自己怎麼做銅絲臘梅花都記得,我甚至連譚伯伯家一碗粉多少錢都記不得了,更不用說汪曾祺還寫了那麼多小說,把以前那些人都寫下來,用文字去記得。
能給每個老小區都配備一個汪曾祺嗎?它們都需要。
另外的焦慮就是關於家庭的了,過年過節,人來人往,說多少句話,就被戳多少次心窩,在很多場家宴上,我渴望工作,還不如讓一篇明天就要交的兩千字的稿子把我釘死在辦公桌前,也好過耗費一個長長的午後聽長輩寒暄,親朋吹牛。
是年在過我,它在用許多看不見的針扎我,總之不讓人好過。看似是放假,看似是回家,背後的脆弱太多,留下的焦慮和許多餘韻待捉摸。
希望以後真的能以寫字人的身份工作,這樣過完年之後,我就給自己放一個長長的假,來消解年假帶給我的痛楚。
開玩笑的,不工作哪行,我永遠成不了汪曾祺,和我永遠成不了林語堂是一樣的,還是老老實實打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