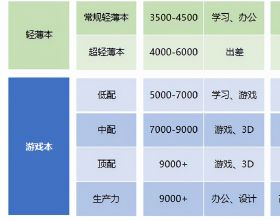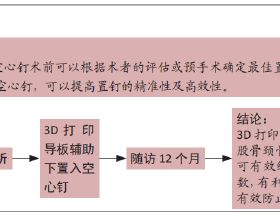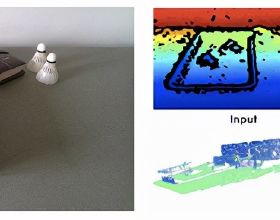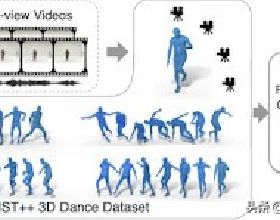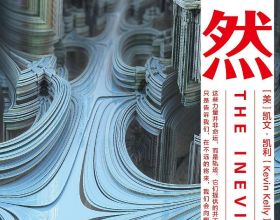導讀:當全球正在“向東看”的時候,中東也是如此。 近年來,中國與中東國家的關係日趨升溫,簽署的合作協議不斷增加。據悉,2020年,中國已取代歐盟成為海合會的最大貿易伙伴,且雙方有意考慮開展自貿協定的談判。 今年初,海合會四國集體訪華,伊朗、土耳其兩國外長也紛至而來;隨後,卡達、阿聯酋等國領導人出席北京冬奧會開幕式。此番外交情景引發外界密切關注。 與此同時,中東內部局勢也在發生微妙的變化,如以色列總統訪問阿聯酋,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訪問以色列等等。今年又恰逢中以建交30週年,怎麼展望中以關係的前景?中國在發展與中東地區的關係時,如何平衡與長期在此地經營、且擁有巨大影響力的美國的關係? 觀察者網採訪了上海社科院上合組織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中東學會高階顧問潘光。
觀察者網:今年年初,中東六國組團訪華,但這裡面並沒有以色列。其實從去年巴以再次爆發衝突之後,中方作為聯合國安理會輪值國,對該事件也有表態,中方甚至邀請巴以雙方到中國會談。外界對中國在中東地區的動向一直很關注,尤其是聯絡到美國在該區域長期以來的影響力。您如何評價近段時期中國與中東國家之間的往來,以及外界的關注?
潘光:這個問題不復雜。年初,沙特、科威特、阿曼、巴林四個海合會國家訪華,它們跟中國本來就有協議。在海合會國家中,跟中國關係最密切的是阿聯酋,不過這次海合會國家中的阿聯酋沒來,可能雙方互訪比較多了,也不一定在年初訪問。卡達也是如此,本身跟中國的雙邊往來很多;再者,卡達和其他幾個國家存在矛盾,曾在2017年時發生過斷交危機,所以也不會跟其他國家一起訪華。實際上,這是中國和海合會之間的一個安排。最近,阿聯酋和卡達領導人都來參加了北京冬奧會開幕式。
以色列和海合會之間本身有點隔閡,也不會跟他們一塊來。不過總的來說,這幾年以色列跟海合會國家的關係也越來越熱,特別是跟巴林、阿聯酋的關係較好,與沙特的關係也還不錯,但是還不會正式建立外交關係。
至於伊朗就更不會和這些國家組團訪華了,伊朗外長和土耳其外長都是單獨訪華。
從另一層面來看,美國拜登政府上臺後改變前任特朗普時期的一些做法。特朗普任內提出的幾個政策太過極端,一是退出伊核協議,二是承認戈蘭高地是以色列的領土,三是將美國駐以大使館遷到耶路撒冷。後兩者完全違背聯合國決議,聯合國決議認為戈蘭高地是敘利亞領土,耶路撒冷為國際共管——最早的聯合國決議將耶路撒冷作為聯合國管轄的地方。
不過,當時這幾個政策在民主黨內部也沒有強烈反對,因為怕得罪猶太社團,奧巴馬任內美國和以色列的關係搞得很僵,比如內塔尼亞胡曾直接進入美國國會作演講,但根本沒有透過政府,奧巴馬對此非常不滿。
現在拜登上臺,正好內塔尼亞胡也下臺了,所以他也有可能逐步作些改變。我估計美國可能重回伊朗核協議,但目前還有些事情沒有跟伊朗方面談妥,美國駐以大使館應該就繼續放在耶路撒冷了,但會重新在特拉維夫建立領事館。因為美國和巴勒斯坦的交流主要透過特拉維夫領事館。至於戈蘭高地,拜登不會專門發聲明說美國不再承認戈蘭高地是以色列領土,這會直接影響美國跟以色列的關係,但會慢慢回到奧巴馬時期的政策軌道上去,同時儘量保持低調,不要觸怒以色列。
以色列現在很緊張,但也不敢公開出來高調反對美國調整政策。以方的表態其實就是,你們與伊朗談,我也不反對,但對於這個協議,我們是反對的;即便恢復伊核協議,就能確保伊朗拿不到核武器嗎?
去年突發巴以衝突,中方提出可以為巴以雙方談判提供場所;其實過去也有過類似情況,不過不是巴以官方,而是雙方的民間非政府組織或非執政黨派到中國來談過,這種談判是比較容易的,以前已經談過若干次。
觀察者網:在談到中以關係的時候,總繞不開美國因素。一方面,美國政府更迭、以色列新政府上臺,美以關係是否也受到了一些影響,尤其是針對特朗普時期的幾項舉措會否繼續延續?另一方面,美國因素究竟在當前的中以關係中發揮著什麼作用,比如《耶路撒冷郵報》1月稱,以色列同意向美國通報有關與中國貿易的最新情況,以避免緊張局勢;去年中資投資承建的海法港也歷經美方施壓。這類事件對中以關係產生多大影響?
潘光:今年恰逢中以建交30週年,中國已經成為以色列全球第三大貿易伙伴。很多以色列官員,像以色列駐上海總領事在跟我們的談話間,都表示中國對以色列的重要性。比如,以色列海法港、特拉維夫輕軌,這些專案都是中國在承建,以色列也加入了亞投行,而且是作為亞投行發起國,還參加了“一帶一路”,他們認識到要在中東、以色列搞基建專案,不得不靠中國,美國人只會帶來槍炮,但不會來修路。
前些天我在接受其他媒體採訪的時候,還是說了一直堅持的觀點,就是中國的經濟投入和美國的軍事投入在某些地方是可以互補的,比如在海灣國家。很簡單,美國的幾大海外軍事基地都在那裡,在卡達的軍事基地最大,在沙特有兩個,在阿聯酋也有,但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不是美國工人在做,而是中國工人,以及來自泰國、菲律賓、斯里蘭卡、印度等東南亞、南亞國家的勞工在做。幾年前我到卡達去,發現這個國家裡面有80%以上是外國人,主要是來打工的,拿本國護照的只佔20%左右,阿聯酋也是如此。
此前,中以簽署海法港協議的時候,美國起初根本沒注意,等到開工了,才出來反對,還聲稱如果海法港由中國承建,那麼以後美國軍艦就不會停靠了。現在,海法港已經修建完工,全自動化碼頭,以色列人看到的時候都愣住了,沒想到中國的工程技術這麼先進;然而美國卻在以色列背後施加壓力,問題是美國不可能來幫助修建這樣一個港口。
以色列第一大報紙《耶路撒冷郵報》為此刊登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文章說如果中國要在以色列搞間諜活動,根本用不著建一個港口,它只要在海法租一套公寓就可以了。大家紛紛讚歎,這個話說得太妙了。

北京時間2021年9月1日11時25分,以色列當地時間下午6時26分,上港集團以色列海法新港正式開港。圖自央視新聞
最近以色列要跟美國簽署一個檔案、向美國通報與中國相關的貿易情況。這實際上只是應付美國的一個手段。事實上,與中國的貿易往來根本不用通報,在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商務部等機構釋出的相關檔案中都能公開查到。
美國最關注的是要以色列通報所謂的敏感高科技專案,但以色列說我現在與中國合作的也沒有敏感高科技專案。過去中以合作的最大問題是,美以合作專案規定在一定期限內不能轉讓給中國,20年前以色列原定要賣給中國的預警機,最終在美方壓力下只能撤銷,撤銷後以色列還賠了幾個億,因為中國已經付了定金,此後以色列也不敢跟中國做軍火貿易。當然私下有沒有交易,這可能就說不清了。
還有一個美國比較忌諱的方面就是美以合作技術,規定10年以後可以作為以方的技術。所以,國外民間往往有很多傳得神乎其神的東西,什麼中國的殲十戰鬥機像以色列的飛機、技術是以色列給的等等。以色列方面則一直堅持,如果是美以合作的技術,要給別人,肯定是超過10年了,如果是以色列單獨技術,那願意賣給誰就賣給誰。
而且,軍火武器一旦進入國際市場以後,幾乎是完全自由流動的,到了誰手裡,誰又再轉手賣出去,這個動向很難摸清。打個比方,武器從中國賣到另一國,如果再經由這個國家賣到第三國,我們也管不了。
但現在在武器軍火這種事情上,我們也很謹慎,比如我們跟以色列承諾不會向伊朗出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他們就很放心。最近,有美媒稱中方將導彈技術賣給沙特,以色列也沒有太大反彈,因為它也想跟沙特、阿聯酋恢復關係。所以,這其中的問題很複雜,我們也要結合局勢變化來分析。
美國要施壓也只能做到這個程度,以色列表個態,有重要敏感技術會向美方通報。不久前,我碰到上海中以創新基地高層人士,也提到了這個美以協議,對方表示籤這份協議前知會了中方,而且簽了協議也不代表不跟中國做生意。
類似這種情況,可能今後較長一段時間內會繼續存在,即一方面美國施壓、以色列應付,另一方面以色列和中國繼續開展貿易往來,有的公開做,有的私下做。
如果你去看一下中以關係的定位,就會發現跟其他國家的描述都不太一樣,中以是創新合作關係,“創新”一詞意味著什麼,其實大家心裡也都明白。美國當然也清楚,但對以色列也沒辦法。如果美國對以色列施壓太大,也會得罪美國國內的猶太人。
當然,從我們的角度來說,有些事情不要過多計較。之前我在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也說了,有很多專案中方願意做的,但如果以方現在有困難,我們可以等。
觀察者網:稍早前,在1月24日舉辦的中以建交30週年研討會上,有參會老師提到了雙方媒體對對方形象的塑造問題。出於語言問題,國內對中東媒體或輿論的關注度不高,所以對當地精英和普通民眾對中國的看法也並不瞭解,您過去在交流訪問中,對於以色列媒體、民間輿論對中國的看法有什麼觀察?
潘光:雙方的媒體、輿論確實都存在這樣的問題。以方有些人被稱為所謂“親華派”,與之相對應的就有“親美派”。“親美派”就會在一些問題上追隨西方、抹黑中國,比如炒作新疆人權話題,不過他們不說新疆種族滅絕,因為他們認為“種族滅絕”這個詞是針對納粹屠殺猶太人的,但有些人會跟著西方報紙討論香港問題,不過總體上不是很多。另外一方面,一些媒體、民間輿論在談到中以關係時,總會提及中國救助猶太人的那段歷史,現在也是中以友好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那麼,從中國方面來看,問題大多出在一些地攤雜誌、所謂暢銷書作者的胡編亂造,比如有些暢銷書大談特談2008年金融危機是美國猶太人造成的,再比如猶太人如何賺錢、如何吝嗇、如何精於算計等等,這類歪曲的言論傳久了,就會給一部分民眾造成刻板印象。
甚至《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還為此來採訪我,問我這是不是反猶主義,中國有沒有反猶主義?我說,中國從來就沒有歐洲那種反猶主義,中國儒家文化裡面就不存在這種因素,出現上述現象,主要是因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很多人想賺錢,所以就有了這些稀奇古怪的書,把猶太人形容成賺錢萬能;猶太人對這種說法也很反感,他們辯駁說我們賺錢也很辛苦的。
不過,我也對猶太人說過,你們在談判中確實極其精明,你們對每一分錢都會討價還價,但一旦簽好合同後,你們是絕對守信的。
其實,中以兩國的一些媒體都犯了類似的錯誤,換句話說是一些現實利益因素導致了一些錯誤的說法。
觀察者網:確實,在去年的巴以衝突中,有以色列媒體對於中國方面的一些表述也表示不滿,認為中國偏袒巴勒斯坦一方,您怎麼看這種情況?
潘光:以色列方面對於中國官方媒體的報道確實有點意見,認為太傾向於巴勒斯坦一方。實際上,中國媒體、外交部發言人、在聯合國,我們投票是支援巴勒斯坦的,這是我們長期的官方立場,現在有一些細微改變,但不可能徹底改變。
當年我們是完全支援阿拉伯、反對以色列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導阿拉法特多次訪問中國,中方也給了他們武器。現在,我們的電視臺、報紙等媒體,總體還是支援巴勒斯坦的合法權利,在這個問題上中方主張一向很明確,支援“兩國論”,以色列國和巴勒斯坦國和平共處。美國拜登政府上臺後,應該也會回到“兩國論”主張。以色列內部有些比較極端的人對這個觀點不滿意,但他們也知道這是國際社會相對主流的觀點。未來隨著雙方良性互動,這個問題會逐漸解決。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國跟以色列為什麼不能建交,因為雙方都遭到了第三國的否決,美國否決以色列,阿拉伯國家否決中國,結果沒想到尼克松訪華以後,美國對以色列不否決了,而且希望以色列能儘快與中國建交,那麼中國方面,等到蘇聯解體以後阿拉伯國家的反對意見也沒有了,當時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後來俄羅斯都跟以色列建交。
緊跟著,馬德里中東和會召開。在馬德里和談之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國應儘快與以色列建交,否則中國沒法參加這次會議。於是,1992年1月24號,成為中以建交的關鍵日子。當時,我們寫了很多報告給外交部。中以建交後4天,1月28號,中國派代表參加馬德里和會。
我一直說中美爭端是中以關係之間最大的障礙,對中國來說,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否決中國的對外政策,但以色列有這個問題,以色列的對華政策,美國還是有否決權。當然這種否決權不像過去那樣強大,所以有時候也可以躲得過。

2022年1月30日,以色列總統赫爾佐格開始對阿聯酋進行為期兩天的訪問,被稱為是歷史性的訪問。圖自歐洲時報
觀察者網:其實最近中東關係也有變動,比如以色列總統1月底訪問阿聯酋(去年底以色列總理首次訪問),再比如去年底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訪問以色列,雙方達成了一些共識等等。在伊朗核協議談判前路不明朗之際,這一系列舉動會對地區局勢帶來什麼影響?
潘光:現在巴勒斯坦對以色列態度也有所改變,內塔尼亞胡下臺後,以色列對巴勒斯坦態度也比較好,而且以色列和海灣國家之間的關係會繼續推動。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只要巴以雙方的良性互動在穩步推進,時間長了以後,對中國來說,壓力也小了。
觀察者網:隨著美國撤軍阿富汗、在中東地區逐步實施收縮戰略,有些外媒或國外學者專家在談中東問題時,會有意將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提升作為一個對比,認為中國已經成為中東地區的“玩家”之一,您怎麼評價這種看法?未來中美在中東的影響力會出現轉折性的變化嗎,怎麼看待這種預期?
潘光:還是我一貫的觀點,美軍撤出了阿富汗,但實際上美國並沒有撤出中東,它在中東主要是軍事存在。現在伊拉克、敘利亞還有少數一部分美軍,其他主要駐紮在海灣國家,卡達有美國最大的軍事基地,還有沙特、阿聯酋。當年可能因為中東石油,還有些經濟存在,但現在中東石油對美國來說也比較無所謂了。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存在和戰略存在,不會有大的改變,但經濟存在越來越薄弱。
所以,現在的中東格局很有意思,我一直說中國在中東已經佔經濟優勢,比如一帶一路,大部分中東國家都參與了這個倡議。關鍵是看今後中國的經濟介入與美俄的軍事介入是否可以互補,或者說多大程度上的互補。
這其實跟阿富汗的形勢一樣,當年在阿富汗,美國人打仗,中國人修橋修路,這一模式將來在中東會繼續存在。雖然現在“一帶一路”在阿富汗無法推進,但在中東地區倒是進展不錯,大多數國家都在參與,而且這些參與的國家大多有美國軍人在那裡。
當然,除了經濟互補之外,還有反恐、打擊海盜方面的合作。中國在吉布提的基地已經在發揮作用了。
目前中美在中東偶然還會發生衝突,但跟在東海、朝鮮半島、臺灣地區、南海的形勢完全不一樣,中國在這裡反而跟美國、俄羅斯、歐洲等有所互補與合作。
我們在中東主要是勸和促談,軍事存在體現在聯合國維和部隊,在黎巴嫩南部大概有一千多名中國軍人,這些中國軍人非常受黎巴嫩人民的歡迎,掃地雷、開路、修橋等等。黎巴嫩南部正好是真主黨地盤,所以我個人推測真主黨跟中國的關係應該不會差。中國的聯合國維和軍人正好夾在真主黨和以色列軍隊之間,我以前到過戈蘭高地,以色列方面的軍事指揮官就指給我看,他說你看那塊地方就駐紮著Chinese Army。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臺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閱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