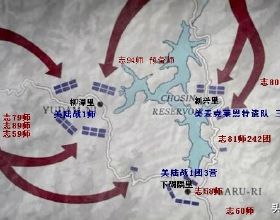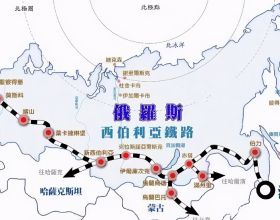歐洲的“恐俄症”由來已久,第一次爆發,要追溯到1204年的那場十字軍東征。這場“信仰之戰”的最初目標是埃及重鎮薩拉,但十字軍走到半路,發現君士坦丁堡好像更有賺頭,於是調轉矛頭就攻陷了這座千年古城。
為了捍衛君士坦丁堡,俄羅斯的前身羅斯人派出了維京戰士組成的瓦蘭人衛隊,他們與十字軍浴血奮戰,沒有一人投降,最終全軍覆沒。
這是一場頗值得玩味的戰爭:打著信仰旗號的歐洲騎士們在君士坦丁堡燒殺搶掠,聖壇被砸碎,聖母銅像被熔鑄,宮殿被夷為平地,甚至連修女都慘遭玷汙……而羅斯人卻個個表現得像光榮的騎士。
歐洲強盜從這場戰爭中賺得滿盆滿缽,而城內的東正教僧侶不得不逃往俄羅斯。這個橫跨亞歐的大國,也因此在信仰上與歐洲徹底分道揚鑣。
後來蒙古橫掃歐亞大陸,在俄羅斯境內建立了金帳汗國,歐洲人把對東正教和蒙古人的畏懼、都投射到俄羅斯身上,“恐俄症”像瘟疫一樣蔓延。
在整個文藝復興時期,歐洲人都在極力貶低俄羅斯。例如法國大文豪拉伯雷認為俄羅斯人“與印度人、波斯人和野蠻人屬於同類”;孟德斯鳩認為俄國是專制制度的極致體現;盧梭乾脆直接給他們蓋棺定論,認為“俄國人永遠不會成為真正文明的民族”。
歐洲經過漫長的中世紀薰染,思考問題很難脫離宗教視角,在他們的意識中,“基督教歐洲”與“東正教俄羅斯”是有血海深仇的,俄羅斯人早晚會報復。
他們大概忘了,當年是誰以宗教名義瘋狂東征虐奪、血洗君士坦丁堡,激起不可磨滅的仇恨的。
18世紀末,伴隨著彼得大帝改革後俄國的逐漸強大,歐洲的恐俄症達到了一個小高潮。一代歐洲精英全盤否定俄羅斯,他們甚至不允許俄羅斯人擁有優點。
例如,在談到俄羅斯人的勇敢時,狄德羅是這樣評價的:“奴隸制和迷信激發了他們對生命和對死亡的蔑視。”
法國作為當時的歐洲大陸霸主,對俄羅斯人的仇恨值也是最高的。這種集體意識,最終導致了拿破崙那場著名的遠征。
作為歐洲霸主,不把全歐洲的敵人俄羅斯打趴下,如何服眾呢?
1812年那個寒冷的冬季,拿破崙60萬大軍在莫斯科損失殆盡,帶著最後3萬人灰溜溜逃回了大本營。這場戰爭,英勇善戰的俄羅斯人僅僅損失了21萬軍隊,個個以一敵三,將法蘭西皇帝的威嚴碾得粉碎,拿破崙也因此跌落神壇。
讓人意外的是,這場戰爭之後,整個歐洲都瘋狂地愛上了俄羅斯,風評來了個180°大轉彎,俄羅斯直接從“不配擁有優點的野蠻人”變成了“人類的理想代表”。
當然,歐洲對俄羅斯態度的變化註定是短暫的,因為那時的他們只想打倒拿破崙,而俄羅斯人幫歐洲達成了心願,讚美俄羅斯在很多國家也就成了政治正確。
“反俄棋手”法國人十分清楚,歐洲讚美俄羅斯是假,反對法國霸權是真,他們緩過勁之後,又扛起了反俄大旗,在輿論陣地開始反攻。
1843年,一本影響深遠的醜化俄羅斯的暢銷書《1839年的俄羅斯》在巴黎出版,短時間內再版三次,再一次點燃了全歐洲的恐俄症。
這本書的核心觀點是:俄國人不愛歐洲文化,只是在模仿它,以便強大起來後去搞侵略。
這本書影響力巨大,一直到二戰後,依然被歐美學術界評為對俄羅斯描述最出色的文獻。
吉·梅坦在《致命的偏見》中對這本書的評價非常具有代表性:這本著作成為恐俄人士的萬能《聖經》,是恐俄人士用作證據的不竭源泉和插相簿。
有心的讀者一定會發現,早期的反俄先鋒基本都是法國人。為了詆譭俄羅斯,這幫文化人找出了很多奇怪的角度:比如基督教與東正教的世仇,比如俄羅斯人與蒙古人的聯姻關係……
然而真正的原因只有一個:作為歐洲陸地霸主的法國,想在全歐洲營造反俄氣氛、從而把俄羅斯排除在自己的勢力範圍之外。
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英國人也加入了恐俄陣營,逐漸接替法國,成為歐洲反俄急先鋒,這又是為何呢?
答案依然是君士坦丁堡。
這座城市是銜接歐亞大陸的紐帶,但卻因為東正教的歷史關係,天然和俄羅斯人比較親近。英國人認為:“君士坦丁堡是架設在東西方之間的一道金橋,不透過這道橋,西方文明就不能像太陽一樣繞過世界; 而不同俄國進行鬥爭,英國就不能透過這道橋。”
當時的英國,國力處於巔峰,自稱“日不落帝國”,它的野心已經不侷限在歐洲,而是想要控制整個歐亞大陸。
眾所周知,英國是個純粹的海權國家,陸軍戰力非常一般,連一個阿富汗都拿不下來;而歐亞大陸縱深太大,中西亞全是陸地,這是陸權國家俄羅斯的主場,如果俄羅斯繼續壯大,英國無論如何也沒法在亞洲心臟地帶與其競爭。
1853年,英國和法國這對反俄新老棋手聯袂出擊,在克里米亞徹底擊敗了俄國。
克里米亞一丟,就意味著俄國無法再向南拓展勢力,起碼透過君士坦丁堡進攻歐洲的路線是被堵住了,英國人這才稍微寬了點心。
那麼德國呢?
眾所周知,二戰時期德國對蘇聯可是夠狠,他們的恐俄症又是怎麼回事?
其實,1870年德國統一之前,德國與俄國的關係還不錯,日耳曼貴族長期和俄國羅曼諾夫家族聯姻,兩國貴族沾親帶故,其樂融融。
德國與法國不一樣,它想做歐洲霸主,首要敵人是法國,其次才是俄國。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希特勒上臺後開始瘋狂反俄,甚至提出了“生存空間”理論專門用來反斯拉夫民族?
在希特勒的支援下,俄羅斯人被認為是文明血統最少的民族。德軍依據人類學家沃爾夫岡·阿貝爾的理論,制定了一項“逐步消滅俄羅斯”的可怕計劃。
二戰時期,德國成為歐洲“恐俄症”的代言人,其真實目的是想給英美製造煙幕彈,好為擴軍備戰爭取空間。
一句話,德國並不恐俄,都是裝出來的。
二戰之後,扛起“恐俄症”輿論大旗的國家,那就只能是美國了。
美國這個國家特別純粹,作為“資本家的天堂”,美國所有行為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掙錢。
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實力一落千丈,美國其實沒必要恐俄,但這並不耽誤美國以恐俄為藉口,煽動恐慌情緒,一方面可以轉移國內各種矛盾,另一方面也能加速資本回流,繼續薅全世界的羊毛。
——————
參考文獻:
1、孫芳,西方“恐俄症” 從歷史心理到政治心理,載於《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20年第4期;
2、侯艾君,俄羅斯批判西方恐俄症及其啟事,載於《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