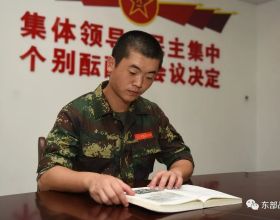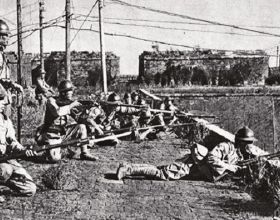胡適在北平燕京大學講演《談談做夢》講演稿 (《新疆日報》,1947年12月21日)

胡適題扇面,寫錄王安石《夢》詩一首(原載1929年《上海畫報》)
2021年12月17日,為現代著名學者胡適先生130週年誕辰;12月18日,又逢宋代政治家、文學家王安石千年誕辰。如此巧合,不禁令筆者憶及胡適曾一度引用王安石《夢》詩,頻頻公開講演“做夢”的往事。
胡適講演引用王安石的《夢》,激勵青年人“做夢”
前些年,坊間曾流行一篇據胡適講演稿摘錄整理的文章,徑直冠以《胡適:人生就算是做夢,也要做一個像樣子的夢》的題目,一時頗為醒目,頻頻被眾多公微及自媒體引用,儼然已成勵志美文。
事實上,這篇以“夢想”激勵青年的文章,乃是胡適於1948年8月12日在北平空軍第二軍區司令部講演,原題為《人生問題》。此次講演的大致內容,於講演次日即刊發於北平《世界日報》《華北日報》之上,後來又輯入了《胡適全集》第22卷,遂廣為世人所知。
由於講演之末,胡適引用王安石所作《夢》詩一首作為結尾,當年聽眾與後世讀者,都很容易將其歸納成一篇以“夢想”激勵青年的美文,並將其視作胡適講《夢》並談“做夢”之始。殊不知,在此一年之前,胡適早已開始在公開場合引用王安石的《夢》,並由之講演“做夢”,激勵青年人“做夢”了。
譬如,1947年10月17日,胡適就曾在南京應政治大學之邀,做過主題為“大學即研究院”的講演,就曾提及“青年人要有夢想,夢想去做專家權威,去做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就曾呼籲青年人“不要失掉小孩子做夢的精神!去夢想,去實現夢想吧!”
然而,此次講演還沒有引用王安石的《夢》,也並不是明確以“做夢”為主題的講演,只是有涉及到激勵青年人懷抱夢想,實現夢想的內容。約兩個月之後,胡適將此次講演的內容,進一步修訂充實,又拿到北平的燕京大學重新講演了一次,這一次主題就明確為“談談做夢”。此次講演,與在南京政大的講演,不但內容上有所差異,其最大的區別還在於,開場即引用並講解了王安石所作《夢》詩一首,可視作胡適在公開講演中首次引介王安石的《夢》。僅據目前已知的文獻記載而言,王安石的這首詩,胡適非常喜愛,引用了至少近二十年。
遺憾的是,胡適在燕大所做“談談做夢”講演的事蹟,《胡適年譜》《胡適日記》等基礎文獻,俱無記載。實際上,就連《胡適全集》《胡適演講集》等權威文獻中,對此也未見任何載錄。幸運的是,筆者於1947年12月21日的《新疆日報》上,意外發現了刊載於該報的胡適“談談做夢”之講演稿。
希望大家做些像樣的夢
可見,胡適公開引用講解王安石的《夢》之始,並以之引申出主題為“談談做夢”的講演,實為1947年11月13日在北平燕京大學的那場講演。當天,胡適講演的開場白是這樣的:
宋朝的哲學家、儒學家兼文學家王安石,是個積極的人。佛教講人生如夢,很使人悲觀。王安石研究佛學卻得到一種積極的人生觀,從下面這首“夢”詩裡,可以看出他的見解:
知世如夢無所求,無所求心普空寂,還似夢中隨夢境,成就河沙夢功德。
我們不相信人生是夢,但是許多事是從夢想成功的。人生幾十年,做夢的機會很少,我們應該做一番有趣味的,像樣的,轟轟烈烈的大夢。
此次講演一週之後,《新疆日報》上刊發了經過整理之後2000餘字的講演稿,乃是由當年一位在燕大親聆胡適講演的聽眾摘要記錄而成。不過,該報特意對此稿加有按語,明確聲稱:
“這是北大校長鬍適先生上月十三日下午在燕京大學的講演,不是全文,也沒經胡先生校正,如有錯誤,由記者負責。”
僅從這份講演稿內容來考察,與近一年之後胡適的《人生問題》講演,頗為不同。講演中,除了開場即引用並講解了王安石的《夢》,接著還簡要列舉了自己年輕時做過的“大夢”,即倡舉白話文運動與推進新文學運動。隨後,又列舉了美國康乃爾大學與霍浦金斯大學創辦的事蹟。這一中一外,兩組事例,生動地說明了年輕人不但應當“做夢”,還應當做“像樣子的夢”,夢想實現也罷,部分實現也罷,沒實現也罷,才不枉幾十年的人生旅程。不過,雖然前後兩次講演內容確實有所不同,可在講演開場或結尾時引用王安石詩句的做法,以及由之引申勉勵年輕人“做夢”並努力實現夢想的講演主旨,還是如出一轍的。
無獨有偶,就在筆者尋獲此次講演的《新疆日報》轉載報道之後不久,又有幸尋獲了此次講演的《燕大雙週刊》首發報道。這份對開八版的這份校內小報,於1947年11月15日印行的第四十八期之上,以“胡適先生來校說夢”為主題,以“夢能決定終身不難實現,希望大家做些像樣的夢”為副題,用了一個半版面來刊發胡適的講演報道,足見當年師生對此次講演的重視程度。兩相對照比較,可知《燕大雙週刊》報道中的胡適講演內容部分,與《新疆日報》轉發的內容,完全一致。
豈可不努力做一個轟轟烈烈像個樣子的夢
事實上,早在那一場燕大講演近二十年之前,胡適就已經將王安石的《夢》,寫入信札、寫上扇面,在筆下提出並呼籲過有志青年同來“做夢”了。
當年,胡適的北大學生儲皖峰,於1929年春,應時為上海中國公學校長鬍適之聘,赴任該校大學部教授,“因為過於勞碌一點,加之食物不清潔,馬上得到腸窒弗司的病症,不得已住到吳淞海濱療養院”。當時,胡適對其多有探視慰問,還親致信札以表關切。其中有一通這樣寫道:
知世如夢無所求,無所求心普空寂。還似夢中隨夢境,成就河沙夢功德。
荊公此詩,我最愛誦。知道人生如夢,故無所營求,也無所貪戀。但人生只有這一次做夢的機會,豈可輕易錯過?豈可不努力做一個轟轟烈烈痛痛快快的夢?
這一通寫於1929年8月27日的胡適信札,約於三年之後,由儲氏轉錄發表於1932年10月22日印行的《國立浙江大學校刊》第108期之上。當時,胡適早已辭職北上,返歸北大任教,儲氏也已出任浙大講師,但對恩師的昔日關懷及這一通訊札格外珍視,遂署以“推仔”的筆名,以隨筆連載的方式,冠之以《琴畫室漫錄:(四)胡適慰病函》的題目,將之公開發表了出來。
實際上,在致信儲氏之前,稍稍往前推三個月時,同年5月間,胡適還曾將這首《夢》寫入扇面,題贈給了友人楊吉孚;這張扇面即刻被刊印在了《上海畫報》上,成了當年上海文化圈子裡的一樁“掌故”。
寫完扇面後的胡適,還意猶未盡,又將對這首《夢》的個人理解,抒寫了一番。可能是覺得自己鍾愛有加的這首詩及其理解,對於解答“人生有何意義”這樣的青年人生觀問題,有所幫助——胡適又將之收入《人生有何意義(答某君書)》一文中,列為第二章節,重擬題為“為人寫扇子的話”,輯入《胡適文存(三集)》,於1930年9月正式出版。其原文如下:
知世如夢無所求,無所求心普空寂。還似夢中隨夢境,成就河沙夢功德。
王荊公小詩一首,真是有得於佛法的話。認得人生如夢,故無所求。但無所求,不是無為。人生固然不過一夢,但一生只有這一場做夢的機會,豈可不努力做一個轟轟烈烈像個樣子的夢?豈可糊糊塗塗懵懵懂懂混過這幾十年嗎?
民國十八年五月十三日
顯然,胡適對王安石這首詩的理解與引用,都已頗具個性與時代感。或許,這跨越千年的文心詩境,之所以有這麼一種冥通默契,之所以有這麼一番因緣際會,本即是一代又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精英“初心”不改,始終懷揣“夢想”,傾力追尋“夢想”,憑欄回望之際,終究有著那麼一場“夢遇”般的心領神會罷。
王安石的“有為主義”胡適終生推崇
胡適對王安石其人其文其思想的喜愛與推崇,還絕不僅限於這一首《夢》。早在1932年8月為山東齊魯大學題詞時,胡適就曾引用王氏語錄,為之這樣寫道:
“王荊公說,學者之事,必先為己。其為己有餘,然後可以為人。他所謂‘為己’,不是自私的營謀,只是易卜生說的‘先把你這塊材料鑄造成器’。”
除了胡適自己引用王氏詩文與語錄,有所抒發與引申之外,胡適本人對王安石的一句評語,也被同時代其他學者所認同和引用。1933年1月出版的《王安石評傳》,著者柯昌頤本是歷史學家,曾為清末狀元,乃是前輩學者,卻也十分認同並引用了胡適的評語,以此來加持自己的學術觀點。書中轉引胡適的評語如下:
“看慣了近世國家注重財政的趨勢,自然不覺王安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會主義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安石的見解和魄力了。”
雖僅僅是短短一句評語,卻也足見胡適眼中的王安石,有著何等非凡的歷史地位了。胡適晚年更有意對王安石做一“總評”,在其逝世一年之前,曾撰有一篇《王荊公的有為主義》。此文開宗明義,十分明確地指出:
“我常引王荊公的詩句來說明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是用‘有為’來替代‘無為’。他的文集裡……都很明白地提倡一種有為主義,明白地頌揚人工開物成務的功績。”
此時的胡適,還頗推崇王安石的另一首詩《登飛來峰》,經常將詩中末兩句“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拈提出來,多次書寫,頻頻題贈友人。遙望千年已過,塵世滄海桑田,世界地覆天翻——王安石“變法”的時代,早已成了過眼雲煙;即便胡適投身“新文化”的時代,也已為百年舊夢。
回顧70年餘年之前,胡適以自己已實現或部分實現的夢想為例,在大學講堂中激勵年輕人的那一句話,至今仍很勵志:“年輕人應該放膽做夢,不必怕人說是夢想者,夢往往可以決定終身,至少也可以決定一部分。”不得不承認,講演中的那一句,“我們不相信人生是夢,但是許多事是從夢想成功的。人生幾十年,做夢的機會很少,我們應該做一番有趣味的,像樣的,轟轟烈烈的大夢”,至今仍很動人。
文並供圖/肖伊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