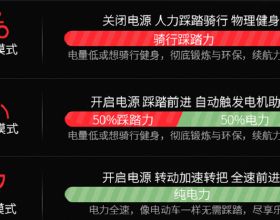1982年正月二十一,對姜秀芝老師來說,絕對是最悲痛的日子。他的丈夫於二根兒,一大早騎車去縣城,卻成了他們夫妻的永別。
於二根是縣一高的數學老師,春節開學的第二個星期一,他起了個大早往縣城趕,騎車後面的貨架上,是姜秀芝老師給他收拾的一大包一星期用的東西。他高興地出門,姜秀芝老師目送他走出家門,望著他騎著車子離開村子,騎上了通往縣城的公路。
姜秀芝老師是我們村小的民辦教師,丈夫上班走了,他安頓好三個孩子,和大哥一起吃完早飯,也到學校去上課。
大哥於大根也是村小的民辦教師,爹孃去世早,他供應弟弟二根上了大學。於二根大學畢業後,他又給弟弟於二根張羅婚事,娶了村裡最漂亮的姑娘姜秀芝。他和姜秀芝老師是一個學校的同事,現在成了姜秀芝的大伯子哥,成了一家人。
於大根腿有殘疾,腿瘸。殘疾人,還是民辦教師,是不好找媳婦的。弟弟在縣城高中教書,弟媳婦姜秀芝一人照顧三個孩子,還要種田,於大根兒就跟著他們一起過日子,幫著弟媳婦兒照顧家,幫著她種田。他們的日子過的還可以。掰著指頭算,雖然他和兄弟媳婦兒掙錢不多,總算也掙錢。一家三個人掙錢,還有田地,日子還算美滿。眼下的家庭情況,讓過慣苦日子的於大根感到很滿足。
可是往往天有不測風雲。於大根,姜秀芝他們清楚的記得,就在上午快放學的時候,他們接到了二根出事的噩耗。他的弟弟於二根在去上班的途中,被一輛拖拉機撞了,等拉到醫院,人已經死去。他們清楚地記得這一天,1982年正月二十一,在縣人民醫院的急救室裡,於二根已經成了一具冰冷的屍體。僵硬的屍體,滿臉血汙,弟媳婦兒姜秀芝當場昏死過去,他的腦海裡一片迷茫。
弟弟二根比他小三歲,在他高中畢業那一年,爹也去世了。是他供應的弟弟上了高中,是他供應的弟弟上了大學。弟弟好不容易有了讓村裡人羨慕的工作,他們的苦日子總算熬出了頭。突然天降災禍,出現了這樣的事兒,毫無疑問,他們家的天塌了。接下來意味什麼?迷茫中的於大根很清楚。
弟媳姜秀芝30歲剛露頭,肯定會改嫁。弟媳婦兒改嫁了,三個幼小的孩子,也一定跟著走。他們這個家馬上就會崩塌,就會剩他一個人。
弟弟的死,對弟媳婦兒來說是痛苦的,是悲傷的,但是痛苦和悲傷過後,她還會尋找新的生活。而他呢?面對著將要離散的家,他覺得自己的命太苦了,覺得對不起自己的爹孃。他沒有看好這個家。於大根幾乎崩潰,幾乎絕望了。
弟弟的喪事辦完後,於大根整整瘦了一圈兒。弟媳婦走與不走成了他心中探究的最大問題,這個問題時刻纏繞著他,讓他寢食難安。他沒有權利留下弟媳婦兒,也沒有權利留那三個幼小的孩子。就是有這個權利,他能留得住嗎?他只有等待,在等待中觀察著,在觀察中等待著。
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兄弟媳婦兒姜秀芝很快的恢復了平靜,很快的進入到了正常的生活狀態。該去教學去教學,該洗衣洗衣,該做飯做飯。
這種平靜的生活,讓他忐忑不安,既然弟媳婦兒能這樣,他忍著心中的巨大的疼痛也要進入到正常的生活中,該上課上課,改種田種田。他睡得比以前晚多了,早晨起床也格外早。家裡的事兒他不問,田裡的事兒他不讓弟媳婦管。
弟弟沒了, 他覺得和弟媳婦兒在一起生活很彆扭。一個孤男,一個寡女,不多說一句話,他從學校回到家裡,只有埋頭幹活。他們的家是清淨的,清淨中透出了許多淒涼。
一年以後,弟媳婦兒沒有改嫁的意思,村裡以前也有這樣的情況,女人死了男人,用不了幾天就改嫁了。弟媳婦兒姜秀芝的舉動,讓他感到很奇怪。
有一天,吃過晚飯,他正要起身往外走,弟媳婦兒姜秀芝叫住了他,讓他不要走。
他愣愣的站在飯桌前。姜秀芝讓他坐下,很冷靜地對他說。大哥,我知道你心裡想什麼,你是怕俺走,怕帶走孩子,我想了好長時間,決定不能往前走。二根對我好,你對我也好,我走了對不起你們於家。
女人說的很平靜,眼裡淚光閃閃。
於大根完全不知所措,面對眼前的女人,他的弟媳婦,他能說什麼呢?他只有說,二根不在了,你以後的路還很長,還是考慮清楚,不要為這個家把自己耽誤了。於大根想說很多話,但對面前的女人他難以完全表達出自己的想法。
女人說,有你在,哥,有孩子在,我們的苦難日子會熬過去的。以後不要提二根了,既然他不在了,提他還有什麼用?
女人一臉平靜,於大根的淚水順著臉頰流淌下來。他猛然覺得一身的輕鬆,一身的力量,家裡有孩子,孩子有媽媽,這也算是一個溫暖的家。
他們飯桌上的話多起來,每天晚飯時,都討論第二天的事,放學後,該幹什麼農活兒,他們商量著,他們的日子是有計劃的,是井井有條的。他們也討論教學上的事兒,討論學校的事兒,討論學生的事兒。總之,他們迴歸正常生活以後,日子裡有了笑聲,有了愉悅。
85年以後,民辦教師的培訓和考試多了起來。趕到星期天培訓,於大根一大早就起床,安排好一切,讓姜秀芝去培訓,自己在家,看著孩子,到地裡管理莊稼。姜秀芝回家後,把培訓的內容講給於大根聽。於大根從來沒有參加過培訓,但他的學習任務一點兒也沒有落下。
遇到考試,於大根必須得去,他不想去,這個家一天都離不開他。一個接一個的考試讓他感到力不從心。看著三個一天比一天長高的孩子,看著村裡人的生活家家都比他們好,於大根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他對姜秀芝說他要辭職,在家照顧田地。孩子們一天比一天大了,以後上學要花很多錢,他想多掙點兒錢。
姜秀芝知道,大哥為這個家操勞的太多了,如果真的讓大哥失去教師這個職務,肯定對不起大哥,這對大哥肯定是不公平的。他無論如何也不能答應,她說,你為這個家失去的太多了,俺知道你熱愛教育,喜歡教學,咱們就是日子太苦,也不能放棄這份工作。什麼事兒俺都能答應你,就辭職這件事兒,俺堅決不同意。大根說,咱家的日子太苦了,就咱倆這點兒錢,能夠幹什麼?你要知道,孩子們以後要上初中,上高中,讀大學,那要花很多很多錢。俺種完地,可以去打工,多掙些錢,為孩子們準備著。
姜秀芝是一個很有理性的女人,她喜歡往遠處看。他說,哥,不要看眼下,眼下我們確實窮,孩子們花錢的事兒以後再說。你聽俺的吧,民辦教師好壞是個工作,說不定以後會轉正的,你現在辭職了,到將來後悔怎麼辦?毀了你的前途,我能對得起……女人眼睛一紅,淚水湧了出來……咱們只是苦了點兒……再苦也要堅持……於大根雖然腿腳不好,但他是個硬漢子,很少掉眼淚,這次,他眼睛裡淚花閃閃。
經過幾次考試,兩個人都取得了《專業資格證》,但是這個證書只是一個過渡性的,臨時性的。學校開會說,每一個民辦教師都要取得相應的學歷。剛好,民辦教師能離職進修,於大根想讓姜秀芝離職進修,去拿學歷。
他們兩個的工資加到一起,一個月不足100元,張秀芝要去帶去離職進修,對這個家庭來說,肯定是入不敷出。於大根的話剛一出口,姜秀芝就表示反對。於大根很堅決,他說,我已經和大隊、學校說好了,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咱們不能失去。不就是兩年的時間嗎?家裡有我呢,你就放心去吧。
姜秀芝知道大哥誠意,知道大哥的倔強。但這是這個家,大哥那樣的腿腳,白天教學,抽時間種地,還要照顧孩子,她無論如何也走不開,大哥這樣的決定讓他很為難。
最終他拗不過大哥,還是到縣進修學校進修。一家的生活完全壓在了於大根的身上。家裡缺的是錢,一放學,他就趕緊回家,抓緊幹農活兒。田裡的活幹完了,星期天一大早安置好孩子,就到村窯廠去裝窯。一天能掙十多元錢,這十多元錢,是姜秀芝一個星期的生活費。
大哥的身體很單薄,大哥走路一瘸一拐,姜秀芝接過大哥手中帶著汗水的鈔票,她的心幾乎碎了。她實在不願意花大哥的血汗錢,可是不花又有什麼辦法呢?民辦教師的工資不能按月發放,半年也難發一次工資,她們家沒有多餘的錢,她只有含著淚水,拿著這些錢走向縣城。
他也很佩服大哥的學問,在他上學的這兩年時間裡,大哥報了電大。他一次也沒有參加過輔導,靠著自學,等她進修畢業的時候,大哥竟然也拿到了大專文憑。
他們的日子一天一天的向前走,走的是那樣的艱難。一個大伯子哥,一個弟媳婦,一個孤男,一個寡女,同住一個院子,同在一個屋簷下,村裡人難免有許多閒話,這些閒話肯定到不了他們的耳朵裡。有一天,三叔把大根叫到了他家裡,說大根快40歲了,也該成個家了。
於大根說,三叔,我這個樣子一瘸一拐的,能成家嗎?二根的幾個孩子,馬上需要花大錢,我怎好成家?他提到二根,三叔哀嘆一聲,說,哎,街坊的話難聽啊!
大根知道三叔的意思,他不傻,從村裡的眼神裡也能讀出一些問題。他說,身正不怕影子斜,誰愛說啥誰說啥?
那也要注意點,你們都是文化人,不能給咱們老於家丟臉。
於大根對姜秀芝沒有絲毫的非分之想,他心疼姜秀芝一點兒不假,但沒有對姜秀芝有男女之間的意思。他是大伯子,是長兄,長兄如父,他如果對弟媳婦兒有那個意思,連自己都覺得是齷齪。他知道什麼是倫理綱常,人失去了這些,怎麼能在村裡抬起頭?怎麼能站在講臺上去教學生。
他對三叔說,俺知道該怎麼做,無論別人說什麼,這個家我不能不管。
從三叔家出來,天已經很晚,他走進家門,姜秀芝還沒有睡。聽到開門聲,女人走出來。他問於大哥,三叔找你有啥事兒?
於大根說,沒啥大事兒,說了一些家裡的雜事。他沒有說那事兒,女人的聲音很低,怯怯地,帶著幾分羞澀。
大根沒有回答女人,推開了西廂房的門,對女人說,睡吧,沒什麼事兒。
大哥,女人叫了一聲,纏綿而柔美,這聲音裡帶著苦澀,帶著溫柔的淚水……(未完,待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