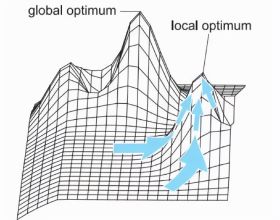二戰期間,隨著對英國的戰爭陷入僵局,政治聲望岌岌可危的希特勒,為了挽回其在“容克”軍官團以及軍工寡頭們心目中“戰無不勝”的形象,更為消除來自東方的所謂“威脅”,希特勒決心挑起一場新的戰爭,而他所選擇的對手,正是擁有著強大紅色武裝和空前動員能力的蘇聯。
希特勒雖然瘋狂,卻並不是一個瘋子。為了能夠最大限度地提升勝算,他和納粹德國頂尖的參謀團隊,苦心孤詣地擬定了一個宏大的進攻方案——著名的“巴巴羅薩”計劃……
“巴巴羅薩”計劃的由來
一般認為,希特勒早在1940年7月便決定向蘇聯發動進攻,並委託德國陸軍最高統帥部草擬了一份名為“奧托”計劃的作戰方案。但事實上,希特勒對東方的野心早在其執政之前便已然萌發,在其煽動性的施政綱領《我的奮鬥》一書中,希特勒便曾含糊地提出,為了奪取更多的“生存空間”,德國需要大力向東方擴張。
“巴巴羅薩”行動前,駐紮在東普魯士的德國士兵
而在此後的宣傳之中,納粹黨的喉舌們更不遺餘力地將德國人塑造為擁有“完美基因”的“雅利安人”後代,並將以斯拉夫人為主的東歐各民族歸入“未開化”的野蠻人行列。基於這套理論,打著“優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理論”的旗號,納粹德國從1939年便開始謀劃著所謂的“東方計劃”。
按照希姆萊等人設想,未來德國將透過軍事及逐步減少糧食供給等手段,逐步消滅定居於東歐境內的2000萬至3000萬斯拉夫人和猶太人,而在將剩餘的斯拉夫人驅逐至苦寒的西伯利亞之後,德國將透過25年的時間逐漸向斯拉夫人騰出的“生存空間”移民500萬至1000萬人,以最終實現當地的“日耳曼化”。
當然,納粹德國的高官們很清楚,在自己於東歐“跑馬圈地”、將眾多弱小民族收為奴隸的妄想前面,還阻擋著一堵名為“蘇聯”的高牆。因此,法國戰役剛剛結束,希特勒便授意陸軍參謀長弗朗茨·哈爾德(Franz Halder)安排人手擬定對蘇聯的進攻計劃。但此時整個德國陸軍都沉浸在佔領巴黎的欣喜若狂之中,哈爾德隨後便把這個任務交給了第18集團軍參謀長埃裡希·馬克斯。而如此安排,並非是馬克斯有什麼過人的軍事天賦,僅僅是因為第18集團軍剛剛受命從法國前線調往波蘭的波茲南佈防,一旦與蘇聯開戰,該部將首當其衝。
秉承 “容克”軍官團慣常於圖上作業的優良傳統。馬克斯很快便編寫出了一份名為“東方行動”的作戰方案,並草率地劃出一條自毗鄰北冰洋的蘇聯港口城市阿爾漢格爾斯克,經高爾基、羅斯托夫,直至裡海沿岸的阿斯特拉罕的攻擊停止線。
由於線段兩端的城市皆以字母A開頭,因此這條攻擊停止線又被稱為“AA線”,而之所以要將其作為德國陸軍入侵蘇聯的最終目標,馬克斯給出的解釋是,唯有如此才能令德國本土免於蘇聯空軍的遠端打擊。基於這一說法,我們有理由相信,馬克斯只是粗略地估算了蘇聯空軍當時最新列裝的Pe—8四發重型轟炸機的最大航程,便潦草地將戰線延伸至了距離德國本土2000多千米之外。
更為離譜的是,馬克斯認為德國陸軍僅需要9—17周便可抵達“AA線”。雖然很難理解他的自信從何而來,但有一個數據卻可供參考,那便是德國用了6周左右的時間便打垮了由法國、比利時、荷蘭以及英國遠征軍組成的300萬聯軍,從法德邊境一直打到了700千米之外毗鄰大西洋的法國布列塔尼地區。從這個角度來看,馬克斯計劃用1.5倍於法國戰役的時間打敗約290萬的蘇聯紅軍、抵達2000餘千米外的AA線,似乎算是“料敵從寬”。
1939年10月,在柏林總理府,希特勒授予弗蘭茨·哈爾德、古德里安、赫爾曼·霍特、阿道夫·施特勞斯、埃裡希·霍普納和弗里德里希·奧爾布里希特(從左至右)騎士鐵十字勳章
馬克斯的“東方行動”雖然粗糙,卻迎合了納粹德國此時目空一切的躁動情緒。以哈爾德為首的德國陸軍高層只是對其簡單進行了一些完善,便冠以“奧托計劃”的代號,於1940年12月5日呈交了希特勒。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德國陸軍曾同樣將以武力併吞奧地利的軍事行動,命名為“奧托計劃”,當時的“奧托”指的是流亡海外的奧匈帝國末代皇儲奧托·馮·哈布斯堡,但自德國吞併奧地利以來,奧托·馮·哈布斯堡便拒絕與納粹合作。因此,此處的“奧托”,指的是公元926年加冕為首任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德意志君主奧托一世。
應該說,德國陸軍選定這個代號還是花了些心思的,畢竟奧托一世不僅是神聖羅馬帝國的奠基人,更是德意志歷代君主中最早向東擴張的帝王。然而,方案提交上去,卻並未能討到元首的歡心。12月18日,希特勒下達了“第21號訓令”,正式要求德國國防軍在結束與英國的戰爭之前,用一場迅捷的軍事行動徹底摧毀蘇維埃聯盟,並親自將這一軍事行動命名為“巴巴羅薩計劃”。
一般認為,希特勒此處提到的“巴巴羅薩”,指的是公元1115年加冕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德意志國王腓特烈一世。雖然同樣都是“九五之尊”,腓特烈一世的文治武功相較於奧托大帝卻都要差上一大截。縱然領導過“第三次十字軍東征”,最終卻淹死在一條無名的小河之中,可謂“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那麼希特勒為什麼要用這樣“倒黴蛋”來命名這場至關重要的軍事行動呢?
有一些研究者想當然地以為,希特勒之所以否定奧托大帝,是因為這位皇帝歷史上曾大舉入侵過亞平寧半島,若以之為行動代號,極易引起盟友義大利的反感。而腓特烈一世雖然結局淒涼,卻終究曾引領過中歐地區的大小貴族踏上過東征之路,符合希特勒糾集義大利、芬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等國僕從軍大舉進攻蘇聯的“大戰略”。但若仔細分析便不難看出,“巴巴羅薩”之名的背後,有著更為殘酷的真相。
1941年,希特勒(左二)和德國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參謀長凱特爾(右一)、最高統帥部作戰部長約德爾(左一)等在總部研究作戰計劃
“巴巴羅薩”一詞,在古拉丁語中本意為“紅鬍子”。由於許多具有這一外貌特徵的人多是心狠手辣之輩,幾經傳播,這個詞便成為殺人越貨的代名詞。因此中世紀歐洲被冠以“巴巴羅薩”的強盜眾多,其中最著名的當屬15世紀得到奧斯曼帝國支援、橫行於地中海的海雷丁。因此希特勒以“巴巴羅薩”之名進攻蘇聯,並不單純是為了借古喻今、重現神聖羅馬帝國的榮光,而是期望德國軍隊在攻入蘇聯國土內後撕去文明的偽裝,以極度野蠻的燒殺擄掠去征服東方。
蘇聯在“巴巴羅薩”計劃前的反應
其實,作為一個與納粹德國有著複雜邊境糾紛和地緣政治糾葛且意識形態衝突嚴重的大國,蘇聯政府對柏林方面的一舉一動並非毫無知覺。面對納粹德國向蘇德邊境的增兵舉措,蘇聯軍方始終保持著高度關注。早在1941年4月10日,以鐵木辛哥為主席的蘇聯最高軍事委員會便要求西部軍區的所有部隊都進入戰備狀態。
蘇德戰爭期間,蘇聯國防人民委員鐵木辛哥元帥(右)與一名紅軍士兵在戰壕裡觀察作戰情況
5月13日,從蘇聯內地軍區調來的第19、第21、第22集團軍和從遠東方面軍、後貝加爾軍區調來的第16集團軍(下轄2個步兵軍、1個機械化軍)和第21軍,總計28個步兵師按照蘇聯陸軍總參謀部的要求,向第聶伯河、西德維納河流域開進,並編入西部特別軍區。
6月14日至6月19日,蘇聯國防委員會命令各軍區在當月21日至25日內,必須將指揮機構遷入野戰指揮所,對機場及其他軍事目標進行偽裝,坦克和汽車必須塗上偽裝色。而蘇聯紅軍總政治部起草的一份《近期紅軍中政治宣傳任務》小冊子更明確地提出“準備進行一場正義的、進攻性的、無堅不摧的戰爭”。
此時按照戰前的規劃,蘇聯紅軍沿縱深方向呈梯次配置。戰略第一梯隊包括西部各軍區的作戰軍隊共計171個師(104個步兵師、40個坦克師、20個摩托化師和7個騎兵師),分佈在從巴倫支海到黑海的4500千米戰線上。這些部隊之中,以56個師和2個旅部署於邊境地帶組成第一梯隊;52個師組成的第二梯隊,分佈在後方50至100千米處;62個師作為各邊境軍區的預備隊,分佈在距國界100至400千米處。
整個部署依託新國境線、1939年的舊國境線以及後方核心大城市做梯次防禦。北方以列寧格勒為後方核心,里加、塔林為核心前沿進行築壘,任務是保衛從邊境到列寧格勒的波羅的海沿岸國土;中部以莫斯科為後方核心,明斯克、斯摩稜斯克為核心前沿進行築壘,任務是保衛白俄羅斯以及通向莫斯科的奧爾沙路橋;西南以基輔為後方核心,敖德薩為核心前沿進行築壘,任務是保衛整個烏克蘭。
以上種種無一不說明,蘇聯紅軍已然敏銳感覺到戰爭的逼近,並著手進行準備。但必須指出的是,此時的斯大林恐怕並不相信希特勒會貿然對蘇聯發動進攻。畢竟,此時不列顛群島的上空,英、德雙方的空軍仍在纏鬥,而為了最大限度地開動戰爭機器,德國更需要來自蘇聯的各種工業原料。
所以,斯大林很可能仍認為希特勒在東線集中兵力的行徑,更多是為了營造一種緊張氣氛,以便維護其獨裁統治。同時,鑑於蘇聯與羅馬尼亞、芬蘭等國依舊存在著嚴重的邊境分歧,德國陸軍部署在這一區域,也可能真的只是一種防禦姿態。
正是基於上述分析,斯大林很難不將英國首相丘吉爾等西方政要發出的警告視為挑撥離間。與斯大林在戰略上誤判相比,蘇聯一線的高階軍官或許更能直觀感受戰爭逼近的腳步,但是此時的蘇聯紅軍似乎仍未掌握現代戰爭的精髓,在很多蘇聯軍官的概念中,戰爭或許仍將以邊境摩擦、小規模衝突的模式啟幕,並在雙方不斷投入精銳部隊和重型武器的過程中逐步升級。因此只要將精銳部隊集中到邊境附近,在後方部署充足的後備梯隊,便足以應對一切的挑戰。
因此,當1941年6月22日,“巴巴羅薩”計劃正式發動,相比較進攻發起的突然性,攻入蘇聯的德軍數量之巨、配合之緊密,才是讓蘇軍最為震撼的慘痛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