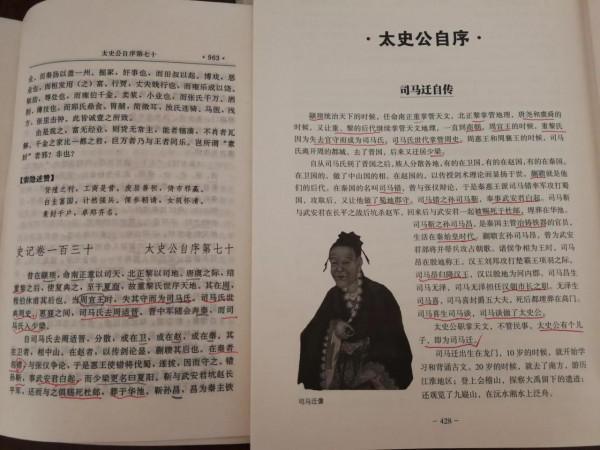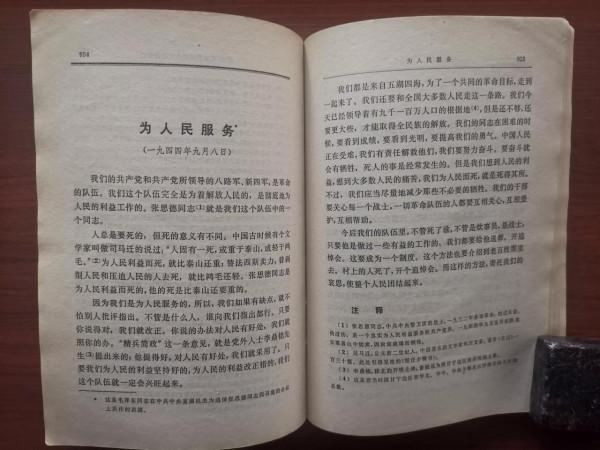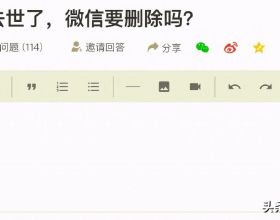今天學習李凱老師專講《史記》第四講——《報任安書》的微詞。
李老師首先指出,司馬遷寫《史記》有著自己的獨特性,這個獨特性,有一篇文字值得深入研究,就是著名的《報任安書》(又名《報任少卿書》。李老師從六個方面對這封信作了分析和解讀。
第一,任少卿的地位及給司馬遷寫信一事。
任少卿就是任安,《報任少卿書》收錄在《古文觀止》中,也被班固收在《漢書》中。任安是司馬遷的朋友,在漢朝歷史上有傳記,《史記》中也有《任安傳》。他的地位很高,擔任過北軍使者。當時漢家有南北二軍,北軍擔負著整個長安城的治安和戍衛重任。北軍使者是北軍的負責人,手握重兵。任安曾給司馬遷寫信,說您不應當頹廢,應當薦賢進士,給國家舉薦賢能之人。
第二,漢朝職官曆史的演繹、禮儀及司馬遷受宮刑後的政治待遇。
司馬遷在李陵之禍後,雖然慘遭宮刑,但還被漢武帝重用,充任中書令,這在漢朝的職官曆史發展上是一個里程碑。因為中國古代的職官有一個歷史趨勢,從王室或者皇家的私屬逐漸變成朝廷的大僚,由家而國這個發展的過程。先看宰相的“宰”字,什麼叫做宰?宰就是家宰或者叫臣宰,這是貴族的家臣,王的家臣,後來給王當大管家,掌丞天子處理萬機。王把家和國同化了,所以他的家臣——“宰”,後來成為宰相,“相”是輔佐的意思,就是由貴族之私屬而演變為朝廷之大僚。錢穆先生在《秦漢史》裡說得很清楚,在秦的三公九卿制中,九卿和三公很大的特色就是為皇室服務,只有幾個官是國的色彩,比如廷尉掌司法,治粟內史掌管財政,而另外的許多官都是為皇室服務,像剛才提到的丞相,基本上就是周朝的太宰,御史大夫相當於少宰,也就是小宰,御史中丞相當於宰夫。所以由朝廷的大僚看,他的確這時候還不是太明確,還有貴族私屬的特色,由貴族私屬逐漸發展為朝廷大僚。後來三公權力越來越大,皇帝受制於三公,往往按捺不住內心的憤怒。漢武帝採取手段,用聽他話的人來架空丞相,組成一個新的組織,史書稱之為中朝。中朝很重要的就是由兩撥人組成,第一撥人是文學侍從、貴姓長史,比如漢武帝重用過的司馬相如、衛青、朱買臣等人。而另外一撥人也進入中朝的,就是中長史、宦者,司馬遷就屬於這類人,以宦者的身份成為中書令。中書令就是皇帝的機要秘書。史書說漢武帝讓史官給自己的小兒子劉弗陵即漢昭帝講成王輔政圖。周成王年幼,聽他叔叔周公旦的,後來平息了三監之亂,治理卓越,周朝大治,迎來成康之治,周有成康,漢有文景。這個故事,電視劇《漢武大帝》就演成了由司馬遷講,司馬遷的身份一方面是史官,另一方面是漢武帝的貼身心腹。所以,當時司馬遷的處境是漢武帝的身邊人。
第三,司馬遷遲遲不給任安回信意味著什麼。
任安曾給司馬遷寫信,說你這麼重要的身份,不應頹廢,應給國家舉薦賢能。司馬遷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有搭理任安,這意味的是,你沒有受過宮刑,你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吧,我還薦賢進士呢,我給李陵說了一句好話差點人頭落地,我這倒大黴了,我噤若寒蟬你懂嗎?所以,他沒有理任安。
第四,西漢歷史上的“巫蠱之禍”。
漢武帝徵和二年,此時距司馬遷受宮刑的漢武帝天漢二年,已經過去了八年,天漢二年是公元前 99 年,徵和二年是公元前 91 年,這時出了一場大禍,叫“巫蠱之禍”。《史記》裡沒有太多記載,以“巫蠱之禍”為下限,很可能這一年司馬遷就停筆不寫了,再寫也沒法寫,那都是太敏感的話題。“巫蠱之禍”為漢代歷史上最大一次內訌,統治集團內部狗咬狗,據說當時長安的水渠都染成了紅色,誅殺上萬,太子兵敗。太子一度找過北軍使者任安,求他發兵,可任安按兵不動。這場變亂之後,漢武帝重重處理了一堆支援太子的人。任安因為沒有支援太子,而得到了皇帝對他的首肯和默許。可沒過多久,皇帝又說都是冤案,給太子平反,反攻倒算找到任安,質問他為什麼不發兵,為什麼不救太子?這時任安可是有口難辯,就被當做大奸大惡而判處腰斬。古代是秋後斬決,於是被關押在死牢之中,這就是公元前 91 年天漢二年的“巫蠱之禍”。這時司馬遷想起來了,任安還給自己寫過信,我得給他回信了,我要再不給他回信,他就看不到了。於是,司馬遷寫了《報任少卿書》,這個“報”字就是覆信的意思,你說讓我薦賢進士,我不是說不想,我是沒那個能力,我現在噤若寒蟬,想當初就是一句話給李陵求情,差點人頭落地,後來僥倖活了下來,受了宮刑,忍辱負重,這個心情你理解嗎?你當時根本不理解,而現在理解了吧,現在你的心情就是我當年的心情。
第五,關於《報任少卿書》的寫作時間的爭議。
王國維先生在考證司馬遷的生年卒年一系列年代學問題的時候,認為這封信應當寫於公元前 93 年,在巫蠱之禍出現之前,因為這個信裡頭有明確字樣,說皇帝要東巡,而皇帝東巡是有史書記載的,這下找到了具體的事件做依撐。但今天也有不少學者不讚許他的這個推論,認為應當完成於公元前 90 年,也就是剛才說的漢武帝徵和三年。我們認為,把它說成徵和三年更有依據,因為這時任安明確犯死罪,《報任少卿書》明確的說,任安幾次犯死罪,這是最重大的一次,其它的沒找到。所以這種說法是幾種年代的推論中最合理的,更重要的是與司馬遷的價值觀和心境彌合程度最高。在任安判死罪,捲入統治集團這場內訌的時候,司馬遷才有可能敞開心扉地傾吐肺腑之言。否則,如果任安是因為其它過失而被判死罪的話,我們認為還不大可能讓司馬遷說出這麼多深刻的話。
第六,《報任少卿書》的話題。
司馬遷給任安回信的話題,其主題詞就是“伴君如伴虎,噤若寒蟬”。司馬遷的這個價值觀,與《報任少卿書》的語境彌合度非常大。司馬遷為什麼要寫這封信?這封信就是他晚年如履薄冰的心境寫照。這封信如此,《史記》書也如此,許多內容欲言又止。即便說是微詞,今天我們看也不是潑婦罵街,許多環節都是點到為止,我對你進行批評,也是有理有據讓你服氣,應當說這都經過司馬遷一系列縝密的考量,表現出他史官的風格。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裡有這麼一句話:“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大意是說,人總有一死,有的人死得比泰山還重,有的人死得比鴻毛還輕,這是因為他們死的作用不同啊。
1944年9月8日,毛主席在著名的《為人民服務》的講演中,引用了司馬遷《報任安書》中的一這句名言。毛主席說:“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
願《史記》的生命之樹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