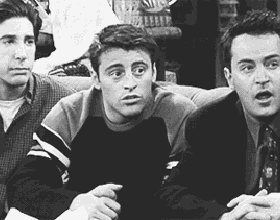“五嶺北來峰在地,九州南盡水浮天。”嶺南大地倚山臨海,地勢開陽。自古以來,嶺南人採中原之精粹,納四海之新風,融匯昇華,自成宗系,形成別具一格的嶺南文化。且務實、開放、相容、創新之風至今賡續不斷。而其文脈之傳承,實有賴於歷代學者開館授徒,薪火相傳。尤其是書院產生之後,學派紛呈,名人輩出,在中華文化之林中獨樹一幟。
清 黎簡《碧嶂紅棉圖》
嶺南文化源於何時
清初“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在《廣東文集》序言中說:“廣東居天下之南,故曰南中,亦曰南裔。火之所房,祝融之墟在焉,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極。極,故其發之也遲,始燃於漢,熾於唐於宋,至有明乃照於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稱廣東。”
屈大均認為,廣東在我國的南方,所以古代叫“南中”、“南裔”。這個地方,與天上二十八宿的“大火”房宿對應,也是“火神”祝融管轄的地域。在《易經》中,離卦屬火,又代表“文明”,而廣東正處於離卦之地,所以屈大均說“天下文明至斯而極”。
“極”,是指地理之極。古人一直認為,我國的文化發源地是中原地區。中原文化向南傳播至廣東,在地理上已是盡頭了。所以廣東的文化相對於其他地方起步較慢,在秦漢時期才開始萌芽。不過,嶺南文化雖然起步晚,但後勁十足,到唐宋時期已嶄露頭角,明代中葉之後,更是大放光芒,直追中原。發展到清代和近現代,又達到了一個高峰。
嶺南文化始於何人
屈大均曾說:“越人以文事知名者,自高固始。”
又說:“南越文章,以尉佗始。”
高固是南海人。周顯王時,嶺南地屬楚國管轄。高固才能出眾,為楚威王相。傳說他擔任楚相時,位於越秀山的“楚庭”有“五羊銜谷”之祥。
當時,有個名叫鐸椒的文官,見楚威王沒有通讀《左氏春秋》(即《左傳》),便把以往成敗得失的歷史經驗編為四十章,名為《鐸氏微》,由高固獻給楚威王,因此楚國文教日興。所以屈大均說廣東人從事文教事業是從高固開始。可惜的是,高固沒有文章流傳下來。
尉陀即南越王趙佗。漢初,漢文帝有《賜尉陀書》,尉佗也有《上漢文帝書》。屈大均認為尉陀的《上漢文帝書》“辭甚醇雅”,故說“南越文章,以尉佗始”。但又懷疑是由其來自中原的“秘書”代筆,未必是尉陀本人或南越人所作。
因此,高固和尉佗都算不上是嶺南文化的創始人。
那麼,嶺南文化的創始人是誰呢?
屈大均說:
“然則文其以漢之陳元為始乎?其請立左氏一疏,大有功聖經。次則楊孚有請均行三年通喪一疏,即其《南裔異物志》,辭旨古奧,散見他書,搜輯之亦可以為廣東文之權輿。”
屈大均在這裡只提及陳元和楊孚兩人,實際上陳元的父親陳欽,也是嶺南文化的開山祖。這三個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嶺南人。
嶺南經學的興起,始於陳欽
陳欽,字子佚,生於漢宣帝末年,世居蒼梧郡廣信(廣東封開縣及廣西梧州市一帶)。“廣信”的得名,是漢武帝平定嶺南後,鑑於原南海郡的郡治番禺城已焚為廢墟,遂將嶺南首府遷至蒼梧郡離水與鬱水的交匯處,並取名“廣信”,取意“初開粵地,宜廣佈恩信”。
因廣信地處中原與嶺南交通往來的水陸要衝,又一度成為嶺南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所以最早受到中原文化的薰陶,出現了嶺南地區最早的一批文化精英,其中最傑出的就是陳欽。
史籍記載,陳欽自幼博覽群書,熟習“五經”(《易》《書》《詩》《禮》《春秋》)。漢成帝時,被舉薦為“茂才”,師從經學大師賈護,研習《左氏春秋》。他博採眾長,融匯貫通,卓然自成一家,撰有《陳氏春秋》(已佚),與當時博學多才的經學名家劉歆齊名。
隨後,陳欽來到京師長安,被朝廷任命為“五經博士”。不久,又負責教育皇室子弟及貴戚。陳欽的弟子中,有兩人做了皇帝:一位是漢平帝,另一位是時任大司馬,後來篡漢的王莽。不過,陳欽雖是王莽的老師,但最終還是被王莽所害,在獄中自殺。
漢代的經學,有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之分。自漢武帝立經學博士後,今文派完全碾壓古文派,“五經博士”人是清一色的今文派學者。王莽改制,始立古文經學博士。陳欽是古文派學者,他能躋身於“五經博士”之列,在當時也是鳳毛麟角。更重要的是,他是嶺南研究經學的第一人。
嶺南人辦“書院”,始於陳元
陳元,字長孫。他幼承家學,傳習父業,逐字逐句對《左氏春秋》進行考證和註解。因所有精力和時間都用於經學研習,以至於“不與鄉里通”,被鄉親們視為“不近人情”。
東漢初年,陳元赴京城任議郎。由於他對《左氏春秋》考證深入,註疏周詳,見解獨到,一時名噪公卿。史稱他與當時著名的學者桓譚、杜林、鄭興齊名,“為學者所宗”。
陳元任議郎期間,做了兩件影響後世的事情:
一、力爭立《左氏春秋》博士。光武中興後,有人提出恢復“《左氏傳》博士”。當時朝廷對此事的爭議十分激烈,反對者範升等人認為“左氏淺末,不宜立”。陳元聞之,立馬上疏光武帝,據理駁斥,後又與範升反覆辯論十數次,最後陳元駁倒範升,光武帝遂允立“《左氏傳》博士”。
二、在洛陽設館授徒。雖然光武帝同意立“《左氏傳》博士”,陳元也是公認的第一人選,但漢武帝偏偏不用陳元,而任用第二人選李封為博士。沒多久,李封病死,光武帝本來就不太喜歡古文經學,於是趁機將“《左氏傳》博士”廢掉。
博士未當成,陳元便另尋他徑傳經。據史籍記載,陳元在京城洛陽“以授徒為業,傳《左氏春秋》”。陳元在洛陽設館授徒,可謂嶺南人辦私學之肇端,雖然當時不叫書院,但形式上與書院無多大差別。
陳元的著作《陳元集》及《左氏異同》均早已亡佚,所幸《後漢書·陳元傳》收入了陳元的兩篇疏議,這是歷史上由嶺南籍人士撰寫的最早的政論文章。
學者評價:二陳是“粵人文之大宗”
陳欽、陳元作為漢代古文經學派代表,對《左氏春秋》的研究達到了最高水平,是當時全國學術界的標杆。儘管陳欽、陳元的活動主要在嶺外,但他們不僅是吸納中原文化的先行者,同時也是嶺南文化的“拓荒者”。
《廣東通志》的儒林傳,把陳欽、陳元列為嶺南儒林之首,盛讚“陳元獨能以經學振興一時,誠嶺海之儒宗也”。
屈大均說:“粵處炎荒,去古帝王都會最遠,固聲教所不能先及者也。乃其士君子向學之初,即知誦法孔子,服習《春秋》,始則高固發其源,繼則元父子疏其委,其家法教授,流風餘澤之所遺,猶能使鄉閭後進若王範、黃恭諸人,篤好著書,屬辭比事,多以《春秋》為名。此其繼往開來之功,誠吾粵人文之大宗,所宜俎豆之勿衰者也。”
城中村裡深藏2000年“楊孚井”
漢代嶺南文化的“拓荒者”中,“二陳”沒有完整的著作流傳下來,活動遺址也蕩然無存。另一位重要人物楊孚,則不僅有較為完整的著作傳世,還有居住和著書講學的遺址可尋。
楊孚,字孝元,東漢南海郡番禺下渡頭村(今廣州海珠區下渡路)人。漢章帝時,楊孚獲舉薦北上京師洛陽,通過了朝廷舉辦的“賢良對策”考核,官拜議郎,以皇帝身邊近臣身份參政議政。
據《百越先賢志》等書記載,楊孚任議郎曾提出兩項重要主張。一是極力主張以孝治天下,要求郡國之士誦讀《孝經》,為漢和帝所採納,下詔命令“臣民均行三年通喪”,同時獎勵有孝行的臣民,救濟孤寡貧老者,影響深遠。二是提出“吏治必務廉平”,主張以廉潔作為選拔和考核幹部的標準,這一建言也獲得了皇帝的認同。
在珠江南岸的楊孚故居,古人多有題詠。如唐代詩人許渾有“煙深楊子宅,雲斷越王臺”,以及“河畔雪飛楊子宅,海邊花盛越王臺”句,表明至少在唐代,“楊子宅”已成廣州名勝,可與“越王臺”媲美。
楊孚故居保留了很長時間,“失蹤”的時間可能是明末。清乾隆年間的《番禺縣誌》曾記載:“後有張瓊者,掘地種蔞,得一磚刻雲:楊孝元宅。”這個獲磚之地,被確認為楊孚宅第遺址。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也提及此事。
現在,楊孚故居只剩下一處遺址,就是原楊孚故居後花園的“楊孚井”。這口形制古拙的紅砂岩古井,正是當年楊孚所開鑿,雖已有近兩千年曆史,但至今井水依然清澈。不過,這口井藏在海珠區的城中村中,要找到它著實不易,即使是廣州人,也可能會“蕩失路”(迷路)。
想參觀“楊孚井”,最好乘坐廣州地鐵8號線,在鷺江站B出口出站後左轉,進入下渡路,往前走數百米,走到冠記腸粉店處,就左轉進入旁邊小路,可見到不遠處有“楊孚故宅”照壁,然後按指示牌找到下渡東約一巷,就可見到“楊孚井”了。如乘坐公交車,可坐8路、24路、93路、182路、229路車等到下渡路口。
帶回松樹種宅前,珠江南岸變“河南”
楊孚從洛陽榮歸故里後,從河南帶回兩棵松樹植於宅前。這本來是一件日常小事,但不久後,便發生了令人嘖嘖稱奇的“怪事”。
據《廣東新語》記載:“廣州南岸有大洲,週迴五六十里,江水四環,名河南。人以為在江水之南,故曰河南,非也。漢章帝時,南海有楊孚者……其家在珠江南,嘗移洛陽松柏種宅前,隆冬蜚雪盈樹,人皆異之,因目其所居曰河南,河南之得名自孚始。嶺南天暖無雪,而孚之松柏獨有雪,氣之所召,無間遠邇。雪其為松柏來耶?為孚來耶?”
廣州地屬無冬區,冬季一般不會下雪。但自從楊孚帶回洛陽松柏後,北方之雪便隨著他移植的松柏來到無雪之地,且只落在楊孚宅前的松柏上。此事確實有點神奇,人們搞不清楚飛雪是為松柏而來,還是為楊孚而來。出於對楊孚的敬仰,人們稱他所居住的地方為“河南”,並尊稱他為“南雪先生”。久而久之,約定俗成,進而把四面環水的整個“江南洲”也稱之為“河南”。
因此,屈大均認為:“河南之得名自孚始。”至今,廣州人仍稱呼珠江南岸的海珠區為“河南”。
此外海珠區不少地名也與楊孚移植松樹有關。歷代文化人以“門鄰楊子宅”為榮,百姓則紛紛種植松樹。由此出現了不少與松樹有關的地名,如萬松園、萬松山、大松崗、半松坡等,可見楊孚在民間的影響之大。
撰寫《南裔異物志》,漱珠崗上講學
楊孚是通才式人物,既有卓越的政治才華,又有淵博的文史學識。
在洛陽當議郎時,楊孚瞭解到交趾部和郡縣長官為了討好朝中權貴,大肆搜刮嶺南特產,“競事珍獻”,致使民不聊生,怨聲載道。便上疏提出嚴禁此類行為,懲治貪官汙吏。
同時,他還把嶺南土特產分列條目,撰寫成《南裔異物志》,並“列舉物性靈悟,指為異品,以諷切之”。此書一出,嶺南異物廣為人知,貪官汙吏不得不有所收斂。
《南裔異物志》原書在宋代已失佚,後人轉相引用,故“散見他書”。清代南海人曾釗從諸書中重新輯錄成兩卷本《異物志》,流傳至今。這本書開我國學者雜記地方風物之先河,為此後同類撰述開拓了新領域,漢代以後,步其後塵者層出不窮。
在史學領域,楊孚的《南裔異物志》處於正史與稗史之間,在當時史學門類單一、尚未充分發展的時代,為史學創立了新的門類。
楊孚晚年從京城退休,返穗定居。他見附近有一山崗(即現在的漱珠崗)奇石疊起,老樹參天,環境清幽,便結廬其間,名之為“石邊祠”,在此講學和著書,漱珠崗從此留下了嶺南書院的早期印記。
南宋時,嶺南文化名人崔與之慕名而來,也在漱珠崗設帳講學。清末道士李明徹在漱珠崗建純陽觀時,為紀念楊孚和崔與之,在純陽殿兩側建楊孚祠和崔清獻祠。
此後,漱珠崗便成為文化人的聚會點。清同治年間,名畫家蘇六朋在此建松枝仙館;嶺南畫派奠基人居巢、居廉常來此登高作畫;其後“二居”弟子高劍父、高其峰、陳樹人等在此栽梅樹,結成“梅社”,並將社名刻於漱石上。
學者評價:嶺南“詩始楊孚”
楊孚的《南裔異物志》,多為散文,亦有四言韻文的“讚語”,文體頗為獨特。後人認為,楊孚在行文中運用藻言韻語,是為了便於士民誦讀。
正因此書文體獨特,屈大均《廣東新語·詩語》中,有“詩始楊孚”一條,屈大均說:“其為《南裔異物贊》(即《南裔異物志》),亦詩之流也。然則廣東之詩,其始於孚乎?”
標題為“詩始楊孚”,然後行文又打問號,屈大均之所以不肯輕易下結論,是因早在西漢初年,嶺南人張買“鼓棹能為越謳”。有一次他陪伴漢惠帝劉盈在苑池遊樂,一邊划槳,一邊唱自己改編的廣東民歌,歌詞頗有諷諫之意,讓漢惠帝有所領悟。
不過,張買充其量只是個“歌星”,不能稱之為“詩人”,且張買沒有作品流傳下來,廣東真正的“詩祖”,還是楊孚。
楊孚在嶺南文化史上還有一項第一。因《續後漢書·五行志》注引楊孚《董卓傳》,這也是嶺南人著作被載入史志的頭一回,所以曾釗說:“粵人著作見於史志,以議郎為始。”
文:廣州日報·新花城記者 鍾葵
圖:廣州日報·新花城記者 鍾葵
廣州日報·新花城編輯 戴雨靜
【來源:廣州日報全媒體】
宣告:此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若有來源錯誤或者侵犯您的合法權益,您可透過郵箱與我們取得聯絡,我們將及時進行處理。郵箱地址:[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