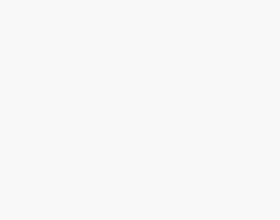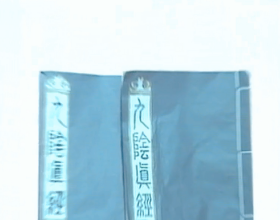【直新聞按】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22年經濟工作的基調是“穩字當頭、穩中求進”。2021年全年,中國的GDP同比增長了8.1%,達到了人民幣114.4萬億元,然而第四季度增幅走低,受到外界關注。
走低意味著此前走高,增幅高高低低之間對國民經濟的健康執行帶來哪些機會?為什麼說這種走低是受短期收縮性措施的影響?是否可控?新的一年,中國經濟的增長空間在哪裡?美聯儲加息對中國的貨幣政策將產生什麼影響?2021年,中國淨增人口僅為48萬,值不值得擔憂?此外,一項影響深遠的措施正在深圳進行試驗——放寬市場準入特別措施。過去為什麼要管治?現在又為什麼要放開?為什麼選擇在深圳首吃“螃蟹”?
帶著這些問題,深圳衛視直新聞專訪了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教授。
林毅夫,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第十二屆、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曾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世界銀行高階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貼。2013年9月被聘任為國務院參事。
訪談中最令記者印象深刻的是,林毅夫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歷程瞭然於胸。無論是不同時期的經濟執行資料,還是政策應對,他都如數家珍。當記者表示,“聽起來您對今年的中國經濟還是有信心”時,林毅夫笑著點點頭。
有人說,中國經濟發展史就是“中國崩潰論”的失敗史。訪談結束後,記者問林毅夫怎麼看這句話,他笑言道:“我們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中國經濟有自己的發展路徑。”
林毅夫對記者強調,他相信,2022年的經濟增速應該會在可接受的區間內。
以下是專訪實錄。
深圳衛視直新聞駐京記者 唐萍:國家統計局公佈的人口資料引發大家關注,2021年的人口淨增長僅僅為48萬,有觀察說中國的人口“零增長”甚至是“負增長”時代提前來了,這會給中國經濟未來的預期帶來什麼影響?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林毅夫:對經濟發展作出貢獻的不是人口,而是勞動力。現在出生率低,它影響勞動力也是15年後的事,當前勞動力並沒有減少,所以對當前影響其實並不大,尤其在短期之內,重要的是怎麼樣讓我們能夠不斷地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把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空間應用好的話,我們的經濟還是會維持一個比較高的增長勢頭。
對於未來的話,現在人口增長速度下降,可能接近0,15年、20年以後會不會造成勞動力瓶頸?我想這個問題要這麼分析,首先來講,對經濟增長重要的不是勞動力的數量,而是勞動力的質量。對生產的貢獻更大,質量是比數量更重要的。如果在這段時間裡,我們可以針對這種人口趨勢,加強教育,提高勞動力的質量,到那時候數量雖然不增加,但質量增加了。
第二,我們15年、20年以後收入水平提高了,經濟要發展,主要是資本更密集、技術更密集的產業。這種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就不是那麼大。
第三,我們如果說要真正解決勞動力短缺問題,我們國內的退休年齡相對來說較早,現在男的60歲退休,女的55歲退休,國際上一般是65歲,或是更高年齡才退休。所以如果真的是數量的問題,我想我們也可以延長退休年齡。
所以我並不是說人口因素不重要,但是我們要分析人口因素對我們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是透過什麼機制。從這種機制來看的話,短期沒有什麼影響。長期的話,我們可以靠提高勞動者的質量,然後再加上產業升級,需要發展的產業是資本跟技術更密集的,它需要有高質量的勞動力。如果要解決勞動力短缺限制的話,辦法就是可以把退休年齡適當延長一點。
深圳衛視直新聞駐京記者 唐萍:中國2021年GDP同比增長了8.1%,但是第四季度的增幅走低引發了關注,您認為這其中潛藏了哪些經濟下行的壓力?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林毅夫:經濟發展取決於年度之間的增長不要大起大落。在2021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增長率非常高的情況下,推出短期收縮性政策措施,可以提供一個視窗機遇期,更有利於我們經濟的長遠發展。大家也知道,我們連續推出了幾項房地產政策、平臺治理等調控措施,這種政策短期內會有收縮性,因此在第三季度、第四季度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有所下滑,而全年平均8.1%的GDP增速仍是相當高的。未來中國仍將根據2022年的經濟發展需要,採取必要的宏觀政策措施,讓我們的經濟增長趨於平穩。我相信,2022年政府有關部門的措施推出以後,經濟增速應該還是會在可接受增長區間內的。
深圳衛視直新聞駐京記者 唐萍:我們今年要怎麼樣才能止住“經濟增速”下行趨勢?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林毅夫:作為一個還在追趕的國家,我們有很多發展空間,例如產業升級、技術創新的空間,以及與“新經濟”發達國家齊頭並進的創新空間,例如在基礎設施方面,像“新經濟”所要的新基礎設施、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是政府可以作為積極財政政策著力的地方。同時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離不開金融支援,所以如果貨幣政策採取一定程度的寬鬆,就能夠鼓勵更多民間的投資。在這幾個方面的綜合作用之下,應該可以讓我們在2022年的經濟增長穩定在合理區間內。
深圳衛視直新聞駐京記者 唐萍:國際形勢方面,美聯儲加息會給中國的貨幣政策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林毅夫:美聯儲加息很可能會使得短期美元升值,資金可能從一些發展中國家流回美國。這種情況對於一些國家的宏觀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將會有挑戰。但是,因為中國相比其它發展中國家有一點優勢——我國對短期資金的流動一直有管理,只要針對短期資金流動的可能性採取必要的管理措施,那麼美元加息帶來的國際資金迴流美國的影響就會得到緩解。更何況我們還有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也意味著我國的貨幣政策應用的空間會比其它發展中國家貨幣應用的空間更大。我們受到美元加息的衝擊,應該會比其它國家小得多,我們只要把國內的事情做好,我們的經濟就能夠按照預計的增長速度、增長方式來執行。
深圳衛視直新聞駐京記者 唐萍:最後一個問題是關於深圳再次首吃“螃蟹”的。國家發改委和商務部召開《關於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放寬市場準入若干特別措施意見》的釋出會。為何選擇在深圳進行這項改革?放寬市場準入將如何激發市場活力?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林毅夫:首先,為什麼我們在改革開放的這段時間裡,要對市場準入有所管制,最主要就是我們在改革開放初期,還存在大量的、資本非常密集的、違反我們國家比較優勢的這種產業。如果沒有保護補貼,這種產業可能就難以生存,所以當時市場準入的限制,實際上是對違反比較優勢產業的一種保護方式。
那麼現在為什麼要放開?因為我們經過40多年的發展,資本積累得很快,要求稟賦結構的變化,比較優勢的升級,已經符合我們的比較優勢了,它的市場準入就可以放開。所以這裡面反映的,實際上是我們國家發展程序中比較優勢的變化,那麼政策應該相應地隨著這種條件的變化來調整。
為什麼選擇深圳作為先行示範區?因為深圳從原來一個小漁村開始,也是從勞動密集型的加工類開始的,但深圳這些年已經是領先全國的發展,現在在人均GDP發展水平裡,已經排在全國的前沿了。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的政策都是先找一個地方來做試點,來看它的效果怎麼樣,然後有什麼經驗可以總結。
深圳作為全國的特區,它的政策總是走在全國的前沿,所以我們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怎樣構建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剩下幾個還有待突破的領域,包括原來保護的這種資本比較密集、比較先進產業市場準入的放開。我想找深圳來做試點,一方面是對深圳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深圳的條件,在全國來說是比較好的,它有這個條件來做試點。
我也非常希望,深圳能夠在改革開放以後,在我們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時候,它總是以一個先行先試的方式,走向市場經濟,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的新框架之下,能夠再發揮深圳的作用,為全國在最後的攻關、最後的衝刺做出成績來。
作者丨唐萍,深圳衛視直新聞駐京記者
編輯丨葉俊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