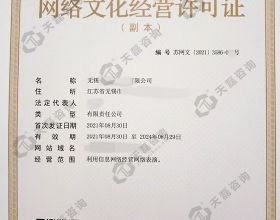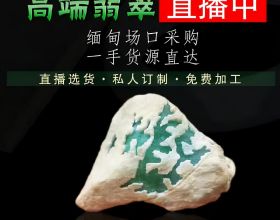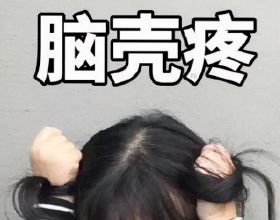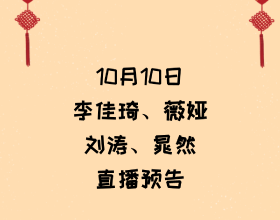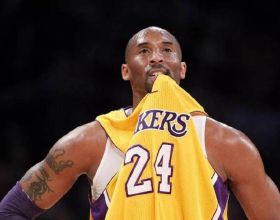多羅郡王家族墓在今天的房山區長溝鎮西甘池村和韓村河鎮二龍崗村一帶,歲月變遷,時至今日多羅郡王家族墓遺存建築已經無多。要了解清代多羅郡王這個顯赫的郡王家族,我們首先得弄清楚清代的王爵襲封制度,以及滿清近三百年曆史中出現的12位鐵帽子王。
大概是進一步吸取明王朝藩王制度造成的王室貴族尾大不掉、消耗民力、滋生腐敗的教訓。清朝王爵制度不僅約束了授封親王等王室貴族的封地自由,而且規定了爵位世系遞減降級的制度。也就是說親王世子承襲王位降級為郡王,而郡王子承襲則降級為貝勒,依次類推。但是,清初有6位親王和2位郡王因戰功赫赫,得以不受這項制度約束。他們的王爵世襲罔替,親王的世子仍然還是親王。此8位被稱為“鐵帽子王”,8人名聲之大,即便不熟悉大清歷史者,亦能聽聞一二。如,和碩禮親王代善、和碩睿親王多爾袞、和碩豫親王多鐸等等。清朝中後期,亦有4位親王授封,也就是雍正朝的允祥,晚清的奕訢、奕譞和奕劻。
筆者此次考察的多羅順承郡王家族墓,即是這2位“鐵帽子”郡王中的一支。多羅順承郡王與多羅克勤郡王皆為和碩禮親王代善後裔。代善是努爾哈赤第二子,在太祖長子褚英早死後,代善實際為諸貝勒之首,後又有擁護皇太極和福臨繼位之功,得到“鐵帽子王”的待遇也在情理之中。代善有子八人,長子嶽託戰功卓著,授封多羅克勤郡王,是為克勤郡王一支之始。三子薩哈璘成為世子,也就是和碩穎毅親王。薩哈璘二子勒克德渾因戰功,於順治五年(1648) 授封多羅順承郡王,郡王位可以永世罔替,也就是筆者此番考察的第一代“鐵帽子”順承郡王,諡號“恭惠”。
勒克德渾繼承了父輩驍勇善戰的特點,為清朝入關以後掃清明朝殘餘勢力立下了汗馬功勞。可惜順治九年,年僅34的他病逝,由四子勒爾錦繼爵位。勒爾錦同樣驍勇善戰,其最大功績就是任寧南靖寇大將軍,平定了吳三桂叛亂。但在戰役最後階段卻因貽誤戰機遭到削爵,順承郡王爵位相繼由其四位兒子勒爾貝、延奇、充保及穆布巴繼承。至康熙四十三年(1715年),穆布巴因不法被削爵。順承郡王爵位又改由勒克德渾、勒爾錦兄長諾羅布繼承。自此,諾羅布後代相繼襲得順承郡王爵位。順承郡王共歷10代15位,自第一代順承郡王勒克德渾始,幾乎歷代順承郡王墓址都選在今天的房山區西甘池村、二龍崗村一帶,是為多羅順承郡王家族墓。
據馮其利《北京王爺墳》一書考證,西甘池村葬有11代順承王,分別是:順承恭惠郡王勒克德渾、勒爾錦、勒爾貝、延奇、充保、忠郡王諾羅布、慎郡王恆昌、簡郡王倫柱、勤郡王春山、敏郡王慶恩、質郡王訥勒赫。二龍崗村葬有3代順承王,分別是:錫保、恪郡王熙良、恭郡王泰斐英阿(末代順承郡王訥勒赫死於民國,無王陵)。時過境遷。如今僅剩下4座寶頂、4通石碑。其中4座寶頂和3通石碑位於西甘池村,二龍崗村僅餘1通石碑,為第10代順承恭郡王泰裴英阿陵墓之碑。
筆者此番到訪西甘池村,見到的景象基本與前人所做的考古調查一致。由西甘池村東南口進入村子,前行百米再向左百米,即可看到一處被柵欄圈起來的方形廢園,園內雜草叢生,附近村民傾倒的糞水淌滿地面,園內南北兩側各有一通石碑,體量相當。相比之下,南側的較為簡單,而北側石碑贔屓座下水盤雕刻更為精美,四角各有一小鬼,南碑水盤僅為波浪圖案。兩碑中,南碑為一代王勒克德渾碑,順治十二年(1655年)十月初八日立。北碑為勒克德渾三子,七代王諾羅布碑,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五月初七日立。在進村公路北側,與此二碑相距300米的一村民院內,還有一通石碑。從外可見贔屓頭已經被砌於院牆內,而高大的碑首從很遠就可望到。該碑主是第12代順承簡郡王倫柱,立於道光四年(1824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南側碑園後本就是陵墓神道,依王墓建築的宏大森嚴法則,這裡儼然非常寬廣。然而時至今日,完全建於順承郡王家族墓地上的西甘池村,村民的院落已經把王陵大院切分成了很多小格子。從村中公路繞過院牆,可以看到正對碑園後300米的陵墓寶頂,南北橫向排列,一共三座。關於這三座寶頂,墓主何人,尚沒有定論。但顯然,中間最高大者為一代王勒克德渾,而北側者應該是其三子,七代王諾羅布。作為第二代順承郡王的勒爾錦,由於生前遭到削爵,死後亦只能孤零零地葬在其父陵園南面400米的位置。西甘池村遺存的四座寶頂中的第四座,正是指二代順承郡王勒爾錦寶頂。三座寶頂所在位置已經是西甘池村最南端,再向南就是村民的田地。此時正是秋末,玉米才收割完畢。沿著地頭田埂南向走400米,到勒爾錦寶頂前,這座寶頂較前三座要小很多,且寶頂上有明顯的盜洞被封堵痕跡。
有資料顯示,多羅順承郡王家族墓內享殿毀於1948年的戰火。但是顯而易見,後世人口的過度繁殖遷徙,才是造成這處宏大王陵墓區毀壞的真兇,且這一趨勢仍在蔓延。行走在西甘池村內,可以輕易在角落裡發現當年陵區建築物的殘件,如一處漢白玉柱櫥、一段陵牆。在三座大寶頂北側,又建起了新房,這戶人家的大門正對北側寶頂。這與兩三年前其他同道者尋訪時,“三座寶頂位於一片菜地之中”的描述又發生了變化。至於那通被村民院子圈進去的龜馱碑,則更顯示出順承郡王墓的變遷和時下的衰敗晚景。無疑,簡郡王倫柱的寶頂就在碑後百米的範圍內,但是這裡已經是一排排緊密連線的院落,至於輪柱的寶頂和地宮自然早已煙消雲散。在逝者亡靈的安息之所上,又在演繹著一戶戶人家的喜怒哀樂。這便是歷史的輪迴,人世的無常。(摘自筆者文章《三訪清代王爺墳05·尋找清多羅順承郡王家族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