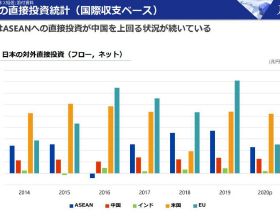曾經記得讀朝鮮戰爭相關書籍的時候,當時中國政府曾多次透過各種渠道向美國表明,中國人民不會對朝鮮戰爭置之不理,可是美國政府就是顧若罔聞,他們認為,僅憑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一句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說明不了什麼,況且在舊中國近100年的歷史裡,都是被外國列強按在地上打,怎麼憑毛澤東主席一句話,就會有任何改變呢?
這也是我多年一直不太能理解的地方,同樣還是那個國家的百姓,在國民黨統治時期,被日本侵佔了大半個中國,生靈塗炭,為什麼從中國共產黨1921年成立,到1953年在朝鮮戰場上打敗美國聯軍,這短短30年的時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使曾經飢寒交迫,到處被人欺負的中國人民,可以打敗當時武器最先進的美國聯軍?
透過讀《紅星照耀中國》這本書,我基本上找到了一些答案。
作者透過在解放區的4個月的親身經歷告訴了我們,在當時的解放區和國民黨統治區有著怎樣的區別,真是一個是天堂,一個是地獄。
例如,共產黨政策中的一個根本要素---重新分配土地
當時中國農民在舊政權下所承受的各種苛捐雜稅等遠遠超出了實際的承受能力,民不聊生,怨聲載道。現在,紅軍不論到哪裡,他們都毫無疑問地根本改變了佃農、貧農、中農以及所有“貧苦”成分的處境。在新區中第一年就取消了一切租稅,使農民們有透口氣的機會;其次,他們把土地分給缺地農民,大片大片地開“荒”-多數是在外或在逃地主的土地。第三,他們沒收有錢階級的土地和牲口,分配給窮人。透過這些措施,使農民自己擁有了土地,不用再被地主剝削,真正的翻身做主。這樣就釋放出了巨大的生產力和活力。
在蘇區工廠的工人每月工資十到十五元,膳宿由國家供給。工人可得到免費醫療,工傷可以得到補償。女工懷孕生產期間有四個月假期,不扣工資,還為工人的子女設了一個簡陋的託兒所。做母親的可以得到她們的一部分“社會保險”,那是由從工資額中扣除百分之十加上政府同額津貼所得的一筆基金。
政府捐助相當於工資總額的百分之二的款項供工人作文娛費用,這些基金都由工會和工人組織的工廠委員會共同管理。每星期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時。作者訪問的時候,那些工廠都一天開工二十四小時,分三班倒一也許是中國最忙的工廠!
如果我們把當時生活在同中國其他地方的國民黨統治區做一對比,才能瞭解差距有多大,例如,上海的工廠裡,小小的男女童工一天坐在那裡或站在那裡要幹十二三個小時的活,下了班精疲力盡地就躺倒在他們的床-機器下面鋪的髒被子-上睡著了。繅絲廠的小姑娘和棉紡廠的臉色蒼白的年輕婦女-她們同上海大多數工廠的包身工一樣-實際上賣身為奴,為期四五年,給工廠做工,未經許可不得擅離門警森嚴、高牆厚壁的廠址。一九三五年在上海的街頭和河浜裡收殮的兩萬九千具屍體,這些都是赤貧的窮人的屍體,他們無力餵養的孩子餓死的屍體和溺嬰的屍體。
對於蘇區的這些工人來說,不論他們的生活是多麼原始簡單,但至少這是一種健康的生活,有運動、新鮮的山間空氣、自由、尊嚴、希望,這一切都有充分發展的餘地。他們知道沒有人在靠他們發財,他們已經意識到他們是在為自己和為中國做工,而且他們說他們是革命者!
這種變化何其壯哉!
人們從被資本家壓迫的身份變成了自己當家做主,無論再苦再累都是在為自己而工作。打起仗來,也不再是為某個軍閥賣命,而是在為自己的國家而戰鬥,正是應驗了毛澤東主席的那句話“中國人民如果加以訓練,武裝,組織,他們也會變成不可征服的偉大力量的。”
作者簡介:
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1905年7月17日—1972年2月15日)生於美國密蘇里州,美國著名記者。代表作《紅星照耀中國》。他於1928年來華,曾任歐美幾家報社駐華記者、通訊員。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諾同時兼任北平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1936年6月斯諾訪問陝甘寧邊區,寫了大量通訊報道,成為第一個採訪紅區的西方記者。
新中國成立後,他曾三次來華訪問,並與毛澤東主席見面。1972年2月15日,斯諾因病在瑞士日內瓦逝世。後人遵照其遺願,其一部分骨灰葬在中國,地點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
寫作背景:
一九三六年是中國國內局勢大轉變的關鍵性的一年。埃德加·斯諾帶了當時無法理解的關於革命與戰爭的無數問題,六月間由北平出發,經轉西安,冒了生命危險,進入陝甘寧邊區。他也是在紅色區域進行採訪的第一個西方新聞記者。
他達到了目的。他衝破了國民黨以及資本主義世界對中國革命的嚴密的新聞封鎖。首先他到了當時蘇區的臨時首都保安(即志丹縣),和毛澤東同志進行長時間的對話,蒐集了關於二萬五千里長徵的第一手資料。然後,經過長途跋涉,他到達了寧夏南部的預旺縣,這已經是和國民黨中央部隊犬牙交錯的前沿陣地了。最後他冒著炮火,重新折回保安,由保安順利地到了西安。當他回到北平時,正是西安事變爆發前夕。他在北平首先為英美報刊寫了許多篇轟動一時的通訊報道,然後彙編成一本書,書名是《紅星照耀中國》。
“紅星照耀中國”,甚至還照耀世界,作為一個資產階級報紙的新聞記者,他已經預感到了,雖然他當時的報道,侷限於中國的“西北角”一片人口稀少的荒涼的被國民黨強大部隊重重圍困的紅軍根據地。這四個月旅行使一個來自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新聞記者,在思想感情上起了極大的變化。他對於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人,革命的戰士、農民、牧民、工人、共青團員、少先隊員,有了真摯的熱烈的感情,從而對於在革命與戰爭的激浪中的中國,有了深刻的正確的認識。這種認識不久就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和盧溝橋事變以後的全面抗日戰爭所證實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紅星照耀中國》就由倫敦戈蘭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到了十一月已發行了五版。這時候斯諾正在上海這個被日本帝國主義包圍的孤島上。當時上海租界當局對中日戰爭宣告中立,要公開出版發行這本書是不可能的,在繼續進行新聞封鎖的國民黨統治區,是更不必說了。但是得到斯諾本人的同意,漂泊在上海租界內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中共地下黨員的領導下,組織起來,以“復社”的名義,集體翻譯、印刷、出版和發行這本書的中譯本。斯諾除了對原著的文字作了少量的增刪,並且增加了為原書所沒有的大量圖片以外,還為中譯本寫了序言。由於當時所處的環境,中譯本用了《西行漫記》這個書名,作為掩護。
《西行漫記》出版以後,不到幾個月,就轟動了國內以及國外華僑所在地。在香港以及海外華人集中的地點,出版的《西行漫記》的無數重印本和翻印本。
埃德加·斯諾 一九三八年中譯本作者序
這一本書出版之後,居然風行各國,與其說是由於這一本著作的風格和形式,倒不如說是由於這一本書的內容罷了。從字面上講起來,這一本書是我寫的,這是真的。可是從最實際主義的意義來講,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革命青年們所創造,所寫下的。這些革命青年們使本書所描寫的故事活著。所以這一本書如果是一種正確的記錄和解釋,那就因為這是他們的書。而且從嚴格的字面上的意義來講,這一本書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寫的,而是毛澤東、彭德懷、周恩來、林伯渠、徐海東、徐特立這些人-他們的鬥爭生活就是本書描寫的物件-所口述的。
此外還有毛澤東、彭德懷等人所作的長篇談話,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辭,解釋中國革命的原因和目的。還有幾十篇和無名的紅色戰士、農民、工人、知識分子所作的對話,從這些對話裡面,讀者可以約略窺知使他們成為不可征服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慾望,那種熱情。-凡是這些,斷不是一個作家所能創造出來的。這些是人類歷史本身的豐富而燦爛的精華。
此外《西行漫記》值得一提的,是透過紅軍的經驗所得到的一種客觀教訓,就是有組織的民眾-尤其是農民大眾--在革命游擊戰爭中的不可征服的力量。我記起毛澤東向我說過一句話,因為毛所預測的許多事,現在已變成真實的歷史,所以我把這句話再重述一遍。他說:“紅軍,由於他自己的鬥爭,從軍閥手裡,爭得自由,而成了一種不可征服的力量。反日義勇軍從日本侵略者的手裡奪得行動自由,也同樣地武裝了自己。中國人民如果加以訓練,武裝,組織,他們也會變成不可征服的偉大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