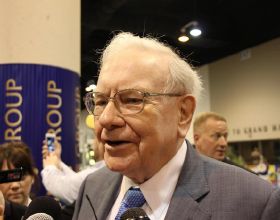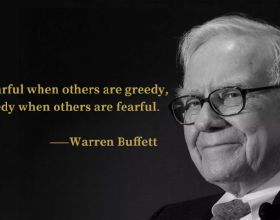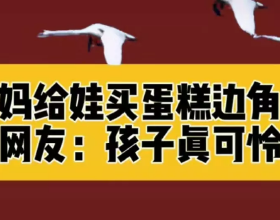對於分佈眾多的鄉村普通廟宇而言,進入21世紀後,隨著鄉村社會經濟水平的提高和村民生活條件的改善,村廟重塑、祭拜習俗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發展。但近年來,大量年輕一代和精英分子離開鄉村,傳統村落呈現凋敝態勢,村廟的維護及鑲嵌在廟宇中的民間信仰文化再次面臨傳承危機。如筆者在對魯中地區鄉村廟宇的調查中發現,許多村廟佔地面積較小,興修年代較近,缺乏鮮明的民俗特色,大多數只能處於“自娛自樂”的現狀,無法達到像高丙中教授在考察範莊龍牌會的歷史變遷中所指出的,民間廟宇透過雙名制可以有效化解當下信仰活動中的高度緊張狀態。大部分村廟作為民間信仰習俗的活動場所,在鄉村治理方面發揮著輔助教化的作用,但往往僅能滿足部分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民俗傳承功能大大弱化。
滿足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鄉村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躍進的過程中,其內在裂變的激烈程度遠遠甚於城市。鄉村轉型給農民心理帶來諸多不適應與苦痛煩惱,加之外在生存因素影響,往往使他們有強烈的心理慰藉訴求。當外在因素的干擾和內在心理的困頓交織在一起時,一個合適的釋放渠道就顯得尤為重要。一方面,村廟的存在恰恰可以滿足部分農民的心理需求,雖然此類需求充滿著世俗化的功利氣息,但是透過廟宇平臺,部分農民可以將世俗生活中的壓抑感轉化為對他人無害的信仰,從而使自己獲得某種解脫感。另一方面,社會轉型時期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基層政府治理能力的疲軟、文化娛樂生活的匱乏等,在一定程度上給邪教以可乘之機。從這個層面考慮,民間信仰習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邪教異端在鄉村土壤的滋生繁衍。
可以有效降低政府的鄉村治理成本
民間信仰所傳達出的樸素情懷具有一定的正向價值導向作用,從這一角度考慮,民間信仰習俗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倡導並行不悖。民間信仰可以增強信任感,起到規範和聚攏作用,透過各種儀式、制度促進村民的合作,從而提高社會效率。將民間信仰視為一種社會資本,可以有效降低政府的鄉村治理成本,體現“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推動和諧社會的構建。如很多村民對民間信仰神祗懷有敬畏之心,相信樸素的“因果報應論”,在祭祀儀式中,不論是祈福還是懺悔,均表現出虔誠的態度。可以說,廟宇規範了人神之間、信眾之間、家戶之間、村落之間、村落與政府之間的互惠關係,民間信仰習俗在鄉村治理體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承載鄉土文化習俗傳統的廟宇
在“文革”期間,民間信仰作為封建糟粕遭到了壓制和摒棄,“掃除一切牛鬼蛇神”,致使傳統民俗、建築等遭受了毀滅性的破壞。改革開放後,風氣開化,鄉村的民俗宗教活動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復甦,學界為此提出了“傳統的發明”“國家—社會關係”“宗教市場”三種解釋模式。筆者在調研中瞭解到,該地區的民間信仰活動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得到恢復,傳統民間習俗透過祭祀活動得到了傳承延續。但是,筆者在走訪中也發現,當前年輕一輩對民俗傳承、祭祀儀式等並無多大熱情,他們的離鄉離土使得該地區的鄉村民俗傳承面臨新的危機與挑戰。(社會科學報社融媒體“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見社會科學報及官方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