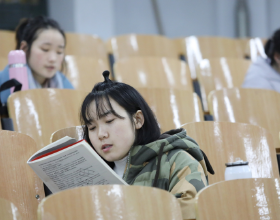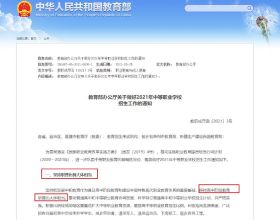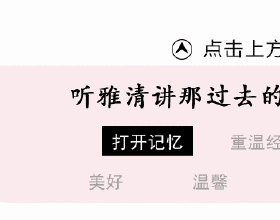20世紀初,諾貝爾獎得主Karl Landsteiner博士發現了人類的ABO血型。百年來科學積累發現,血型不僅與安全輸血相關,還能影響人體免疫和疾病感染[1]。但鮮為人知的是,ABO血型其實與人體微生物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2]。
去年1月,刊登在《自然·遺傳學》期刊的研究報道,人體ABO血型跟腸道微生物組成的關聯[3]。基於德國人群,科學家們發現ABO和FUT2基因的互相作用對腸道中的擬桿菌(Bacteroides)和糞桿菌(Faecalibacterium)的丰度有一定的影響。
然而這個發現僅限於德國人群,訊號沒有達到全域性(Study-wide)顯著性,也沒有被其他人群驗證。研究使用了16S rRNA基因擴增測序鑑定菌群,該技術對菌群的解析度有限,其鑑定表現不如更可靠的鳥槍法宏基因組測序。
今年2月3日,《自然·遺傳學》又背靠背發表了兩項基於大人群的宿主和腸道微生物的關聯研究,同時驗證了ABO和FUT2基因的互作對腸道微生物組成的影響。
第一個研究是基於約6000人的芬蘭佇列,由Michael Inouye領銜的墨爾本、劍橋、赫爾辛基以及聖地亞哥多個研究室組建的國際團隊完成[4],中國研究者覃友文博士是這個研究的獨立第一作者(目前就職於深圳華大基因)。
另一項研究是基於約7700人的荷蘭佇列,由Alexandra Zhernakova和Serena Sanna領銜的歐洲團隊完成[5]。
值得注意的是,兩項研究都使用了鳥槍法宏基因組測序鑑定菌群,並且都是在單一中心完成,降低了多中心之間的實驗和技術誤差,其精準度與之前提到的德國研究相比,有了很大的提升。
縱觀三項研究,我們不難發現,這些研究報道的關聯遺傳位點和微生物其實並不盡相同。
在德國人群的研究中,位於ABO基因座上的兩個獨立位點與糞桿菌(Faecalibacterium)和擬桿菌(Bacteroides)的丰度關聯。而在芬蘭人群中,ABO基因上的另外兩個位點與Faecalicatena lactaris和柯林斯氏菌(Collinsella)的丰度關聯。在荷蘭人群中,ABO基因上的位點又與Bifidobacterium、Collinsella、乳糖和半乳糖降解通路的丰度關聯。
雖然三個研究發現的關聯是體現在不同的遺傳位點和微生物物種,這些研究都一致揭示著ABO和FUT2基因之間的互作影響著菌群組成。
ABO基因控制的抗原是一種多糖物質,可以被特定細菌分解利用;ABO抗原在粘膜細胞的表達受FUT2基因控制[6]。基因型為FUT2 rs601338:AG/AA的人可以在粘膜細胞分泌ABO抗原,稱為“分泌型”。基因型為FUT2 rs601338:GG的人在粘膜細胞無可分泌ABO抗原,稱為“非分泌型”。
在“分泌型”人中,腸道粘膜可以分泌ABO抗原,從而促進某些細菌的生長。全球約有85%的人是FUT2分泌型,另外15%是非分泌型。這些發現推動了宿主與微生物互作的認識,為未來的精準干預腸道微生物提供新思路。
為什麼這些特定細菌能分解人源複雜多糖?由於細菌的代謝功能需要特定生物酶,而這些酶又受基因編碼調控。研究者聚焦於已有的細菌基因組,發現F. lactaris具有分解ABO抗原和黏膜多糖基因,並且體外培養實驗也觀察到該細菌能在豬粘膜為單一碳源的培養基中生長[4, 7]。這些證據充分支援了ABO抗原能作為細菌營養物質的推斷。
由於膳食纖維的攝入會影響粘膜降解細菌的丰度,其中包括與ABO基因關聯的柯林斯氏菌(Collinsella)[8],所以芬蘭和荷蘭人群的研究還分析了飲食對ABO基因與菌群關聯的影響。
與此前研究一致,在芬蘭人群中,柯林斯氏菌(Collinsella)以及其他粘膜降解細菌在腸道的丰度與膳食纖維攝入呈現負相關的關係。然而在A/B/AB“分泌型”人中,F. lactaris的丰度與膳食纖維攝入量不相關;在非A/B/AB“分泌型”人中,F. lactaris的丰度與膳食纖維攝入量成正相關。
在荷蘭人群中,研究者未發現膳食纖維攝入量對ABO基因與細菌關聯的影響。該研究中飲食資料的獲取比腸道菌群取樣時間早4年,代表性不足,可能是荷蘭人研究中未發現關聯的原因。

遺傳變異和膳食纖維攝入對腸道F. lactaris和Collinsella的影響。圖片來自參考文獻[4]
綜上所述,ABO和FUT2基因對腸道微生物的影響已經在德國、芬蘭和荷蘭人群中陸續被發現證實。這些規律是否能在其他人群中得到重現?此前,中國研究團隊基於約1500位中國年輕人,也揭示了ABO基因對腸道微生物的影響[9]。由於研究樣本量比歐洲人群少,關聯訊號較弱。隨著研究樣本量的加大,在中國和其他非歐洲人群的研究很可能會有更多的類似發現。
此外,這兩個研究也再次驗證了LCT位點與奶製品對雙歧桿菌(Bifidobacterium)的影響。芬蘭和荷蘭的大人群都是在多年前開始搭建,期待國內科學家也能構建類似的大規模研究。
參考文獻:
1.Bayne-Jones, S., DR. KARL LANDSTEINER NOBEL PRIZE LAUREATE IN MEDICINE, 1930. Science, 1931. 73(1901): p. 599-604.
2.Arnolds, K.L., C.G. Martin, and C.A. Lozupone, Blood type and the microbiome- untangling a complex relationship with lessons from pathogens. Current Opinion in Microbiology, 2020. 56: p. 59-66.
3.Rühlemann, M.C.,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n 8,956 German individuals identifies influence of ABO histo-blood groups on gut microbiome. Nature Genetics, 2021. 53(2): p. 147-155.
4.Qin, Y., et al., Combined effects of host genetics and diet on human gut microbiota and incident disease in a single population cohort. Nature Genetics, 2022.
5.Lopera-Maya, E.A., et al., Effect of host genetics on the gut microbiome in 7,738 participants of the Dutch Microbiome Project. Nature Genetics, 2022.
6.Wacklin, P., et al., Secretor genotype (FUT2 gene) i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the composition of Bifidobacteria in the human intestine. PloS one, 2011. 6(5).
7.Leitch, E.C., et al., Selective colonization of insoluble substrates by human faecal bacteria. Environ Microbiol, 2007. 9(3): p. 667-79.
8.Desai, M.S., et al., A Dietary Fiber-Deprived Gut Microbiota Degrades the Colonic Mucus Barrier and Enhances Pathogen Susceptibility. Cell, 2016. 167(5): p. 1339-1353.e21.
9.Liu, X., et al., Mendelian randomization analyses support caus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blood metabolites and the gut microbiome. Nature Genetics, 2022. 54(1): p. 5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