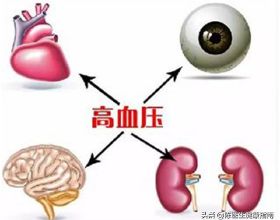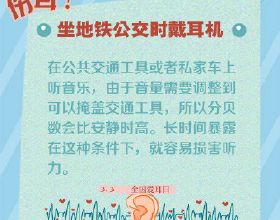拉馬克認為這個器官:(a)被使用;(b)因此得到了改進;(c)這個改進傳給了後代(P126 (奧)埃爾溫·薛定諤《生命是什麼?》)。
我覺得,拉馬克忽視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假如這個將要使用的器官還不存在,我們又該如何看待進化呢(單細胞生物是如何一步一步進化出器官結構的?這與受精卵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地最終發育成胎兒的——也是我想知道的——有著異曲之妙)?再者說,就算是有某些器官真的使用了,也可能只是功能的改變或重新組合,而未必就導致結構的改變。就如同“狼孩”一樣,雖說其身體的功能發生些改變,但是究其實質仍是屬於“人”種。因此,我們應該換個角度,不再囿於“器官的使用”的角度,而是從結構和功能角度,重新思考“進化論”。
一般來講,結構決定著功能,而功能也可反作用於結構。生物體與外部環境相互作用的最終結果就是結構的平衡和功能的平衡,也就是資訊的平衡。
行為的改變導致功能的變化,功能的變化又反作用於結構,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結構的變化,這就是行為改變的積極意義。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行為的變化,要求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結構,只有與之相適應的結構才會產生與之對應的功能能。如此迴圈往復,直至功能的平衡。因此,這裡又會產生新的問題,到底什麼樣的功能改變才會導致新的結構的出現?或者說,功能的變化是否就一定導致出現了新的結構。究其實質,就是一個結構平衡的問題,就如同我們日常看到的那個伸縮的彈簧在做著簡諧運動一樣,結構的平衡也有一個“度”的問題,一旦超出這個度,結構的平衡就會被打破,也就意味著新的結構的誕生。而決定著“度”的關鍵,還是一個能量大小和方向問題。如是正向,即主動性就可能會產生新的結構;如是負向,即被動性,則只會出現功能性的適應性改變。
至此,關於進化論的大致框架問題解決了,而剩下的就是一些具體的細節問題,如外界環境的變化是如何導致生物群體內出現新的變異的。
同時,也可看出一統論與達爾文進化論明顯不同的是,始終堅持平衡決定著物種的進化。而平衡恰是一統論的核心觀念。 2020年4月28日星期二 1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