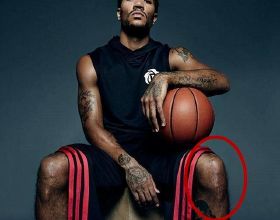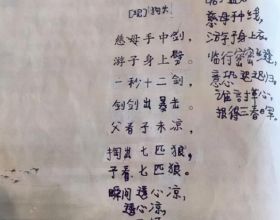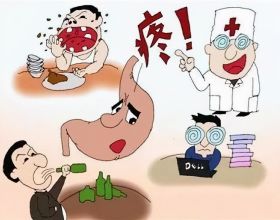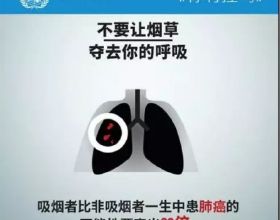1936年秋天,四川宣漢縣一個偏僻的山村,17歲的農家姑娘李德芳,秘密地和一個駐紮在當地的國民黨計程車兵邱大明談起了戀愛。邱大明1915年出生,當年21歲,來自四川榮昌縣。19歲參軍,隨部隊調遣到這裡。這一對年輕人因偶遇而相識相戀,經李德芳父母的同意,在第二年6月,邱大明做了上門女婿。
當時他們並沒有考慮到部隊會隨時離開,夫妻倆的生活並不能長久。基於這一點的原因,當時軍隊有個規定,不允許士兵和當地的姑娘交往。邱大明和李德芳都不在意這一點,就這樣偷偷地在一起了。不值班的時候,他就會到李德芳家中,夫妻團聚。
這樣幸福的日子是短暫的,5個月後的一天,邱大明所在的部隊接到緊急命令,連夜開拔奔赴四川萬源。服從命令,一秒鐘也不能耽擱,這是軍人的天職,軍隊的紀律,所以邱大明沒有任何時間去向妻子說明情況,就隨軍隊出發了。
後來邱大明的部隊被整編進楊森的部隊,開赴江西九江、湖北枝城一帶抗日。邱大明英勇殺敵,升為上尉排長。
有一天,戰鬥間隙,邱大明在一個鎮上買東西,看到一位老婆婆蹲在牆角哭。他上前詢問,原來是老人家拿著一塊銀元,準備來街上買點大米,卻被人認出來銀元是假的。邱大明拿過這枚銀元,把自己的真銀元遞給老婆婆,說:“拿我的真銀元去買米吧!”老婆婆千恩萬謝地走了。
邱大明把那枚假銀元揣進左胸的衣服口袋裡帶走了。在又一次的激烈戰鬥中,敵人一顆流彈擊中邱大明的左胸部,把邱大明打了一個重重的踉蹌。士兵們大喊:“排長中彈了!”滾到坡下的邱大明慢慢恢復了神智,他用手一摸,發現是那枚假銀元起到了作用,替他擋了一下日軍的子彈,神奇地救了他一命。
抗戰勝利後,邱大明從部隊退下來,在瀘縣當派出所所長,那時自己還年輕,又儀表堂堂,又娶了一位姓蒲的女學生,還生下來一個兒子。他解放初期,因種種原因,邱大明化名邱雲,裝扮成民工,參與了修建成渝鐵路和寶成鐵路。1954年,邱大明被送往新疆勞動改造,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生產建設兵團的農二師勞動。
1976,國民黨軍、警、憲、特及其公職人員全部釋放,邱大明在國民黨最後的軍銜是少校,相當於現在的營長。61歲的邱大明領到3000元安置費,從新疆回到重慶。政府聯絡到他的妻子和孩子的下落,在重慶江北區三洞橋,邱大明立即前往趕到重慶想與妻兒團聚。
22年過去了,生活也改變了,他的妻子已經改嫁了兩次,他沒有落腳的地方就和兒子住在了一起。由於一直沒有撫養過兒子,父子感情淡薄,後來兒子給父親騰出來一間小房子,讓他一個人居住,邱大明從此開始了更加孤獨的生活。
邱大明獨自生活了若干年後,他如何也想不到,他的原配妻子李德芳已經來到了三洞橋對面長江南岸,直線距離不到3000米。
當年,邱大明緊急出發,一走了之,再無音訊。留下5個月的新婚妻子,苦等痴盼,平常丈夫時不時地都會回家,這下一連數天未歸,她急忙去打聽,才知道部隊已經離開。真如五雷轟頂,讓她備受打擊。
李德芳對邱大明很痴情,不僅因為他長得一表人才,還因為邱大明體貼能幹,每次回家都很勤快,深得岳父母歡喜、但這次他就就這樣悄悄地走了,沒有留下一句話。
她毫無希望地等,這中間十幾年,父母親人都勸她別等了,邱大明可能早就犧牲了。一直等到新中國成立後,她的丈夫還沒有回來找她,既然他不來,那她就去外面找一找。
1954年,已經35歲的李德芳還是孤身一人。她隻身來到重慶,她想,當年邱大明就是在重慶參軍的,現在抗戰勝利了,邱大明會不會在這裡呢?
初到重慶的李德芳為了生存,幹過很多苦力,幫別人做衣服、做花、帶孩子。她處處留心,也沒有打聽到關於邱大明的任何訊息。後來“三反”“五反”運動,李德芳怕自己國民黨家屬的身份暴露,化名為劉澤華,經人介紹,與一個政治可靠的涪陵來重慶打工的廚師況明結婚了。
有了家,李德芳算是在重慶安頓下來,最初,她和丈夫租住在一處民房,在街頭搭個棚賣粥,維持生活。
再後來他們夫妻倆在百貨公司賣起了百貨,做了10多年的生意有了一定的積蓄,就在兩路口靜園18號買了一套40多平米的房子,結束了十幾年的租房生活。夫妻倆沒有生育,就收養了兩個孩子,孩子長大後,劉澤華夫婦又在南坪買了另一套房子,搬到南坪去了。
在南坪的生活是平靜安穩的,1992年,劉澤華的丈夫況明去世,她與養子之間因為房屋的問題產生矛盾。有一天,她帶著僅有的身家,離開了南坪。
或許是命運的有意安排,老人家漂泊到了江北城,漂流到了三洞橋附近。70多歲的劉澤華偶然認識了一箇中年女子,老人家把自己的遭遇都說了,那女子把劉澤華帶回家,認作乾孃,讓老人住下。
劉澤華經常把自己的積蓄拿出來,買米買菜,補貼一家人吃喝。就這麼幾年過去了,日子長了,劉澤華身上沒有多少錢了,她心想,幹閨女哪有閒錢養活她這撿來的老婆子啊!
1997年,已經78歲的劉澤華感到孤獨無依,她自己需要找個伴,有一處可以安身立命的家。自己這一輩子太坎坷了,到老了,不想再漂泊不定了。
或許是命運的垂憐與眷顧,鄰居有一個熱心的婦女名叫李蠟芝,她給老人家介紹了一個老漢,老漢名字叫邱雲,今年82歲了,身體還算硬朗,有一間乾淨簡陋的住處。李蠟芝叫老人家等著她的訊息,她去打聽一下那位老漢願不願意找個老伴。
劉澤華老太太滿心期盼地等了好幾天,那個老漢也沒有露面,她主動上門到李蠟芝家,提出讓老漢過來見見。
左等右等,李蠟芝把老漢帶過來了,那天,老漢帶著一頂帽子,低著頭半天才說:“我沒錢,吃低保,養不起你。”“我不要你養,我還有點積蓄,我只要一個落腳的地方。”
那老漢又半天不開腔,這次見面顯然沒有結果。又過了半月有餘,一天半晌,劉澤華老太太遇見了帶著帽子的邱雲老漢,他好像是專門等她的,坐在不遠的角落裡,正朝她這邊望著。
老太太走過去打聲招呼,邱大明說:“到我家去吃個便飯吧!”
到了他家,一看:一張木板床,一張支起來的桌子,一臺電視機,就是全部家當。老漢說的便飯,是一盤青椒皮蛋,一盤迴鍋肉。透過一頓簡單的午飯,兩位老人走近了。幾次來往之後,劉澤華老太太主動提出搬過來,她說:“我一個人,沒有兒女過日子,好孤單,你如果同意了,我就去置辦東西。”邱雲老漢已經不反對了。
命運弄人,這算是他們的三婚了。1997年11月間,選了一天正式的好日子,劉澤華老太太添置了一些碗筷和日常用品,他們把相識的人和左鄰右舍請過來,發了一些喜糖,就算是舉行簡樸的婚禮了。
等客人都走光了,兩位老人開始拉起了家常,劉澤華老太太提出辦一個結婚證,像模像樣地過日子。“就想有個安穩的家,好好過日子,死了也好瞑目啊!”
邱雲老漢點頭同意,這時,他們才想起來,互相交個底。
邱雲老漢:“你原來是什麼地方的人?”劉澤華老太太:“宣漢縣,塔河壩,爐子山。”
邱雲老漢心頭一緊:“怎麼會呢?那裡的人都姓李,你怎麼姓劉?”
劉澤華老太太:“我以前就姓李,來重慶才改姓劉。”邱雲老漢連忙問:“那你以前叫什麼名字啊?”
劉澤華老太太:“李德芳。”邱雲老漢驚得目瞪口呆:“你母親是不是姓餘?”
劉澤華老太太:“是啊!你怎麼知道的?”老漢哭了起來:“我是你丈夫啊!我是邱大明!我北上抗日,走得太急了,撇下你,沒辦法和你聯絡啊!”
劉澤華老太太望著他,感覺像做夢一樣恍惚:“邱大明,真的是你嗎?是你嗎?你還活著!變了好多!我認不出來啊!”
是啊!她心中的丈夫還保留在60年前他22歲時的模樣,面前這個久經風霜的82歲的老漢,如何能與當年的邱大明聯絡到一起呢?而她自己,原先那個18歲的小姑娘,也早已換了面貌。那一對年輕恩愛的夫妻早已讓歲月的風輪悄然拖拽到時光的深處,近在咫尺的耄耋老人,相顧不相識。
老太太抱著他,放聲大哭:“這麼多年了,你怎麼不找我啊!”“等打完仗,我想去你家,可是又想那麼多年過去了,你也許早就嫁人了……。”
“我一直等了你十幾年,我一直在想著你啊……。”“我這一輩子對不住你,耽誤了你的青春和幸福……。”
淚眼婆娑,欲哭還笑,1937——1997,60載,太多偶然的因素讓這對相識在戰火中的新婚夫妻在垂垂老矣的暮年重逢再婚。這樣的人生際遇也只有電影鏡頭裡才會出現的吧!
半夜,她常常從夢中醒來,她生怕邱大明先離她而去了,“我又何嘗不怕呢?孤苦無依這麼多年,我們離別了60年,多想在一起多些日子,彌補以前的時光。”邱大明說。
每天早上7點,邱大明準時起床,為老伴準備早餐。有時煮湯圓,有時候會是稀飯或者麵條。邱大明每個月低保130元,慢慢漲到210元,加上老太太年輕時的積蓄,日子就這樣支撐著簡簡單單地過。
後來江北城拆遷,老兩口所在的三洞橋也在拆遷範圍,他們就搬到了李德芳原先在南坪的房子居住。那是一棟獨立的小房子,面積不過50平方米,低矮,卻洋溢著溫馨。
“只要李老太要求,他們家邱老伯總是百依百順。”隔壁鄰居說。老兩口分外珍惜重逢的每一天,結合10多年,從來沒有吵過嘴。邱大明說:“他做夢都沒想到他倆還能重逢,他欠老伴的太多,今後不讓她吃苦,就想好好陪著她。”
邱大明身體更硬朗一些,吃完午飯,邱大明攙扶著李德芳,在家門口前的空地上來來回回慢慢地踱步……。大約半個小時的光景,邱大明又把李德芳攙扶到躺椅上曬太陽,他自己收拾一下碗筷,然後刷碗洗鍋。
老兩口的生活十分規律,買菜煮飯,洗衣做家務由90多歲的邱老伯一個人包攬,閒暇的時間,他們就散步、打牌、讀報和看電視。
2008年,李德芳生病之後,便臥床不起,10月29日凌晨離開人世。1997年——2008年,他們又延續了12年的夫妻前緣。邱大明說:“她拉著我的手,她的手貼在我的手心裡,輕輕地握了一下,她就走了。”邱大明撫摸著妻子的照片,眼眶又紅了起來。
僅僅20天后,邱大明,這位老川軍,也走完了坎坷的人生路,追隨他的老伴而去。
新婚5月,天各一方60載,顛沛流離一生,好在最後還能攜手走完餘生12年,兩位老人離世後,葬在了一起,真真正正的永遠在一起了,沒有比這更圓滿的結局了。
感謝你看完全文。
文字由作者主觀思想+歷史客觀事實梳理撰寫。
讀歷史生智慧,讀歷史長學問,讀歷史明事理。關注@文乎
更多文章請點選下方藍色標題檢視
一輩子沒見到丈夫,守著婆家領養兒女,李鳳蘭是沂蒙最痴情的新娘
追憶肝膽外科之父吳孟超與妻子吳佩煜:同窗相戀,生三女皆有成就
共和國第一軍嫂:高壽115歲,苦等丈夫75載,至死堅信他還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