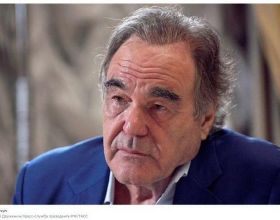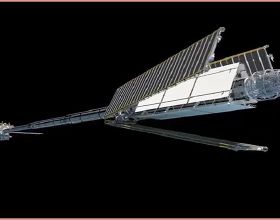1987年,汪曾祺已經出名許久了,應作家聶華苓之邀,他參加一個國際寫作活動,他帶著自己畫的海棠送給聶華苓,上面還畫了一隻蟲,上題一句:
解得夕陽無限好,不須惆悵近黃昏。
汪曾祺給大家做了一桌子菜,大家吃得高高興興,他給妻子施松卿寫信:
“不知道為什麼,女人都喜歡我,真是怪事。
昨天董鼎山、曹又方還有《中報》的一個記者來吃飯。
我給他們做了滷雞蛋、拌芹菜、白菜丸子湯、水煮牛肉,水煮牛肉吃得他們讚不絕口,曹又方抱了我一下。 ”
聶華苓原本叫汪曾祺‘汪老’,到後面就直接叫‘汪大哥’。
若覺人間不好玩,不妨讀讀汪曾祺。
01
賈平凹說:“汪是一文狐,修煉成老精。”
梁文道說:“像一碗白粥,熬得更好。”
沈從文說:“最可愛的還是態度,‘寵辱不驚’!”
汪曾祺自己說:“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於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潤,讓人覺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詩意的。”
汪曾祺一生活得熱鬧,他生的時候,也很熱鬧,那天是元宵節,家家戶戶都在鬧元宵,他就在別人鬧元宵的時候來到世間。
汪家是一個大家族,房屋、傢俱、習慣,都是老的。
祖父是清朝末科“拔貢”,愛喝小酒,下酒菜是半個鹹鴨蛋,喝完酒,就在屋裡大聲誦讀唐詩:“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
小汪曾祺,就在祖父酒後吟誦的詩篇中長大。
他也教汪曾祺讀《論語》等書,教汪曾祺寫字,有時候祖父也會給汪曾祺一杯茶,是西湖龍井。
父親也是金石書畫樣樣精通,每逢春秋佳日,天氣晴和,他就開啟畫室作畫。
汪曾祺喜歡看父親作畫,但見父親對著宣紙端詳半天,然後用筆桿或大拇指在紙上劃幾道,才開始畫,畫完了再看看,最後題字蓋章,掛在牆上,又反反覆覆仔細看。
三歲的時候,母親去世,汪曾祺就和父親一起睡。
有一次,汪曾祺脖子腫了,父親一看,原來長了‘對口’(又叫砍頭瘡),父親趕緊帶著他去看郎中。
郎中看了看,麻利地找出一包手術刀,連麻藥都不打就準備割,父親見狀,趕緊往汪曾祺嘴裡塞一顆蜜棗。
只聽‘呼’的一聲,‘對口’就已經割開了,嘴裡的蜜棗吃完,又塞一顆,然後就回家了。
世間有趣的人不多,有趣的事也不多,一個人,要經歷過很多很多,才能變得有趣。
汪曾祺比較幸運,他的家人是有趣的,並沒有將他教成無趣的人,沒有將他教成醉心功名利祿的人。
02
上小學的時候,汪曾祺去上學,要經過一條大街,放學回家時,他就在大街上東看看,西看看,店鋪、手工作坊、布店、醬園、雜貨店、爆竹店、燒餅店。
他也認認真真地看銀匠做出一個小羅漢,到竹器廠看師傅怎麼樣將一根柱子做成耙子,到車匠店看人家用硬木頭做出各種形狀的器物,,看燈籠鋪做燈籠。
總之,有啥看啥,看啥都津津有味,百看不厭。
等到稍大一點,汪曾祺就學會了喝酒抽菸,他就和父親對坐飲酒,一起抽菸。
十七歲那年,汪曾祺在家裡寫情書,父親就在一旁給他出主意,兩人不像父子,倒像是兄弟。
父親對他說:“我們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1937年暑假後,汪曾祺輾轉借讀,每到星期天,上午就開始上街買東西,吃一碗脆鱔面或辣油麵,或者吃一點豬油青韭餡餅。
麵條細若銀絲,湯也很好。
多年後,汪曾祺還說,江陰的面,是做得最好的。
吃完後,再到書攤上買一點打折促銷的書,然後回學校。
到了下午,就躺在床上吃粉鹽豆,喝白開水。
至於學習?三角函式、化學分子式,都放在一邊,汪曾祺說“考試、分數,於我何有哉?”
03
高中過後,汪曾祺最想考美專,其次是文學。
可是考哪個大學呢?
他聽說西南聯大學風自由,學生上課考試都很隨便。
總而言之,可以自由發揮,不被課程束縛,於是就選擇了西南聯大。
後來他說:
“大部分同學是來尋找真理,尋找智慧的。”
“我尋找什麼?”
“尋找瀟灑。”
當時由於戰亂,西南聯大考試要到昆明,汪曾祺到了昆明,還沒考試,就得了一場嚴重的瘧疾,不得不住進了醫院。
那一次高燒超過40℃,護士給他打強心針。
一看很嚴重,他問:“要不要寫遺書?”
護士嫣然一笑:“怕你燒得太厲害,人受不住!”
後來檢查結果出來,主要問題是惡性瘧疾,護士拿來注射劑。
他又問:“是什麼針?”
護士答:“606”
聽見護士這麼一說,他趕緊回道:“我生的不是梅毒,我從來沒有·····”
護士又一笑,還是給他打了606.
“606”勝利了,瘧疾漸漸好了,可是他又想趕緊出院,醫院實在太難熬了。
為啥呢?
因為醫院規定他不能吃飯,只能吃藕粉和蛋花湯,這讓吃貨汪曾祺怎麼受得了,請求出院,醫生不準,他急了。
“我到昆明是來考大學的,明天就是考期,不讓我出院,那怎麼行!”
考試那天,汪曾祺喝了一碗蛋花湯,晃晃悠悠走進考場,考英語的時候,有一道題目是中文翻英語,中文是一段日記:“我刷了牙,颳了臉……”
最終,汪曾祺這個“學渣”不知“刮臉”怎麼翻譯,就翻譯成“把鬍子弄掉”!
考完了試,一點把握也沒有。
卻也不管,仍舊該怎麼玩就怎麼玩,該怎麼吃就怎麼吃。
04
發榜的時候,汪曾祺也忐忑著,可是一看,自己居然榜上有名。
他考上了西南聯大中文系。
他選了沈從文的課。
沈從文講課,說話聲音小,還一口湘西口音,沒有講義,想到哪裡講哪裡,經常講一句話:
要貼到人物來寫。
那時候的西南聯大,教學環境差,教授的穿著也破破爛爛的,除了學識和文化,除了學術自由,什麼也沒有。
教授聞一多穿一件早就過時了的夾袍,領子很高,袖子很窄;
朱自清的大衣破得不能再穿,就買了一件雲南趕馬人穿的衣服披在身上,遠看有點像一個俠客;
曾昭掄穿著一雙空“前”絕“後”的鞋,腳趾頭露在外面,鞋後跟爛了提不起來,只能半趿著。
汪曾祺在這裡,日子過得也真的很瀟灑自由,他在西南聯大愛三樣東西,一是美食,二是美酒,三是好書。
抽菸喝酒,搞得他牙口不好。
牙痛的時候,他就幸災樂禍地想:我倒看你疼出一朵什麼花來!甚至有時候牙痛到腮幫子腫得老高,他還能和別人談笑。
當時昆明有一修女,是牙醫,汪曾祺攢了一些錢,想去拔牙,可是到了教堂門上寫著:修女因事離開昆明,休診半個月。
牙拔不成了,汪曾祺反而很高興。
拿著那筆拔牙的錢去館子裡,要了一盤冷拼,四兩酒,美美地吃了一頓。
有錢了就去吃,就去喝,沒錢了就幫同學寫文章賺點小費,然後繼續吃。
他幫別人寫的文章,聞一多看了,對那同學說:“你的報告寫得很好,比汪曾祺寫的還好!”
這話傳到汪曾祺的耳朵裡,他偷偷的樂著。
05
汪曾祺喜歡讀書,有一個時期特別喜歡諾獎作家紀德。
他成天夾著一本紀德的書,坐在茶館裡,一邊喝一邊讀,優哉遊哉的。
他也讀薩特的書,雖然當時雲裡霧裡,但終究還是受了影響。
讀大學時,汪曾祺有一個室友,兩人同睡一張木床,汪琪曾上鋪,室友下鋪。
室友是一個很規矩,很用功的人,準時準點睡覺。
汪曾祺卻是夜貓子,每天在圖書館裡看一晚上書,天亮了才回到宿舍,等到回到宿舍的時候,室友已經在樹下苦讀英文了。
半夜的時候,汪曾祺就拿起毛筆,開始記錄一些印象。
他不停地抽菸,有時候煙沒有了,就在地上撿一個長一點的菸蒂,點燃繼續抽。
有時候沒錢吃飯,他就臥床不起,同學見他十一點還不起床,就夾了一本字典來叫他:“起來,去吃飯。”
兩人將字典賣了,吃了飯,就躺在地上看天上的雲,說一些虛無縹緲的胡話。
有一回聞一多看到汪曾祺精神頹廢,還痛批了汪曾祺一頓。
在西南聯大,他逃課、泡茶館,學習一塌糊塗,尤其是英語,大二考試還是0分,數學、體育也上不得檯面。
他是當之無愧的學渣。
學科裡唯有一樣,他特別拿手,那就是國文課,因此聞一多、沈從文都特別喜歡這個小夥子,作文滿分100分,沈從文給了他120分。
尤其是沈從文,對汪曾祺更加愛護有加。
他陪著沈從文一起逛寄賣行,舊貨攤,買耿馬漆盒,買火腿月餅。餓了,就到沈從文宿舍對面的小鋪吃一碗加一個雞蛋的米線。
有一回,汪曾祺喝得爛醉,坐在路邊。
沈從文以為是生病的難民,上前一看,居然是汪曾祺,不得不和幾個同學把汪曾祺扶回去,灌了好些釅茶,汪曾祺才清醒過來。
有些人有趣,生活就過得多姿多彩。
有些人沒趣,就抱怨生活無聊。
06
汪曾祺瀟灑,是真的瀟灑。
似乎不管什麼樣的生活,他都總能“玩”,別人覺得好的,他在玩,別人覺得苦,我也在“玩”。
在西南聯大的時候,日軍轟炸機時常掃蕩,所有人都要“跑警報”,人家都往山裡跑,因為山裡隱蔽,還有防空洞,但他卻攥著一塊點心往松林裡跑。
別人喊他跑反了,他邊跑邊喊:“沒反,松林裡有松子吃,炸死總比餓死強。”
一個人“玩”到極致,就超越了苦中作樂,而是真正的灑脫。
但汪曾祺也吃過這份“瀟灑”帶來的苦楚。
在西南聯大時,汪曾祺由於違反了西南聯大的某些規定,最終連畢業證也沒有拿到。
1946年,西南聯大的老師同學們紛紛北歸,汪曾祺回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的汪曾祺,舉目無親,工作無著落,每天飽受牙疼的折磨,他甚至想到自殺。
老師沈從文得知後,寫了一封長信,將他大罵一通,“你手中有一支筆,怕什麼?”
他整天無所事事地逛皇后道、德輔道,活在在走廊上去看水手、小尚任、廚師打麻將。
那是一段無聊的日子。
後來,他在陽臺上堆著的一堆煤塊裡,看到了一棵芋頭:
“沒有土壤。更沒有肥料,僅僅靠一點雨水,它,長出了幾片碧綠肥厚的大葉子,在微風裡高高興興地搖曳著。”
他看到了生活的勇氣。
找到生活勇氣的汪曾祺,和黃永玉、黃裳一起泡咖啡館,談論文學藝術,組成”上海灘三傑“。
他們一起到巴金蕭珊夫婦家喝茶,看蕭珊表演功夫茶。
喝茶,玩,寫作,到地攤書店裡看書。
1949年,第一本短篇小說集《邂逅集》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07
楊麗萍說:
“有些人的生命是為了傳宗接代,
有些是享受,
有些是體驗,
有些是旁觀。
我是生命的旁觀者,
我來到世上,
就是看一棵樹怎麼生長,
河水怎麼流,
白雲怎麼飄,
甘露怎麼凝結。”
汪曾祺這個人,他是生命的旁觀者,但又熱烈地投入到生活中去。
他快快樂樂地玩,高高興興地吃,隨遇而安地活。
“反右”運動時,汪曾祺被打成“右派分子”,發到張家口西山種樹。
走的那天,他給妻子留下一張紙條:“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就回來。”
種樹的時候,他要在石多土少的山頭用鋤頭刨坑,很累很苦,每天又是隻吃兩個幹饅頭,一個大醃蘿蔔。
時間長了,覺得難以下嚥。
怎麼辦?
山上的酸棗熟了,摘酸棗吃。
草裡有蟈蟈,就燒蟈蟈。
“蟈蟈要吃三尾的,腹大,多子,一會兒就能抓半筐,點一把火,把蟈蟈往火裡一倒,劈劈剝剝,熟了,咬一口大醃蘿蔔,嚼半個燒蟈蟈,就著饅頭吃,香啊”
那時候,汪曾祺已經年近40了,每天干的都是重活髒活。
“扛170多斤重的麻袋,在木板上折返,木板一顫,身子也跟著顫動。”
日子很苦,但他並不抱怨,而是想方設法尋找歡樂。
他被分配去掏廁所,張家口的冬天太冷,把公廁裡的屎尿都凍成了大冰坨子,他得把它們掏出來,搬到一塊兒。
妻子問他:“髒不髒啊,臭不臭啊?”
他笑起來,手舞足蹈地做了一個甩手的動作,沒事,冰碴子落在我身上,抖抖就掉了!
他說:“我們有過各種創傷,但我們今天應該快活”。
無論日子怎麼樣,快樂總沒有錯。
08
“右派分子”的帽子摘掉後,一時之間,汪曾祺不知道該去幹什麼,他就申請留在農業科學研究所打雜。
研究所要畫一套馬鈴薯圖譜,把這個任務就給了他。
汪曾祺就帶著幾本書,開始奔赴工作地點,白天畫圖譜,晚上燈下讀書。
他畫各個種類的馬鈴薯,馬鈴薯開花,他就畫花和葉子;等馬鈴薯逐漸成熟,他就畫薯塊。畫完一種薯塊,他就把它放進牛糞火裡烤,然後吃掉。
對此,他頗為洋洋自得。
因為像他這樣吃過那麼多品種的馬鈴薯的,全國沒有第二個。
“人不管走到哪一步,總得找點樂子,想一點辦法,老是愁眉苦臉的,幹嘛呢? ”
能夠不苦的人生,都是上天眷顧的人生,但是能夠苦中作樂的人生,都是自己經營出來的。
關於那些苦難的日子,有人曾問他:“這麼些年你是怎麼過來的?”
他回答:“隨遇而安。”
隨遇而安,不是隨波逐流,不是自暴自棄,而是安於當下,享受當下。
09
1980年,北京玉淵潭公園飛來幾隻天鵝,汪曾祺每天都會去看看。
一天夜裡,兩個青年將天鵝打死了,要吃它們的肉。
汪曾祺很氣憤,也很悲憫,回家之後連夜寫下了一篇小說《天鵝之死》。
他說:“我們青年的生活應該更充實,更優美,更高尚”
他的兒子汪朗說:“他寫這篇小說,並不只是嘆惋一隻天鵝的命運,而是對許多人失去愛美之心而感到深深的悲哀。”
這一年,汪曾祺已經60歲了。
就在他60歲這年,他開始火了起來,越來越多的人知道這個“玩世不恭”又很愛吃的溫暖的老頭。
晚年的汪曾祺,兒孫繞膝。
他的夫人叫他老頭兒,他的三個兒女也叫他老頭兒,就連他的孫女,也叫他老頭兒。
他在家裡有了一個別號:“老頭兒”。
不僅如此,兩個孫女還會給他“上課”。
有一次,他們一家人聊到汪曾祺的作品,大家都挑好的說,但孫女氣哼哼地說:“爺爺寫的東西一點也不好。沒詞兒。”
外孫女也在一邊說:“就是嘛。另外中心思想一點也不突出,扯著扯著就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按我們老師的評分標準,最多算個二類文。”
他聽後,哈哈大笑,嘴裡還一再重複著:“沒詞兒,沒詞兒,說得好,說得好!”
他喜歡畫畫,可是他的孫女覺得他畫的鳥太醜,因為他畫的鳥“瞪著眼睛,梗著脖子”。
於是,兩個孩子就送了他一件禮物:
一個小小的鳥窩模型,窩裡有幾隻小蛋,窩邊上立著一隻小鳥。
她們很認真地說:“爺爺,你畫的鳥太醜了,老是瞪著大眼睛,脖子還梗著。以後照著這個鳥好好畫啊。”
老頭兒笑呵呵地把鳥窩放進了自己的書櫃,一直留著。不過,他畫的鳥還是瞪著眼睛,梗著脖子。
還有一次,他畫了一幅荷花,兩個孩子看了說:“荷花應該是長在水裡的啊,怎麼看不出來呢?咱們給他添上吧”
於是兩個人便在畫的下面添上了幾道水紋。
添完之後看了看,又說:“右邊怎麼空了那麼多地方啊,添上兩朵花吧,於是又畫上了兩朵荷花”。
一幅畫,變成了祖孫三人的共同作品。
汪曾祺在一邊,也不反對,甚至覺得有趣。
年歲越大,他似乎越懂得生活的樂趣。
10
今天看汪曾祺的作品,很多都是美食相關的。
比如寫鹹鴨蛋,他說:“曾經滄海難為水,他鄉鹹鴨蛋,我實在瞧不上。”
比如他寫西瓜:“西瓜以繩絡懸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聲,涼氣四溢,連眼睛都是涼的。”
瞧,他就是這樣的人,他不僅寫,而且喜歡自己做美食。
四方食事,不過一碗人間煙火。
到了一個新地方,有人愛逛百貨公司,有人愛逛書店,我寧可去逛逛菜市場。看看生雞活鴨、新鮮水靈的瓜菜、彤紅的辣椒,熱熱鬧鬧,挨挨擠擠,讓人感到一種生之樂趣。
他說自己最大的樂趣,就是看家人和朋友吃他做的飯菜盤盤光。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離世。
去世前,他對女兒說:“給我來一杯碧綠!透亮!的龍井!”
可是,茶還沒上來,他便與世長辭。
他雖然走了,但卻越來越多的人記得他,從他的書裡得到溫暖。
11
生活,對於大家來說,都是吃喝拉撒睡等幾件事。
但每個人對生活的態度,就決定了生活不同的樣子,抱怨生活的人,總是因為一點點不順心就失去擁有的快樂。
快樂生活的人,總是因為一點點好事,就重新快樂起來。
有些人看不到生活的樂趣,就覺得生活是無趣的,哪怕他又很多快樂的機會,他也看不到。
有些人去創造生活的樂趣,哪怕日子苦兮兮的,他也能從中看到好玩的地方。
沒有人能一直幸運,只有一直努力幸運的人。
那些活著是最幸福快樂的人,不一定是生活得最幸運的人,但一定是最會玩的人。
文|不有趣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