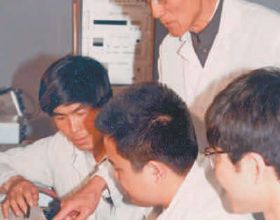今天重新回顧多年前的祈福行程,我們走了一萬千八千多里,我在行走中,徹底康復了下半身骨頭,途中規定:食素,不坐纜車,遇山爬山,遇水涉水。全程走下來的,不坐纜車全程爬山的,只有俞總、我和陳運松先生三人。
一路行走,一路疑惑,我是誰?我們是誰?
當時對於選擇祈福的寺廟,除了一定要去傳統的四大名寺外,覺得還一定要去南京毗盧寺,這是直覺告訴我的。
因事先無法與各寺院的主持們進行溝通,他們不會接手機,而接手機的師傅還要看有無機緣了。
其實江蘇省境內還有一個更有名的寺廟,當時我向主持發出請求後,想了想,覺得還是改去毗盧寺為好。
去毗盧寺的那天,天下起了秋雨,一路淅淅瀝瀝,攝像師小唐埋怨大雨會把機器淋壞。我們都相信,這雨是為著我們下的。就像去五臺山東臺一樣,下了一個月雨的東臺望海寺,恰好在我們到的那一天放晴了,我們幸運地看見被稱為華東第一景的“望海日出”。
毗盧寺很安靜,正在修整,還不對外開放,淨藍法師已經帶領眾僧人做好了準備。
一場在風雨中進行的祈福活動開始了。
上百次去南京,但是,有兩個地方我一直沒有去,一個地方是總統府,另一個地方是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沒有去總統府,是覺得對那裡很熟悉,陳丹青的成名作《攻克總統府》,我拍得很仔細,還有用過很多關於那裡的紀錄片,陳設、走廊,都在畫面中不時相遇,那裡對我沒有新鮮感。
而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是我想去而一直不敢去的地方,不是膽小不敢去。
記得在大學讀書時,幾乎所有的業餘時間,都在看與日本近代史有關的書,日本防衛廳編的書,美國作者的《菊與劍》,《決戰Z字旗》,還有更多的,那個時代日本人寫的書。
一名參加日俄戰爭的日本士兵寫過一本書叫《肉彈》,描寫了日本士兵在中國的土地上,與俄軍決一死戰,決定了日本取代俄國在中國地位的一段歷史的日俄戰爭,只知道書名,後來發現我就讀的學校,是惟一可能有這本書的地方,於是向學校圖書館借書。
開完書單後,過了很長時間,書庫裡走出一位中年的老師,他對我說,給他一些時間,他一定會幫助我找到這本書。
是啊,這是一本1936年印的書,沒有再版過,學校圖書館是全國大學中最大的一座,有不少於二百萬冊的藏書,要在短時間內找到這樣一本書,是需要些時間。
幾天後,我接到了通知,我的書,找到了。
取書的那一天,有幾位老師在等著我,他們極其鄭重地將書交到我手中,並告訴我,只有這一本了,一定要儲存好。
我開啟書,書籤上寫著,1936年燕京大學圖書館的字樣。
沒有人讀過,所以,書很新,沒有摺痕。
無法想象作者櫻井忠溫所記載的一切,就像很多年後,我讀到《東史郎日記》中,最讓我受刺激的,並不是對屠殺中國人的記載,而是他對國民性的判斷,
原文如下:
“他們(指中國人)具有這樣的性格:或者諂媚取寵,或者失聲痛哭,或者色厲內荏,他們要麼裝成一副從內心完全信賴你的樣子來拍你的馬屁,要麼採取特殊的卑躬屈膝的態度,像女人那樣老於世故地耍花招,這是支那人的國民性。
痛苦流涕地揪住你的袖子來求你,抬高你的自尊,這種幫閒似的性格也是他們的國民性。和他們交往使人感到就像和幫閒者們打交道一樣。他們敏銳地觀察地方內心的微妙變化,早早地抓住對方的心理,然後去順應他,他們就像會變的貓眼一樣,顯示出於變化萬化的性格。這樣的人大都卑躬屈膝,喪失骨氣;他們喜歡造謠中傷,姑息遷就而不能堅持已見,這樣的人最終也不能領導別人。”
這是東史郎對國民下的定義。
所以在他們的眼中,中國人的命不如一頭豬,這是當時幾乎每個日本士兵對中國人的看法,從1905年櫻井忠溫的日記到1937年的東史郎日記。
詩人田間同樣在80年前,這樣告誡我們:
假使我們不去打仗,敵人用刺刀殺死了我們,
還要用手指著我們骨頭說:
“看,這是奴隸!”
我們還是記住那些我們陌生的名字:
羅瑾:南京長江照相館店的學員。有一天,他發現來沖洗的照片,全是侵華日軍在南京大屠殺和強姦婦女的畫面時,十分憤怒,悄悄地衝洗了兩套,自己留了一套,用一本黑色相簿保管。之後,羅瑾被招募到汪偽政府交通通訊集訓隊,這個集訓隊住在離現在的“總統府”不足千米的毗盧寺。
為不被他人發現,羅瑾冒著生命危險把16張照片的冊子藏在毗盧寺廁所牆洞裡,之後,相簿又被集訓隊隊員吳旋保管,直到抗戰勝利。照片被送到當時的南京臨時參議會,成為法庭中證明南京大屠殺的最有利的證明。
我終於找到來毗盧寺的理由:
正是這裡,儲存下來了一個民族悲情的記憶,一個讓侵略者得到應有的報應的地方。
淨藍法師用楊柳枝反覆灑著淨水,唱吟佛經。滿懷悲天憫人的佛號一聲聲飄揚在秋雨中。
雨一直下著,風默默地陪伴著,那些在風中逝去的名字,我們陌生的名字,在佛號聲中,有沒有得到些許的安慰?
(夢想的天花板之二十四 毗盧寺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