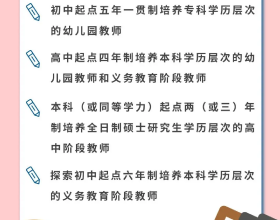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的頂峰--宋朝
中國歷史到了宋代,因為科舉制的普及,由半貴族社會變成了平民社會。這一演變,令皇權終於擺脫了地方世家大族勢力的威脅,真正做到了獨尊。在宋代以前,高門大戶往往能傳遞幾百年,其勢能嚴重影響皇權的執行。宋代卻實現了“富不過三代”,因為科舉制導致社會流動性劇增,“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由底層爬上去容易,而從頂層掉落到底層則更容易,因為權力及身而止,再加上中國的諸子均分制,富家大族的傳遞因此變得極為困難,“貧富無定勢”“富兒更替做”。因此“朝廷無世臣”“無百年之家”。世家大族的命運終結了,地方上不再有可與政府相抗衡的龐大家族。
因此,君主獨裁統治正式開始。不再有貴族和皇帝相抗衡,趙匡胤才有可能隨心所欲地對傳統政治制度進行大幅度修改,杯酒釋兵權,讓中國由尚武變成崇文,此外,還運用“分權”和“制衡”之術,把宰相大權分割成了幾塊,將地方權力一分為四,相互制衡。由此皇帝獨攬軍、政、財一切大權,君權達到空前穩定。
應該說,君權的穩定,不只是皇帝一個人的願望,也是秦制下大部分社會成員的願望。因為從唐代藩鎮割據到五代十國,政權的不穩定造成的混亂,給社會各階層都帶來巨大的痛苦。趙匡胤的集權進行得非常順利,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全社會對五代紛亂政治的痛苦反思。北宋因此取得了中唐之後難得的政治穩定,160多年中不但不再有貴族與之相抗衡,也不再有權臣、外戚、宦官的威脅。
更為重要的是,科舉制徹底解決了地方分裂勢力的問題。科舉制普及之後,流官才徹底“流”了起來,不再像以前那樣受世家大族的掣肘,文官主持下的州縣也不會像以前武將控制的地方那樣演變成威脅中央的力量。從宋代之後,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中,中央徹底佔了上風,宋、元、明、清四朝從未出現地方挑戰中央成功的事例。
但是宋代的集權與後世不同的一點,也是宋代政治最引人注目的一點,是在君權強化的同時,文臣對君權的制衡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姚大力先生認為,唐宋兩朝皇帝制度中,存在著“專制君權持續強化”和“限制君權的制衡程式同樣在增強”兩種趨勢,彼此構成一種“張力”,保證了宋代政治文明向前發展。
宋代政治繼承了唐代“封駁制度”和“諫官制度”的成就,同時,科舉取士的普及,讓儒家“從道不從君”的傳統得到復興,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意識非常強烈。他們宣稱,“(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雖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皇帝雖然可以命令大臣,但是不能違背道理;大臣雖然要為皇帝服務,但是不能盲目曲從。
與此同時,宋代統治者也更加充分地認識到對最高權力進行約束的重要性。據說趙匡胤曾立下誓碑,“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在石碑上留下遺囑,告訴後代皇帝不得殺掉給皇帝提供意見的人,以“養成臣下剛勁之氣”。不管此事是真是假,有宋一代,確實基本沒有殺戮過士大夫。“與士大夫共天下”成為北宋君臣間一條不成文的約定。文官犯了再大的錯,受到的懲罰也不過是貶官而已。宋高宗時,監察御史方庭實居然敢這樣對皇帝宣傳“民主理念”:“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皇帝也沒能拿他怎麼樣。
宋真宗有一次派人拿著親筆詔書來見宰相李沆,詔書的內容是封他寵幸的劉氏為貴妃。李沆認為這個命令不合理,什麼話也沒說,當著太監的面,把皇帝的詔書放到蠟燭上一把火燒掉了,然後對太監說,你就跟皇上說,我不同意。(《宋史·李沆傳》)皇帝也只能無可奈何。
宋代還形成了朝省集議制度,就是集體決策,遇到重大問題,要文武百官一起開會,大家商量解決,皇帝不搞一言堂。有的時候,如果這項政策會影響到普通老百姓,影響到某個行業,還會邀請老百姓參加,就像今天的政策聽證會。比如宋太宗的時候,要起草關於茶葉經營的法律,就專門請來幾十名經營茶葉的商人,讓大家充分發表意見,“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宋史·陳恕傳》)。北宋熙寧年間,在改革財政稅收制度之前,朝廷專門請市井商人,甚至殺豬的、賣肉的,都到朝堂上參與討論,“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二五,熙寧四年七月丁酉)。這在其他朝代,是絕對不可想象的。
宋代政治當然也存在著傳統政治的大量弊端,比如重文輕武、防民過甚,導致國防實力下降;比如地方分權過甚,官員數量過多,造成“三冗”;再比如我們後文將要講到的王安石變法中的一些內容。但是,總體來說,宋代仍然可以說是中國政治文明發展的最高峰。宋代享有空前絕後的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出現了許多民間的小報,稱作“新聞”。小報有自己的專業“爆料人”“記者”:“近年有所謂小報者……訪聞有一使臣及合門院子,專以探報此等事為生……以先得者為功……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報為先,而以朝報為常,真偽亦不復辨也。”這種小報非常注重時效性,由於訊息新奇快捷,發行面廣,勢頭甚至壓倒了政府發行的朝報,因而利潤頗豐,成為我國最早的新聞產業。另外,宋人還享有廣泛的結社自由,只要不拿武器,政府保證人民的結社集會自由,從不加以干涉。宋代演戲,經常諷刺朝政。宋高宗時,著名的奸臣秦檜走後門,讓自己的兒子成了狀元,結果不久,就有人把這件事編成了一齣戲,公開演出,秦檜也無可奈何,沒法處罰。北宋著名昏君宋徽宗看戲的時候,演員在臺上公開批評他的政策不好,“只是百姓一般受無量苦!”,讓老百姓受了很多苦。宋徽宗聽了,“為惻然長思,弗以為罪”,也不敢怪罪這個演員。
推動文明發展的因素是複雜的。中國2000年不停的迴圈,實際上反映出兩方面力量的較量,君權與臣權,中央與地方。這種較量曾經達到了一種難得的平衡,導致即使在基於君主利益而設計的大一統郡縣制度的框架內,君權也曾經得到過比較有效的約束,大一統郡縣體制在遭遇危機後終獲平衡,因此收穫了比較輝煌的政治文明和文化成就。
在比較高的政治文明的基礎上,宋代也取得了輝煌的物質文明。很多人認為,中華文明的頂點在宋朝。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中華文明經過幾千年的曲折發展,在宋朝達到了文化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