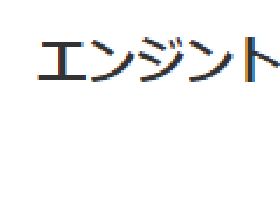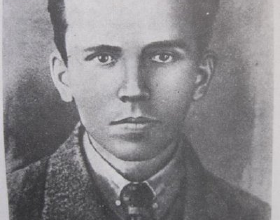春節期間,央視《人世間》熱播。我們一家人也很喜歡,因為充滿了人間煙火氣,道盡了市井百態、人間冷暖。
不過也有人看著不舒服,說上山下鄉那場戲是給社會主義抹黑,那時都是高高興興去的,沒人哭天抹淚。
有高高興興去的,那時青年滿腔熱忱,毛主席的號召讓人熱血沸騰,激動人心。少年不識愁滋味,但是做父母的有生活經驗,他們有憂慮,有擔心,有不捨,流眼淚情有可原,扣上抹黑社會主義的大帽子擔當不起。但真的到了那地方還笑的出來,也只能說是苦中作樂。
我姐姐是高一16歲就沒讀書了,去了山上的林場。因為到處鬧得厲害,不去不革命啊(這也是個大帽子)。16歲的小姑娘跟大老爺們似的,在山上伐木,抬大樹。夏天大個蚊子咬人厲害,冬天經常零下二、三十度,大洋泡嗚嗚的。那個累啊,還不敢發牢騷,只敢過好久回家一趟跟我媽哭。
上山下鄉早期人不多,採取穩妥的策略,對國家建設添磚加瓦,起到了比較好的作用。但是到了六十年代後期,變成了一項政治運動。當時社會經濟單一,失業率高,又鬧運動,文革,書也念不下去,十五、六歲的學生,該唸書的時候不念書你覺得正常嗎?造成了至少十年的教育斷層。每年崗位不多,畢業學生沒地方安,城市壓力巨大。沒有做好準備工作,統籌安排,呼啦啦成百上千萬青年學生湧入農村,對家庭,社會都造成了巨大沖擊。
知青受到歧視、打擊,侵害的也一定程度的存在,你不能說是無病呻吟。去的時候有踴躍報名的,就業困難,也無處可去。也有強制的,登出城市戶口,扣父母工資。政治運動,你去體會。
挺過去的是鍛鍊,挺不過去的是傷害。每個人去的地方不同,際遇也不同,別人遭受的你未必經歷過。
太陽都有黑子,黨也對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總結了經驗教訓。所以,就不必在傷口上塗脂抹粉,文過飾非了。至於說甘如瓊漿,豔若桃李則完全是不在一個頻道上的了。
由電視劇中的一些情節,再說說我在東北的童年生活,頗有親切感。
劇中周秉昆穿了件五花六花的毛褲。我一個男孩子,母親用幾件舊毛衣拆下來的線,合起來織件五顏六色毛衣給我穿,把姐姐小了的花衣服煮成藍色我哥穿。六一節,學校裡要我們穿白鞋,母親捨不得買,用粉筆把我藍鞋子塗成白色,搞得我嘟半天嘴。廣播操比賽我沒運動衣,躲起來沒參加。事情過去了,現在作為笑談。
還有個細節,冬天睡覺,蓋了被子,還把棉衣再蓋到被子上,這個拍的有感覺。門簾是刺繡的,我姐那時用複寫紙描下圖案,多是鴛鴦、花、鳥、魚的圖案,拿個繃子繃住白布,繡了再用剪刀修。
東北冬天長,氣溫低。秋天就要在地窖裡儲藏大白菜,蘿蔔,土豆。有個人說劇中一桌子炒菜是錯誤,應該是燉菜,小雞燉蘑菇之類。真是做夢呢!那個年代,肉都難得吃一回,哪裡有什麼小雞?
有一年快過年了,我父親買一筐冰凍帶魚,一家人喜歡的不得了。母親經常去商店裡買幾分錢一斤的爛蘋果,回來把爛的地方削掉給我們解饞。那時每人每月糧食定量,這個可以理解,國家困難,要保障老百姓生活必需。每人每月一斤白麵一斤大米,主食粗糧,大碴子,高粱,小米,煮飯粗糙,一般煮粥。粥不頂飽,涼的大餅子和窩頭我們也吃的有滋有味,擱現在不行了,呵呵。母親就用玉米麵加點白麵做發糕。逢年過節才吃餃子,母親放幾枚洗過的鋼鏰到裡面,說吃到了就會有好運。
父親撿了幾小塊水淹地偷偷種了茄子、豆角、黃豆,改善家裡生活條件,不敢讓單位知道。黃豆榨油後拿回家的豆渣餅我吃過,挺香的。
冬天的蘋果和鴨梨都凍得像石頭一樣硬,要放到屋裡化一下才咬得動。鴨梨也叫花蓋梨,放到水裡,一會就結層冰,軟乎些就一層一層的啃。有人買了南方的橘子,裡面全是冰碴子。冬天吃一分錢一根冰棒,夏天三分錢一根牛奶冰棒。童年是美好的,因為只有兒童才是無憂無慮的,擔子都是壓在父母和哥哥姐姐身上的。
冬天刮大洋泡,大風天氣,就不準生火了。提前通知,做好乾糧。我們那房子一趟趟都是七八戶連在一起的平房,繕的是草,一個火星飛上去就引燃了。房子是土坯的,炕也是土坯的。有個大炕,還有個小炕,姑娘大了睡。玻璃木窗兩層,冬天往裡灌鋸末渣,縫隙用紙條糊上。裡面熱,外面冷,玻璃上就會有冰花,想象成各種圖案。
腳踏車是奢侈品,要一百多塊錢,幾個月工資,還要有條子才能買得上,鳳凰,永久兩牌子響。我父親買了塊上海牌手錶,後來又買了個鬧鐘,是個母雞吃米,頭會動,被我當玩具擰鬧鈴,擰壞了。
文娛活動一是看電影,二是聽戲匣子。看電影也要有關係才能買到好票,不然你就到哪個犄角旮旯去了,尤其是那個新上映的彩色故事片。收音機也不便宜,要一個多月工資,三國演義,水滸傳,岳家將,楊家將,聽的上癮。不然就八點來鍾早早睡去,省電省錢。
《人世間》,就是普通人在世間的生活,別上綱上線,真誠地生活,閒了看看電視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