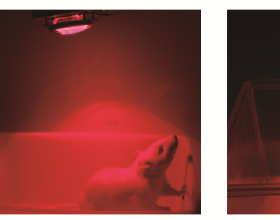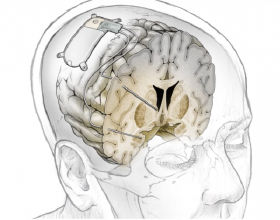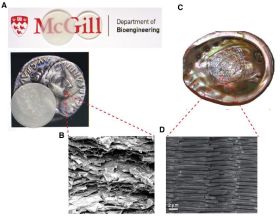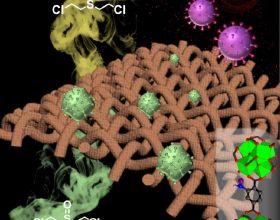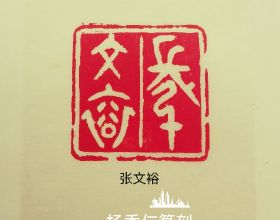作者維舟
江浙一帶近年興起了一種全新的婚姻模式:“兩頭婚”。顧名思義,這是男女雙方“兩頭大”,既不是男娶女嫁,也不是男方入贅,而是兩家對等,“我家不是嫁女兒,你家不是娶媳婦”。小夫妻成婚之後,兩邊都有婚房,兩頭走動,與原生家庭仍然聯絡緊密,孩子也最好生兩個,一個隨父姓,一個隨母姓,延續兩姓血脈,皆大歡喜。
像很多新生事物一樣,外界對“兩頭婚”有不少爭議、誤會和疑慮,肯定者認為這能帶來更平等協商的家庭氛圍、甚至是扭轉少子化的趨勢;質疑者則認為這樣一來,婚姻已純粹淪為一種形式;但更多的人則是忽視,不知道這樣的現象有什麼意義、為什麼值得關注。實際上,這一滴水或許可以折射出當下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的變動。
▌為什麼會有“兩頭婚”
“兩頭婚”的出現不是偶然的,首先出現在長三角一帶更非偶然。
我老家(上海郊外的崇明島)的“兩頭婚”並不太多,但1990年代初也出現了這樣的苗頭。雖然第一代獨生子女那時大多尚未婚配,但社會上已普遍覺得“女兒”也比以往“金貴”了。在當時鄉下蓋樓房的熱潮中,絕大部分家庭都會考慮給適齡的女兒預先留好婚房,按婚房標準裝修——方言稱為“立房頭”,女兒出嫁後回孃家,也能有一個獨立空間。
很多女性出嫁後,一年難得回來幾次,“立房頭”卻儼然成了不可動搖的規矩,如果家裡有兄弟阻撓,通常都被視為霸道的老舊思維。
當時還是獨生子女政策,很少有像現在這樣,生兩個孩子各繼承一家姓氏的,但它的變通形式也已經出現:很多孩子的名字,已由父母的姓氏拼合而成,例如宋楊、張李。這個習俗延續至今,我一位同學婚後的第一個孩子叫陳沈某,二胎放開後,老二就倒過來,叫沈陳某。
近些年,鄉下越來越多的外公外婆也讓孩子改口叫“爺爺奶奶”了。原本這僅限於那些招女婿的家庭,並且會遭人物議,似乎是一種虛名,倒會引發禮法上的混亂——因為兩邊都是“爺爺奶奶”,怎麼搞得清楚?但現在這不僅沒消亡,倒是更流行了,不是“兩頭婚”的家庭也這樣叫。
凡此等等,都可看出“兩頭婚”不是孤立現象,至少相關的一系列做法,在一些地方已被廣為接受,包括:“女兒也是傳後人”(計劃生育的著名標語之一),也能延續血脈、繼承家業,也有在孃家“立房頭”的權利;孃家為女性提供強有力的支援,確保她在婚姻關係中獲得平等對待。當然,“兩頭婚”的一個關鍵前提是:“本地人和本地人婚配”,因為本地人之間更容易知根知底,選擇婚配時也更傾向於“門當戶對”。
為什麼這樣的婚姻形態率先在長三角一帶出現?恐怕也是因為這裡的女性,在家庭的地位相對較高,同時地方經濟相對發達,使得原生家庭更有意願和能力支援女兒,進而更多考慮自家的財產繼承問題。兩邊經濟實力相當,女方更理直氣壯地要求得到和男方對等的權利地位。權利博弈,體現在了婚姻形態的變革上。
▌在傳統與現代之間
這種現象是好事嗎?這取決於你怎麼看了。
趙春蘭是較早關注到這一現象的學者,在她看來,這是一個積極的嘗試,可以改善代際關係,過程充滿協商性:“‘兩頭婚’必然是男女雙方或者雙方家庭基於平等,達成的一種長期契約。婚姻這種契約關係要保持下去,不可能僅僅是一方的需求表達。”
她認為,“兩頭婚”是“傳統和現代在這個村莊和解”,對老百姓而言,這種方式既有傳統的一面(傳宗接代的需求、捨不得女兒離開原生家庭),又契合了當下的一系列需求——比如父母養老、家族財產繼承、情感陪伴,還有女性權利的興起,比如支援女兒、女方冠姓權。
在尋求“傳宗接代”的心理動機上,它是傳統的,但與此同時,支援女兒、女方也想要冠姓權,又是一種現代訴求。以往鄉下的宗法社會里,“絕後頭”甚至是比問候親媽更嚴重的辱罵,也是維繫父權制習俗的根本象徵,因為男性家長對家族成員的所有權,是圍繞著他的姓氏運轉的。在現實中,哪怕是兩性關係相對平等的北歐,結婚隨夫姓、孩子隨父姓仍是預設的習俗,但近些年國內社會已出現了越來越多這樣的呼聲:為什麼懷胎十月、並且以壓倒性比例花費更多精力養育子女的女性,不能給孩子冠以自己的姓氏呢?
當然,會有人嘲諷說,姓氏不過是個象徵,而女性爭的冠姓權,說到底仍是自己的父姓。
也正因為這種婚姻形態同時混雜著傳統理念與現代性,才使得對它的解讀充滿了爭議:因為從個人主義的視角來看,這看上去像是雙方父母干涉了兒女的生活:不是小夫妻自己成立家庭,而是作為家族傳承的一分子,與現代婚姻提倡的婚姻獨立自主格格不入,更激烈者甚至指責這是讓女性淪為生育工具,要為兩家生孩子;而對於理念正統的人來說,它又像是離經叛道。實際上,它所表現出來的“妥協性”,也正是它的“不徹底性”。
▌在傳統與現代之間
“兩頭婚”,乍看上去是爭取“兩性權利”,其實是爭取“兩家權利”,像是以兩家利益為後盾的博弈。
婚姻本身也是一項財產製度,夫妻雙方是把原本和未來的私人財產加以合併,共同撫養後代,透過個人協議約定分配。既然如此,像“兩頭婚”這樣始終把財產留在自家人手裡,倒也省事很多。儘管這也難免會帶來一些新問題(例如,父母兩家的經濟能力不太一樣,那兩個第三代孩子的財產繼承怎麼辦,何況這種經濟實力可能不斷變動),但最大的好處就是兩家對屬於自己支配的財產,擁有了明確的界限和安全感。
為什麼“兩頭婚”在一些地區愈演愈烈,深入一層就會發現,與其說取決於雙方的協商,倒不如說各自追求權利邊界的清晰化,預先防止對自家權利和財產的意外衝擊,即便離婚也好合好散,極大地降低了離婚成本和相應風險。
這意味著,“兩頭婚”的“權利”,並不僅僅意味著冠姓權等方面的平等,還有關鍵的財產權層面的考量。這也可以解釋為何男方家庭願意讓出傳統上屬於己方的一系列權利,因為清晰的產權分割對他們也有利。
事實上,城市家庭也面臨同樣情況:這些年房價高企,男方越來越不願意單方面承擔買房壓力,或不願意把女方的名字寫到房產證上,這從另一側面也顯示出了不少中國家庭對私有財產權缺乏安全感,以至於一開始就明確邊界,直到加深信任後,才可能願意把私人財產變成共同財產。
然而,原生家庭深度介入,就會在支援、維護自己子女利益的同時,很容易逾越邊界,讓小家庭內部的夫妻雙方對立起來,維護各自的原生家庭,阻礙了小家庭的凝聚成形。老一代父母在婚姻中的主導地位上升,甚至讓婚姻變成了可有可無的形式,五四以來的那種浪漫愛情觀更是遭到嚴重衝擊。
“兩頭婚”,或許是一場充滿了精細盤算之後的妥協,既能提升老一代在婚姻中的主導地位,也使財產權得到安全保障,它之所以出現,正是迎合了一些富裕起來的、有財產可以分割的家庭的某些潛在需求。如前文所說,這是個混合了現代和傳統的新生事物,一方面顯示了人們財產和權利意識的興起,另一方面卻還在傳統的宗法家庭框架內。只有當年輕一代習慣作為獨立自主的個體從家庭中脫嵌出來,能在個體權利得到充分保障的基礎上自由戀愛、自願組合時,“兩頭婚”才可能告別它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