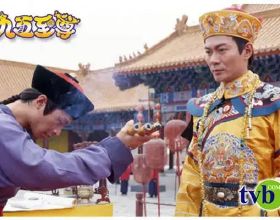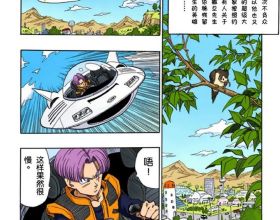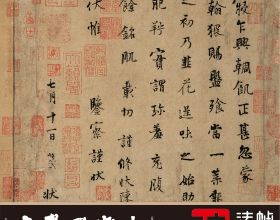北京冬奧會開幕式上,以中國傳統二十四節氣場景作為倒計時畫面的創意,震撼了全世界的觀眾。在二十四節氣中,立春是冬奧會開幕的日子,需要最後一個出場,這樣一來,在倒計時畫面中第一個出現的節氣,就變成了雨水。
如果說立春是一年時間的起始,那麼雨水時節,就是一年生命的起始,從自然草木,到農圃作物,再到人類本身,都在雨水時節展現出了無限的生命力和發展潛能,由此觀之,冬奧會開幕式以“雨水”作為二十四節氣倒計時的起始,不僅與冬奧會開幕的日子配合,還恰到好處地展示了中國傳統中的“生生不息”之理,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的活力與生機。
最早記錄二十四節氣的《逸周書·時訓解》,不但將一年分為了二十四個節氣,還將每個節氣以五天為限,劃分為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列舉了相對應的物候,一年共有七十二候。後世將《逸周書·時訓解》與《禮記·月令》結合起來,構建出“月令七十二候”的物候體系。在七十二候中,雨水節氣的三個物候分別是:“雨水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雁來。又五日,草木萌動。”其中所描述的自然現象雖然不一定與時日完全對應,但卻體現出了雨水時節萬物復甦、欣欣向榮的特徵。
雨水和驚蟄孰為農曆一月的節氣?
在如今的二十四節氣中,雨水緊跟著立春,是農曆一月的第二個節氣,再接下來是驚蟄、春分。這樣的順序與《逸周書·時訓解》《淮南子·天文訓》等先秦、漢初文獻中記載的二十四節氣順序是一樣的。但是,在東漢班固編寫的《漢書·律曆志》中,春季前四個節氣的順序卻是立春、驚蟄、雨水和春分,其中驚蟄和雨水的順序,和現在通行的順序恰好顛倒。這樣先驚蟄、後雨水的歷法,在漢代曾經通行過很長時間,東漢經學家鄭玄在註釋《禮記·月令》時特別說明“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漢始以雨水為二月節。”古時將每月兩個節氣中的前一個稱為“節”,後一個稱為“中”或“氣”,所以鄭玄這段話的意思,就是漢代開始,驚蟄成為了正月的第二個節氣,雨水則退為二月的第一個節氣。
那麼,漢代人為何要調換雨水和驚蟄次序呢?這與儒家經典《禮記·月令》有關。《禮記·月令》將一年分為四季,每一季分為孟、仲、季三部分,各自對應一個月,在每一個月份之下,又記錄了本月的自然物候變化,並根據自然狀況,規定了本月人類社會的行事準則,可以說是一份完整的年中行事指南。在《禮記·月令》中,雖然沒有明確出現“二十四節氣”的說法,但是其中的不少表述,都和後世節氣的名稱相似,比如《禮記·月令》在描述孟春(一月)的物候時說“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其中“蟄蟲始振”指蟄伏的蟲蟻在春天重新煥發生機,這和二十四節氣中的“驚蟄”意思幾乎相同。但是,按照《禮記》的說法,“蟄蟲始振”是一月的物候,二十四節氣中的驚蟄卻是在二月,這就與儒家經典發生了矛盾。同樣,《禮記·月令》在描述仲春(二月)的物候時,又有“始雨水”的說法,其中的“雨水”與節氣中的“雨水”字面相同,但二十四節氣中雨水卻在一月。此外,另一篇與《禮》有關的經典,被認為反映了夏朝曆法的《大戴禮記·夏小正》中,在描述正月的物候時也有“正月啟蟄”的說法,這裡的“啟蟄”,就是“驚蟄”的原名。
這樣看來,在《禮記·月令》和《大戴禮記·夏小正》兩篇儒家經典文獻中,都認為“蟄蟲始振”或“啟蟄”是一月的物候,“雨水”是二月的物候。雖然兩篇文獻都沒有明確提到“驚蟄”或“雨水”是“節氣”,但後世在安排二十四節氣的順序時,如果按照原先的傳統,將雨水放在一月,將驚蟄放在二月,則不免與儒家經典有所扞格。所以西漢末年王莽改制時,國師劉歆奉命編定新的歷法《三統曆》時,就將驚蟄放到了一月,雨水放到了二月,以與《禮記·月令》《大戴禮記·夏小正》的記載配合。這種新的節氣順序,在儒家學者那裡很有市場,比如東漢末年的蔡邕,在疏解《禮記·月令》時,雖然在整體上駁斥了《三統曆》,但依然接納了先驚蟄、後雨水的順序。
不過,到了魏晉南北朝之後,儒家思想在社會中的統治力開始受到衝擊,人們開始廣泛關注《淮南子》這樣的道家、雜家文獻,再加上西晉汲冢戰國古墓中出土了《逸周書》的古文版本,使得這部非儒家的先秦典籍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重新認可《淮南子》《逸周書》中對於二十四節氣的排序。南朝劉宋時學者何承天上《元嘉歷》,“以……雨水為氣初”,在沈約《宋書·律曆志》和敦煌出土的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的日曆中,二十四節氣已經回到雨水在一月緊跟立春,驚蟄在二月開啟春分的順序,和現在一樣了。
雨水物候:鴻雁來,草木萌動,春雨綿長
上文提到最早記錄二十四節氣的《逸周書·時訓解》,不但將一年分為了二十四個節氣,還將每個節氣以五天為限,劃分為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列舉了相對應的物候,一年共有七十二候。由於《逸周書·時訓解》中描寫物候時所用的語句,和《禮記·月令》中描寫各月的句子相似度非常高,所以後世將兩者結合了起來,構建出“月令七十二候”的物候體系。在七十二候中,雨水節氣的三個物候分別是:“雨水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雁來。又五日,草木萌動。”其中所描述的自然現象雖然不一定與時日完全對應,但卻體現出了雨水時節萬物復甦、欣欣向榮的特徵。
三個雨水的物候中,“鴻雁來”指大雁從南方飛回北方,“草木萌動”指花草樹木生長萌芽,這些都是春季天氣回暖之後的典型自然變化,比較容易理解。“獺祭魚”則比較有趣,這裡的“獺”主要指水獺,據古人的觀察,每到春季雨水前後,河冰解凍,游魚上浮,水獺在捕獵游魚之後,常會將魚拖出水中,陳列在岸上,同時後腿站立,兩隻小手放在胸前,好像是在做祭拜的動作。儒家在舉辦宗廟祭祀之禮時,需要先以食物祭祀祖先,然後再自己進食,對於崇信儒道、注重禮儀的儒家學者而言,水獺這樣的動作,表現了動物也會遵從祭祀之禮,正是禮教合於自然天道的證據。舊題元代吳澄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釋“獺祭魚”時,將其與霜降節氣的物候“豺祭獸”並提,說:“祭魚,取魚以祭天也。所謂豺獺知報本,歲始而魚上游,則獺初取以祭。”認為這體現了水獺“不忘本”的高貴品質。
除了遵循禮教之外,獺祭魚還有一個意義,就是標誌著一年漁業活動的開始。早在先秦時期,古人就有了可持續發展的觀念,《逸周書·文傳解》中記載著文王頒佈的禁令:“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認為在魚類生長繁殖的時候,需要有一段休漁期,避免過度捕撈造成漁業資源的枯竭。那麼這個“非時”的標準如何劃分呢?古人認為,每到春天,水獺開始“祭魚”,說明自然界中的生物已開始了捕魚捕獵,這體現了自然天道對捕獵活動的默許,人類於此時開展漁獵活動,方是不違天時。《禮記·王制》雲“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就是以雨水“獺祭魚”的現象為界,區分休漁期和開漁期的。在唐代武后執政的時期,曾經長期推行過素食政策,官員不得殺生而食,鳳閣舍人崔融上書表示反對,其中提到“春生秋殺,天之常道。……豺祭獸,獺祭魚,自然之理也。”以“獺祭魚”為例,說明物種互相捕食,是天道允許的行為。在這個時候,雨水時節捕魚而祭的水獺可能怎麼也想不到,自己居然成為了左右人類社會政策的關鍵角色。
當然,雨水時節最有代表性的物候,還是春雨。不同於夏雨的猛烈和秋雨的淒涼,春雨雨量不大,卻綿延悠長,給人一種溫柔潤澤的感覺。元稹曾寫過一組《詠二十四節氣》的律詩,《雨水》一篇寫道:“雨水洗春容,平田已見龍。祭魚盈浦嶼,歸雁過山峰。雲色輕還重,風光淡又濃。向春入二月,花色影重重。”其中除了獺祭魚、北雁南歸等《禮記·月令》中提到的物候之外,“雲色輕還重,風光淡又濃”兩句,寫出了春日風物在細密春雨的掩映下陰晴不定、濃淡交錯的朦朧感。韓愈《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中的名句“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更是最貼切地表現出春雨若有若無、如絲如夢的感覺。
隨著春雨而來的,是前面提到的“草木萌動”的物候,雖然此時的草木尚在初生的狀態,但已經為冬日單調的大地增添了一分亮色。草木生長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的欣欣向榮之態,也會給人帶來強烈的生之喜悅。唐代詩人獨孤及《山中春思》雲:“獺祭川水大,人家春日長。獨謠晝不暮,搔首慚年芳。靡草知節換,含葩向新陽。不嫌三徑深,為我生池塘。”詩人雖然遠離人世,獨處山中,但依然被雨水時節萌動生機的春草所安慰和感動。而清代乾隆帝《月令七十二候》詩寫到雨水時節“草木萌動”之候時所說“遍地含芽及莩甲,連林柳眼與梅心”,則是更加直接地展現出了雨水時節草木無處不在的蓬勃生命力。
雨水民俗:以“爆米花”預測稻種成色
雨水時節的“草木萌動”,對於文人來說是增加了賞心悅目的美景、窺情鑽貌的詩材,對於農人來說則標誌著一年生計的開端。清人劉秉恬《春雨》詩云:“雨水節逢雨水勻,眼前氣象又添春。落梅片片如垂露,弱柳絲絲可壓塵。和漏今宵聽滴瀝,潤苗來日更精神。年年幸獲豐年象,感切無邊造物仁。”其中“落梅片片如垂露,弱柳絲絲可壓塵”是以詩人之眼欣賞花木勃發之美,“潤苗來日更精神”則是以農人之心讚美雨水對農作物的滋養之功。
春天是播種的季節,播種的時機與天候的晴雨有著密切關係。上海俗諺雲“春雨貴似油,點滴弗白流”,春雨對作物的生長意義重大,要讓莊稼切實享受到春雨的滋潤,最好在雨水前後完成播種植栽。清人王文清《區田農話》說:“《孟子》‘不違農時’,以春耕為第一義。春耕之始,必在雨水節前。”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按照《禮記·月令》的要求,古時的君王在“草木萌動”之後,通常需要頒佈農業政策,測量劃分土地範圍,尋找適合不同作物的土地,親自指導百姓耕種之法,所謂“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農人對耕種的時機、土地和手法具備了相當的瞭解,在雨水節前依法播種,才能最大程度確保一年的收成。
除了選擇合適的播種時間之外,種子的選擇也很重要。在雨水時節,民間有一項重要的傳統習俗,叫作“佔稻色”。清代乾隆帝下令編定的《授時通考》引《田家五行》雲:“雨水節,燒乾鑊,以糯稻爆之,謂之孛婁花,佔稻色。”在雨水時節,人們會將鍋子燒熱,放入糯稻,使其外表在高溫下膨脹爆開,以此預測稻種的成色,爆開的糯稻叫“孛婁花”。具體“佔稻色”時,人們會將早稻和晚稻等不同的糯稻各抓一把,放入不同鍋中,哪個鍋中爆開的糯稻最多最白,就說明這種糯稻成色最好,當然也就最適合大面積播種。
這種爆糯稻以占卜的習俗,早在宋代就已經在江南地區出現。南宋范成大《吳郡志·風俗》言吳郡人每到初春,就會“爆糯谷於釜中,名孛婁,亦曰米花,每人自爆,以卜一歲之休咎。”由此可見,這種佔稻色用的“爆孛婁”,大概就是最早的“爆米花”。只不過我們現在經常在看電影時吃的“爆米花”,主要是傳自南美印第安人,用的“米”是玉米,而傳統的“爆米花”,用的則是糯米,現在江南一代“米花糖”之類的點心,更為接近傳統的手法。根據范成大的說法,吳郡人爆米花,不僅僅可以預測收成,還可以預測個人一年的吉凶,故又稱“卜流花”或“卜年華”。清人李詡有詩歌詠吳地爆米花占卜的習俗說:“東入吳門十萬家,家家爆谷卜年華。就鍋拋下黃金粟,轉手翻成白玉花。紅粉美人佔喜事,白頭老叟問生涯。曉來妝飾諸兒女,數片梅花插鬢斜。”從“佔喜事”到“問生涯”,爆米花占卜的內容既可以是姻緣,也可以是健康,可以說非常多樣化了。在上海,這種習俗同樣非常流行,乾隆年間文人李行南作《申江竹枝詞》詠上海民俗,其中就有對“爆孛婁”的描寫:“糯谷幹收雜禹糧,釜中膈膊鬧花香。今朝孛婁開如雪,卜得今年喜事強。”可見卜流年和佔稻色一樣,都是以稻穀爆開的程度和色澤決定結果好壞的。在農業社會,個人乃至社會的命運,與一年中糧食收成的好壞息息相關,從這個角度來看,從“佔稻色”到“卜流年”的轉換,也自有其合理性。
雨水時節“草木萌發”的物象,也很容易讓人進一步聯想到人類的繁衍與生長,清羅國綱《羅氏會約醫鏡》雲:“立春、雨水二節,得天雨,承接,夫婦各飲一杯,入房即孕胎生子。”認為雨水時節的雨,有促進生育的功能。在川西一代,民間在雨水時有“撞拜寄”的習俗,父母在這一天會帶領子女認乾爹乾媽,以此保證子女的成長過程中受到更多關愛和扶持。這些都是在雨水時節“生長”“發生”特性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民俗。
(徐儷成 作者為文學博士、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
來源: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