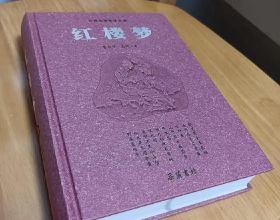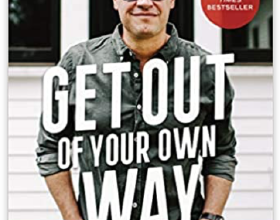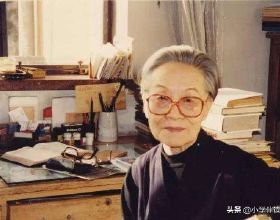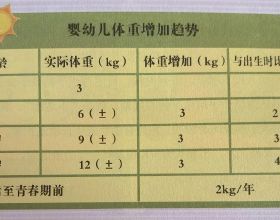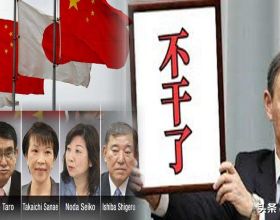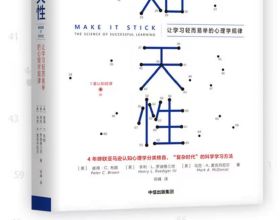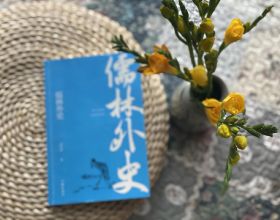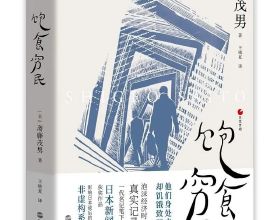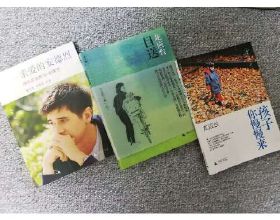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不要悲傷,不要心急!
憂鬱的日子裡需要鎮靜:
相信吧,快樂的日子將會來臨。
詩人總喜歡虛構美好的事物給人們遐想,喜歡美化一切不美好的事物對人們進行催眠,在春風得意之時,人們讀到這些詩會覺得生活充滿無限魅力,人生充滿希望;但是當苦痛的命運兇猛來襲,“鎮靜”並不容易,“快樂”也不是輕而易舉就能得到的事情。
一部《盲山》,一部《親愛的》,兩部電影將人販子拐賣婦女和兒童的罪孽在大螢幕上淺淺道出,叫人淚目。然而電影已經是美化過的表演形式,真實發生在那些貧苦山村中的拐賣案件,遠比我們以為的要更加殘酷和可怕,因為電影中的人物最後都會走出去,而真正困在大山深處的很多女人和孩子,也許一輩子都沒有機會再見到自己的家人。
秦蘭就是一個差一點無法再走出去的女人,她在一座陌生的大山中待了34年,最後終於跑了出來,她是幸運的,但無疑她又是極其不幸的。
她出生在貴州一個貧苦的小山區裡,貧窮和落後就註定了人們思想觀念的陳舊,秦蘭一出生就帶著兩個斷掌紋,“斷掌”被村子裡所有人認為是不吉利的象徵,認為她是天降的災星,所以從小她就受到了無數的冷眼和嘲諷,甚至她一經過別人就會把門關起來。
這種被人排擠和嫌棄的感覺非常不好,秦蘭很想幫家裡出點力,但是父母對她也總是視若無睹,將所有精力都放在她弟弟身上。
那一年秦蘭的父親去世,他們這個家庭的重擔一下子壓在了母親肩上,為了走出這個被大家排擠的地方,也為了給母親分擔生活的壓力,1983年,16歲的秦蘭帶著自己13歲的弟弟踏上了去往新疆的列車。
那時候有人到村子裡來招工,說一個月能掙15塊錢,這高額的薪水讓無數人都心動,秦蘭拿著母親給的40幾元路費,與弟弟逃票上了火車。
列車員在查票的時候將秦蘭的弟弟趕下了車,她當時躲在另一邊,僥倖逃過了查票,這時候當她想要找到弟弟時卻發現自己已經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而弟弟也已經不知道被趕到哪裡去了。無助、害怕、內疚,各種情緒一時之間全部彙集到16歲的秦蘭心裡,她不知如何是好。
而這時候她的處境一點都不輕鬆,因為沒有防備心,她在路上被人迷暈賣到了山東一戶人家,買她的人一個是打了一輩子光棍的中年男子,他們一家人看見她之後眼睛放光,秦蘭很害怕,但是不敢反抗,因為他們送給她的“見面禮”就是一頓毒打。
在這一戶人家飽受折磨之後,秦蘭又被轉手賣到了東北一個貧苦的村子,這一戶人家裡有兩個年紀都不小的男子,他們在看到秦蘭之後同樣展露出凶神惡煞的一面,先將她打了一頓,隨後便將她當成了自己的媳婦,不過是一個完全沒有自由可言的媳婦。
囚禁、打罵、當成工具、鐵鏈繩索......所有在影視作品中出現過的片段全部是秦蘭真實經歷過的,她在十幾歲,在兩個年紀比自己大幾十歲的的男人面前,她連哀嚎的資格都沒有。
整片地方的人都一樣麻木,他們對從外面買過來的女人和小孩都持冷眼旁觀的態度。在他們眼裡這早都已經是習以為常的事情,女人的嘶吼和孩子的啼哭都只代表著他們是正常的人,而語言不通則會讓他們的哭喊變成像動物一樣的嘶鳴,秦蘭逃跑的時候村民會幫著一起追,她早已經被一個封閉的世界鎖住了。
放棄了掙扎之後,秦蘭終於從房間裡被放了出來。她的心裡還有執念,還記得自己是從哪裡來的,但是這些執念只能化作晚上滴在枕頭上的熱淚,不能表現出來。女兒出生了,沒過幾年兒子也出生了。
生下孩子就是她被賣到這個家庭最大的價值,她的“使命”已經完成,“丈夫”和“婆婆”的態度也變了很多,她終於可以像村子裡面的其他農婦一樣正常出門,她也接受了自己只能在這裡耗盡半生的現實。
孩子畢竟是自己生下來的,親生骨肉不能不管,秦蘭決定將孩子撫養成人之後就想盡辦法離開。女兒不被“家人”支援讀書,她便逼著女兒走出大山打工,見見世面;兒子還算機敏,她就逼著兒子不斷學習,最後終於考上了山外面的學校。在子女長大之後,她終於感覺自己得到了救贖。
她已經在這個村子待了三十幾年,沒有人還會擔心她會逃走,也沒有人用鎖鏈再拴著她,她終於逃了出去,後來透過四處打工賺的錢在《等著我》這檔尋親節目上尋找自己的弟弟,希望完成自己的心願,也解救自己幾十年的愧疚。好在她最後見到了弟弟,一個遲到了幾十年的擁抱,讓所有人都為他們感到心疼和高興。
拐賣婦女和兒童是違反我國法律的事情,這種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大,給人們造成的傷害不可彌補和挽救,根據《刑法》第二百四十條:拐賣婦女、兒童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並處沒收財產。
拐賣秦蘭的人販子很有可能已經在某次打拐行動中被抓住,已經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就算沒有被抓住,警方對打擊拐賣人口犯罪的決心也是不容懷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