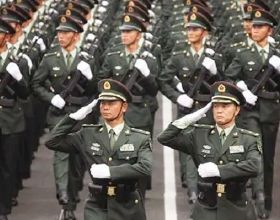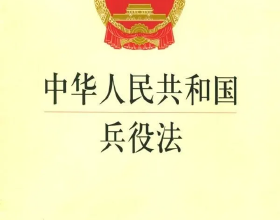“遙遠到底有多遠?”這是我在上軍校期間無數次思考過的問題。
那時,我渴望“遙遠”:世界上最高的人控雷達站“甘巴拉雷達站”、位於祖國最北端的“漠河雷達站”……這些邊遠艱苦雷達站的事蹟,我耳熟能詳。
“到基層去,到艱苦的地方去,到軍事鬥爭準備最需要的地方去,長期為建設資訊化部隊、打贏資訊化戰爭服務!”畢業前夕,我鄭重遞交戍邊申請書,最終如願以償,被分配到距邊境很近的北部戰區空軍某雷達站。

從繁華都市到邊境小鎮,從千里草原到浩瀚戈壁,去雷達站報到的路上,我眼中的景象不斷變換,最後定格在夜色中的幾點微弱燈光。到達雷達站,已是晚上9點多。雖然正是盛夏時節,但邊防雷達站夜晚的寒冷已有幾分刺骨,開啟車門的一瞬間,我便不由地打了個冷戰。
走進宿舍,一個戰士正在掃地。不等互相介紹,他便拽著我走進食堂,指向飯桌上一碗熱氣騰騰的麵條說:“知道新排長要來,站裡特意為你準備的‘紮根面’。”麵條誘人的香氣撲鼻而來,我這才意識到自己趕了一整天路,近9小時沒進食,已是飢腸轆轆。
交談中得知,這位戰士名叫陳林孝,是操縱班班長。也許是怕剛來陌生環境的我拘束,在我埋頭吃麵的時候,陳班長不停地向我“絮叨”:“這裡常年6級大風,無霜期僅有97天,冬天最低氣溫能達到-40℃。”“快遞站點在十幾公里外的小鎮上,站裡半個月出車採購一次食材,包裹到了可以讓他們帶回來……”或許是一路奔波讓我感到疲憊,或許是那碗熱湯麵實在暖胃,又或許是戰友話語間充滿溫暖,從學校到部隊的第一個夜晚,我沒有想象中那麼“水土不服”,伴著沙礫敲擊窗戶的隱約風聲,我睡得格外踏實。
第二天吃過早飯,值班員便吹響了集合哨。那天,我們的任務是改造老舊洞庫。跟隨隊伍走近一個佈滿砂石的山體,我看見一個磚頭壘起的洞口。這是上世紀60年代,老一輩雷達兵為了作戰需要,自己動手挖山掘地建成的隱蔽洞庫。雖然,洞庫如今看著有些破敗,但我彷彿能感受到它蘊含的無窮力量。

由於駐地偏遠、遠離機關,站裡決定自己動手在老洞庫基礎上進行加固改造,使其成為具有倉儲功能的小庫房。還未進入洞庫,一股黴味便撲鼻而來,陰暗潮溼的半地下洞庫已荒廢多年,改造並非易事。正當我考慮如何著手時,一位二級軍士長已走入洞庫,忙碌了起來。後來才知道,他叫吳邦學,雷達技師,那年43歲,在雷達站已經度過了22年時光,是全站兵齡最長的兵。

剛到9月,駐地就迎來第一場雪。鵝毛大雪下了整整一天一夜。出生於寧夏,求學在武漢的我,從未見過積雪沒過小腿的壯觀景象。正當我驚奇、沉浸於雪景時,值班室的對講機突然響了起來:“乙組雷達天線異常,無法轉動!”

此時,距乙組雷達擔負戰備值班僅剩不到1個小時。吳邦學聽到呼叫頂著狂風暴雪跑向雷達陣地,等我也趕到陣地時,吳技師已經爬上8米高的天線。檢查、維護、恢復,1小時後,雷達天線故障清除,正常擔負戰備值班。老吳不顧雙手凍得發紫、麻木,從陣地下來徑直走進雷達方艙,繼續監測雷達開機後的各項資料,確保萬無一失。
在和雷達站官兵朝夕相處的日子裡,我逐漸認識被評為首屆空軍“百名優秀雷達操縱員”的情報分析師康洪、下士第一年就榮立三等功的指令標記員陳勝、為演訓任務屢次推遲休假的雷達操縱員潘彬……駐守在邊境一線,他們守望在遠離祖國首都的地方,心卻始終緊緊貼著祖國的心臟。

如今,軍校畢業已一年多的我,不再關注荒涼與繁華之間是否隔著“遙遠”,也不再關心“遙遠”與“艱苦”是否近義,而是同每一位邊防雷達站的戰友一樣將關注點放在戰位本身,放在使命責任上。

邊防官兵,就像這片荒灘上隨處可見的石頭,單個看都很普通,但把這些石頭一塊一塊壘起來,就成為一堵城牆、一面界碑……
文章作者:王寅旭
主 辦:北部戰區空軍政治工作部
刊 期:第1341期
本期編審:劉小兵 劉漢寶
責任編輯:李俊林
文字統籌:劉若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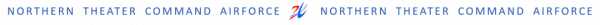
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
分享
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