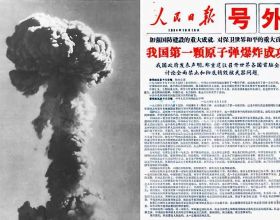餘秀華是一個命運多舛的女人,剛出生時因倒產缺氧導致的腦癱,註定她不能再靠女性的婀娜而取悅他人。只要不成為他人的累贅,不招人過分嫌棄,就已是燒了高香。
是詩歌拯救了她。
《詩刊》編輯劉年先生從一堆文字裡把她扒出來,就像從橫店坡窪上荊棘密佈的亂草中,薅出了一棵被枯枝敗葉包裹的靈芝,抖掉粗劣的草屑,就有靈光閃現出來。
餘秀華的詩不矯情不做作,表情達意沒有忸怩作態,沒有塗脂抹粉,像是一個被偷了幾次東西的村婦,出了門就把肚子裡的憤怒和詛咒喊出來。不想給對方拷問靈魂的機會。該愛的不顧一切去愛,該恨的咬牙切齒去恨。
不久前,她給已經上大學的兒子寫了一首詩,名字就叫《寫給兒子》,詩的第一節是這樣的:“兒子,與你相比我越來越矮了,所以你就要看到我看不到的風景了,我不要求你描繪給我聽,但你要把足跡留在某一個晨曦,聽見風,理解風,聽見雨憐憫雨,由此悲憫這個世界和一個殘疾的母親…”
開篇兩句,“兒子,與你相比我越來越矮了,你就要看到我看不到的風景了”,就把一種榮華散盡、失落感傷的情緒傳達出來,讓許多為人父母者的心絃突然被叩中,有了共鳴,有了諸多的聯想。
顯然,餘秀華這樣說,是在表達兩種意思:
一是說隨著歲月流逝,母親的身軀日漸佝僂萎縮,而兒子的身軀卻日漸高大挺拔,已經遠遠高過母親,從目之所及的視野上來說,兒子看得範圍更廣,距離更遠。
二是說光陰荏苒,母親已盡垂暮之年,隨時都有
油盡燈枯的可能,而兒子正值韶華,生機勃發。註定有一天,母親的生命會戛然而止,而塵世的風景會在歲月的浸染下越發美豔迷人,可惜的是母親永遠看不到了,但是兒子可以看到,可以沉迷其中。
不管是哪一種表達,都讓我們看到了一種悽美。辛苦養大兒女的母親老了,她無法躲開歲月的侵蝕,無法打破生命的規律。但是母親無怨無悔。她有的只是希望兒子“在某一個晨曦,曉風憫雨,並且悲憫這個世界和一位殘疾母親”。這句話很容易理解,就是母親只希望自己走後,兒子能夠善良溫柔地對待這個世界,尤其不要忘了她這個殘疾母親…
言至於此,一個慈善盈懷,心胸開闊的母親躍然紙上,血肉豐滿。
餘秀華,命運給了你殘缺的身體,卻給了你超凡的智慧和高貴的靈魂;不久前,神農架養蜂人還給了你驛路梨花樣浪漫醉人的愛情。希望在你今後的詩歌裡,能少一些一觸即發的鋒芒。
因為那些遲到的饋贈,就是在告訴你:人間值得,不枉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