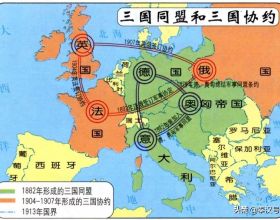說到明朝的朝堂,大家都會想到內閣以及票擬、批紅。可以說內閣制度差不多貫穿著明朝的始終,左右著這個皇朝的浮沉。兩百多年裡皇權和文官集團,也以內閣為戰場,爆發了無數的爭鬥。
雖然內閣對於大明的朝堂重要無比,但是內閣本身的實際權力卻很小。因為它誕生之初就被定性為一個秘書機構(為皇帝處理朝政提供諮詢和意見),不但沒有決策權,連奏事權也沒有。
說明:內閣的票擬本質上還是建議,決定權實際上還是在皇帝手中,並且明朝的皇帝們也始終沒有承認過內閣擁有決策權(只是皇帝們大多數時候不反對票擬)。
決策權大家好理解,沒有奏事權是什麼意思呢?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不能發起工單。內閣即便是想做什麼事情,他們自己也無權提。雖然明朝中後期,內閣閣員們開始兼任其它職務,從而變相地擁有了奏事權。但是這種方式限制很大,因為這個奏事權不能超出兼職範圍(兼職兵部不能奏報吏部事務)。
對於普通的朝廷官員來說這可能沒什麼大不了的。但是對於相當於丞相的內閣大員而言,這就很麻煩。因為他們想要推行的政策往往不會只侷限於某一個衙司,而是涉及到眾多部門的國策。這意味著他們必須要和外朝官員建立廣泛的聯絡,或者說被廣泛的牽制。
例如明朝最有名的內閣首輔張居正,他日常除了票擬之外,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給他的黨羽們寫信。除了聯絡感情,更重要的是告知他們該向朝廷奏請什麼事務了。
正是因為內閣有這個先天性的缺陷,所以明朝的內閣很難擺脫外朝文官集團的束縛,真正的成為可以直接下令的“丞相”。
不過在內閣形成之初,明朝的朝廷曾有個部門可以彌補內閣的這個缺失。
明仁宗洪熙元年正月初八,仁宗下令建弘文閣並鑄弘文閣印,這個新成立的弘文閣被仁宗交由他的老搭檔楊溥管理。弘文閣的職能是什麼?我們看看仁宗是怎麼說的:
命溥掌閣事,親授閣印,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學問。欲廣知民事,為治道輔。有所建白,封識以進。”
《明史·卷一百四十八》
我們可以看出弘文閣有兩大職能,其一是為皇帝收集資訊,其二是對於發現的問題上報建議。
仁宗的意圖是日常由文淵閣輔助他處理朝堂政務,弘文閣在外圍獨立收集資訊,以防外朝官員的遺漏或者瞞報。看似只是給予了奏事權,其實隱含了一項很大的權力 – 監督。
“封識以進”的意思是憑弘文閣印可以跳過正常政務處理流程直接上報於御前。這對於外朝官員們來說就是一種無形的震懾,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的行為是不是被弘文閣發現並如實上報於御前了。
因為不知道,所以在皇帝降罪或者質問前,他們也沒有辯解或者補救的機會。長此以往外朝的文官們會受制於弘文閣,甚至是會唯弘文閣馬首是瞻。
仁宗委任楊溥的原因,一是他太子期間長期合作而來的信任,二是楊溥本人也喜歡密報言事。雖然被成祖關了十年,楊溥一被放出來沒多久就密報言事並獲仁宗褒獎:
仁宗即位,釋出獄,擢翰林學士。嘗密疏言事。帝褒答之,賜鈔幣。
《明史·卷一百四十八》
仁宗本人應該是也挺喜歡密報言事這種行為,他除了賦予弘文閣這個機構這項權力外,同時還給予了自己親信大臣們同樣的權力。他賜予蹇義、楊士奇、楊榮、夏元吉、金幼孜等人“繩愆糾謬”銀印。憑此印,他們可以向皇帝密奏官員、皇族們的不法行為(不過這種更像是種恩寵而不是制度)。
如果仁宗能活得再久一些,弘文閣應該會如文淵閣一樣成為明朝的穩定建制。不論是它獨立成長並發展,還是和文淵閣融合形成新的內閣,必然會從根本上改變大明的朝堂。
仁宗這番操作的初衷是想拓寬君臣、皇帝與外界的溝通渠道,廣知民事,而不是被隔絕於深宮之中。不過七個月後,隨著仁宗的駕崩,弘文閣也被新繼任的宣宗給取消了。這又是為什麼呢?
表面上的原因是,為了應對漢王朱高熙的攻擊。
宣宗繼位後,他的叔叔朱高熙指使黨羽以進疏諫言為名,指責先帝仁宗給予文臣誥敕封贈、修理南巡行宮、抬升殿閣大學士們等行為違背《皇明祖訓》。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開設弘文閣。
宣宗繼位初期對咄咄逼人的朱高熙還是以懷柔、安撫為主。所以楊溥為天子分憂,主動提出撤銷剛開設不久還沒有形成影響的弘文閣。和宣宗默契地玩了一招以退為進,化解朱高熙的凌厲攻勢。
不過深層次的原因還是,皇帝又開始防範文官勢力了。在經歷洪武、永樂兩朝高壓統治後,文官們迎來了夢寐以求的賢君仁宗。但是好日子沒過多久,皇帝就駕崩了,而且這段時日裡雙方的關係也並不是想象的那麼融洽。
文官們總是希望皇帝成為傳說中的天子 – 垂衣拱手、無為而治。但是皇帝們作為活生生的人,又有誰願意做“泥菩薩”呢?李時勉案就是這一根本性矛盾的體現。
李時勉以諫言名義攻擊仁宗三大罪,一整修宮殿,勞民傷財;二挑選侍女,好色縱慾;三幾天不上朝,懶政怠政。仁宗差點被氣死(也有不少人認為他就是李時勉氣死的),甚至臨終前還拉著夏元吉說:“時勉廷辱我”,後悔當時沒直接處死他。
仁宗怒甚,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撲以金瓜,脅折者三,曳出幾死......
仁宗大漸,謂夏原吉曰:“時勉廷辱我。”言已,勃然怒,原吉慰解之。其夕,帝崩。
《明史·列傳第五十一》
難道以李時勉為代表的部分文官真的覺得仁宗是個不堪的昏君庸主麼?當然不是,他們只是希望皇帝能被他們限制和約束而已。
當時還是太子的宣宗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裡,想必宣宗是有仔細思慮過這個問題,而且他在繼位之前應該是得出了自己的結論。這一點從他繼位之後的舉措中就可以明顯地看出來。
宣德元年,明宣宗下令在內廷成立內書堂,由外朝的翰林、大學士做講官,教授內官中優秀者讀書。注意是教內官讀書,而不是識字。目的是什麼,不言而喻,宣德需要穩定地培養出內官來幫助自己處理政務。
所以宣宗應該是意識到了,文官與皇帝之間的矛盾根本就無法消除,所以他決定依靠內廷的宦官來對抗外朝的文官集團。
基於這個認知,宣宗就不會繼續擴大文官集團的許可權,而是會想各種辦法來限制或者削減。所以楊溥主動提出裁撤弘文閣,更多的是洞察了皇帝不便明言之意。但是此舉也標誌了明朝君臣之間的溝通開始走向僵化和無效,慢慢陷入了鬥爭的泥潭。